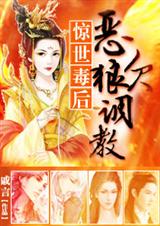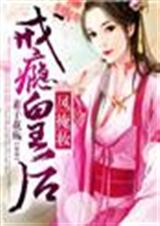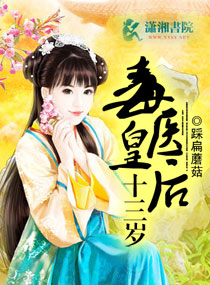唐明皇-第5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应当结束为他担忧受怕的岁月了吧?
不!仍没有完。
那是什么样的岁月啊!
一会,内侍密报:“东宫异常,人传三日内将有刀兵之灾!”
夜不敢寐!
一会,内侍密报:“太平公主府鼓噪,人传即有篡逆之举!”
惊骇万分!
没完没了担惊受怕苦熬日月的他,当时也常常泛舟于这太液池中,徘徊于池心的蓬莱山里,“天啊!真正的蓬莱仙境,你在何处?!朕愿散发木履飘然其间!哪怕让朕能依你的灵石、卧于你的仙芝丛里,过一刻舒心展眉的时光,也胜于头压冕旒,日日惊骇、犯难。”
万想不到,去年七月,正是这折磨了他整整二十九年的三儿,举起莹锋剑,向他的嫡亲姑母无情地投去。
消息传来,使已迁入百福殿中“无为养志”的他,猛觉心如油煎、火焚,两眼一黑,差点昏厥过去。
从那时起,他基本上卧床不起,今年不过五十三岁的他,须发全白,老态龙钟,比七、八十岁的老人还难自持。
在卧床沉思中,他才悟道:这常令他犯难的三儿,岂止神韵、抱负如其曾祖,连那心肠也硬如曾祖!太宗为施展其抱负,青锋所指,不漏同胞兄弟,如今,三儿手中的莹锋,既能向嫡亲姑母砍去,那么,其兄弟的头颅,自然不在话下。
想不到,令他日夜凄惶的事,这么快就发生了!
今晨,他还怔怔地卧伏于百福殿的寝宫里,殿中监姜皎,气急败坏地来禀奏:岐王获罪、危在旦夕!
他还来不及听完姜皎将岐王扮演《死可汗之戏》的事说完,眼前又冒出了团团黑晕。他恍惚看到,李隆基怒目仗剑,大步直逼绑于斩桩上的、神情惶骇的李隆范……
他差点晕倒于寝榻之下!
在姜皎的哀恳、提示下,他忙敕令百福殿总监,前往兴庆坊,宣宋、薛二王解押岐王入宫;他由姜皎搀扶着,上了辂车,直抵大明宫。一路上,他搜肠刮肚,寻找着说服皇帝赦免岐王之罪的理由,想不到,父子刚一见面,三儿就向自己射来那样的目光。眼下,他虽然也止了朝会,扶我返还大明宫,可,他的眼光表明他的杀心已定,断无更改之意。我该怎么办呢?犯难呵!
就要步上丹墀了。
李隆基的脸上、眼里,已没有刚见到太上皇时那不尽的气恼和不满之色。但从两嘴角处那刀刻斧劈般的纹路,却显露出皇帝刚毅果敢的决心:“李唐江山,已被如父皇般的几代懦弱之君弄得晦气冲天,万国不朝,亿兆哀怨!今日,无论是谁,也收不回我出鞘的正国之剑!”
各怀心事的父子俩,步上了丹墀。
紫宸殿的宫侍们,早已打开大殿正门,肘搭拂尘,跪迎在殿檐之下。
李隆基搀扶着父亲,迈入大殿,并将李旦扶入御座;他行了朝见大礼,在御座旁新放的蟠龙御椅上,入了座。
大殿宫侍和两君随驾宫嫔,未见两君下旨,便各随班首,迅速退到紫宸殿两侧长廊之下,屏息侍立;只有一名承宣太监,悄立于殿阶上,听候君命。
紫宸殿外,不时从太液池的上空,传来几声晨鸦的嬉噪。
紫宸殿内,寂静无声。似乎静得连三彩炉内那御制兰麝焚香灰烬断落之声,也略可辨闻。
决心早定。朝会已休。李隆基便镇静地等候着太上发话。
大殿宫侍悄悄地换去了一批焚香。
“多则再上一次焚香,”李隆基望着三彩炉中点点香火,暗揣道,“父皇总得发话了吧……”
“三……郎……!”
就这时,李隆基的耳里传来父亲苍凉的呼唤。他忙一揖手:“父皇!”
可是,好一阵过去了,李隆基却听不见父亲的声音。他有些惊讶地抬头朝御座望去,倏地失措起来:“父皇!你,你?!……”
万万没想到,李旦却伏在御案上,两肩耸动,抽泣开了!
李隆基见父亲那稀疏苍白的鬓角,在伏于御案上的臂弯处颤抖厮磨,他感到一股怜悯之情从心田里升起,鼻子一阵发酸。他陡地立起身来,去御座前搀扶父亲;可是父亲紧伏御案,抽泣得更厉害了!
有那么一瞬,李隆基被父亲的举止搞得头脑懵懂,两眼发直;但当他想到父亲是为什么来到大明宫,又为什么在这紫宸殿内纵横老泪时,那双搀扶父亲的手,却一下子缩了回来!
懦弱的父皇啊!难道你还要用你这懦弱的泪,将我的心浇软、志熔化?难道你想用你这懦弱的泪,消磨掉我那三尺莹锋正国中兴的光芒?
不能!不能!
李隆基闭了闭业已潮湿的双眼,想要离开父亲那抽泣耸动的身躯。
可是,父亲的抽泣声,到底还是留住了他的脚步。这抽泣声,霎那间又化为一连串的质问,在他的耳畔响起:
——父皇为了你,已经暗自流过多少泪、担了多少心?
——父皇在平韦之后,并未依从姑母党羽之谏,将你册为东宫之主!
——父皇力排姑母之阻,传位于你,使你有了翦灭太平、为中兴大唐而一层抱负之机!……
对这样的父皇,能任其伏案悲泣么?天良何在?乏天良者,能安社稷、兴天下吗?
不能!不能啊!
“咚!”
忽然,抽泣得头晕心闷的太上皇,听到身边传来沉重的!声响他忙一下子从御案上抬起头来,却见儿子恭恭敬敬地跪在自己的足旁!
“你、你!”老皇帝手足无措了,忙伸出双手,去搀扶年轻的皇帝。
李隆基的目光落在父亲那瘦骨嶙峋、毫无血色的两掌上,他那铁心钢肠,一下熔化了!他一边归座,一边声音嘶哑地对父亲说:“儿,也是为了宗庙社稷呵!……”他真想说,“可叹却无人为儿的苦心,抛一掬泪水!”但他盯着父亲那泪迹犹存、苍老枯黄的脸,把来到口边的话咽了回去。
李旦听了儿子这掺和着几丝悲凉的抱怨话,心里也凄然、困恼;他诚挚地望着儿子说:“为父者,岂不祈恳上苍,佑儿为一代明君!朕,盼望儿的莹锋剑能早兴乾坤,只是少饮些宗室帝胄的血!……”他的话犹未尽,便又哽哽地说不下去了。
李隆基长叹一声。
“启奏太上、陛下:宋、薛二王,押着岐王殿下于宫门外候宣!”殿中监姜皎,这时匆匆跪奏着。
太上皇闻奏后,将昏花而担忧的目光,投向皇帝;李隆基又长叹一声,才朝姜皎下敕:
“宣进殿来!”
姜皎一颗悬吊吊的心似乎有了些放置处,他慌忙应声出殿而去。
守候在大明宫宫门前的李成器和李隆业,在姜皎宣敕后,忙从马夫手里接过缰绳,踩镫上了坐骑,然后朝四个轿夫一挥马鞭,四人便忙着抬起放于宫门侧边的一乘青葛布篷罩的小轿,悠悠晃晃地随在两位亲王的坐骑后,进了大明宫。
在昭庆门前,两位亲王勒住马缰,由马夫扶着下了坐骑,然后在停放于地的轿门前站住,伸手掀起轿帘,分别轻声唤道:
“四弟!”
“三哥!”
并伸手入轿,将岐王李隆范搀了出来。
三日前兴致勃勃扮演死可汗的岐王,这时真象一个丧魂失魄的死亲王了!他那浓密油黑的头发,绾在头顶,用惨白的绫带扎成个螺髻儿,身上只穿着一条灰绸夹裤,裤外罩着半幅青不青、蓝不蓝的罪裙,上身赤着,足也赤着;两臂被一根丝绦反缚在背后,赤裸的肩上,绑着一根三尺长短、大指粗细的荆条。他面如死灰,眼里闪着落入陷阱无处逃生的野兽那种恐惧、绝望、却又不甘心的光。当大哥和幺弟名为押解、实为搀扶地把他带上御阶时,他望着巍巍紫宸殿,如鬼魅望见刀山油锅,浑身颤索不已。他这极度的恐惧,也传染给扶着他艰难移步的宋王李成器、薛王李隆业,两个人脸色变得煞白,一口又一口地吐出一股股闷气。
临近大殿侧门时,李隆范终于支撑不住,一下子从兄弟肘弯里滑脱,在盈尺高的门栏外,跪伏下去了。
“臣等,叩见太上、大家!”莫奈何,宋、薛二王也只好就地跪下,朗声奏拜。
这一来,慌了殿堂宫侍。他们忙着找来红毡,往侧门前跑去。皇帝却朝他们摆摆手,撩开袍服下摆,走向侧门。看着李隆范的装束、神情,李隆基又是气恼,又是怜悯。他暗暗回头望了望御案上的太上皇。只见父亲注视着这一角落,微微发紫的嘴唇如失去控制一般张开,露出只剩几颗牙齿的淡红的牙龈来。他摇摇头长叹一声,朝宋、薛二王一抬手:“扶他入殿来!”说着,转身回到了自己的座前入了座。
宋、薛二王应声不迭地叩头领旨后,忙扶着岐王进了大殿。在太上皇和皇帝的座间,把他放开,重新跪下;二王却在殿右肃立着。并暗自紧张地窥测着皇帝的神情。
太上皇也怔怔地注视着皇帝。
三对目光,李隆基都察觉到了。他强忍着怒气,冷冷地、朝着跪伏在足前抖似筛糠的岐王唤了一声:“隆范!”
这声冷冷的呼唤,对李隆范来说,不啻一声直贯脑顶的炸雷!他猛地一阵抽搐后,颤声应道:“罪臣在!”
“尔,知罪否?”
“知……知罪在不赦……”
“哼!”
又是一声炸雷,皇帝铁青着脸,按剑而立!
“三、三郎!”望着吓得晕厥过去的四儿,李旦也猛地从御案后立起,颤声呼唤着李隆基。
“陛下!”紧接着,从他的身边,又传来李成器、李隆业那慌乱的哀恳声,二人已双双跪伏在他的身旁。
李隆基却仍按剑走向岐王,声音稍高地唤了一句:“隆范!”
这一声呼唤,使李隆范从麻木中稍稍回过神来,呆呆仰视着李隆基,本能地咽了一口唾沫,又条件反射似地应了一声:“陛下!”
李隆基微微勾下头,又唤:“岐王!”
李隆范只觉得颅腔内“嗡”地一声,赶紧支撑起上半身,呼了声:“万岁哪——”
“四——弟!”
是天旋?是地转?还是紫宸殿被云气所托?阖殿的人,太上皇、宋、薛二王,尤其是岐王,都觉得自己和周围的一切在摇晃、摇晃……忽然,岐王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在地面上膝行着,一下子扑到皇帝的足下,凄切地呼叫着:“三——哥!——”
一股掺和着辛酸的热浪,在李隆基的胸中澎湃;他俯下身去,猛地抽去四弟肩上的荆条,把那赤裸的上身拥入自己怀中!泪水,夺眶而出。
宋王和薛王,也深受震动地掩面而泣。
唯有太上皇,那泪痕尚存、皱纹纵横的脸上,却泛起了笑波。
李隆基任泪水流淌,从怀里松开岐王,将他扶立于座旁。
他拭了拭眼,转过身来,将抽泣不止的宋、薛二王扶起。然后默默地解下佩剑,脱去长裘皇袍,将衬底淡黄绫中衣脱下,给岐王轻轻罩向肩头。岐王双肩却似被滚烫的烙铁烙烧了一般,惊得一跳离地数尺,中衣滑落在地上。他忙着重新跪在地上,拾起中衣,窸窸窣窣地将中衣举过头顶,呈向皇帝,而绾着髻儿的头,却已垂到地面。在一阵极其压抑的、使听者揪心的嘤嘤哭声之后,他突然抬起头来,朝李隆基悔恨不已地嚷起来:“让我死!让我——死呀!”
薛、宋二王,闻声哭得更厉害了。
“四弟呵!”李隆基掺和着深深叹息、充满着手足情谊的呼唤,止住了二人的哭泣。他把岐王扶起,依在自己身边,用露着苦恼和诚挚的目光扫了大哥、幺弟一眼,“你们放宽心怀吧!三郎若有伤慈害亲之意,天日不容!朕,是为了祖宗艰难开创的基业,兴盛宏远呵!……”他顿了一顿,目光渐渐严峻地扫视着身边的岐王、薛王、宋王,直到太上皇的御案前,语气沉痛而凄楚地说下去,“你们,应该懂得,应该懂得了!”
时近申时了。
呈膳太监仍被高力士阻于丹墀下。他发愁地对高力士指指头上已微微西偏的日头,又焦灼地指指殿中,高力士淡淡一笑,朝他摇着手中拂尘,他只得背转身,悻悻而去。
紫宸殿内,只剩下皇帝一人了。
他早已换去了冕旒,戴上了白纱皇帽。脱去长裘龙袍,穿着黄绫团花夹袍,扎着御带,登一双薄底绫靴,坐于御案前,以手托腮,推敲着眼前那道刚刚草成的敕书:
敕:死可汗之戏,外蕃所出;渐渍成俗,因循已久。至使乘肥衣轻,具非法服,阗城鼓噪,深点华风。朕思革颓弊,反于淳朴。书不云乎: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人乃足。况防于政要,取紊礼经。习而行之,将何以训!自今以后,无问蕃汉,即宜禁断!……
望着“即宜禁断”四字,李隆基又提起星拱月升形状的笔架凹中的紫羊毫御笔来,在四字下连连画着圆圈。但是,就在他笔未归架时,他的心中却早已泛起一个苦涩的念头:“‘禁断’、‘禁断’!谈何易呵……”
从他由潞州任上暗藏中兴之志、潜回京师时起,“禁断”二字,便深深地铭刻在他的心目中。当禁不禁,该断不断,坏了军国多少大事!但是,他现在拥有绝对的禁断之权了,方知要实施这两字,是多么的困难!就在今晨,他不是还气若虹,心如铁,要禁断王室贵胄、庙廊大臣中的颓弊之风么?而时过正午,却只能在这一纸黄敕上,禁断区区一戏而已了……霎那间,那被他点着重墨的四字,象一张张满是嘲笑的嘴,对着他。他丢开笔,踱开步,不无狼狈地离开了这一张张嘲笑着的嘴。
长此以往,何事可禁?何事可断?骊山讲武的失败,尚可说用人不当;而眼下只不过决断了一位大臣返朝,便酿出了这么大的风波!
不行!不能这样放过该死的李隆范!
但是,就在他一足迈入座案之间时,他却又独自摇摇头,缓缓退出足来,重新踱着步。
君王无戏言。明君尤应讲信。朝令夕改,徒招朝野疑惧,宫闱更难安宁,百宫难安其位,基此,亿兆何以得安?朝政更难兴盛。
唯今之计?……
亡羊补牢,为时不晚!从今尔后,要坚决地以禁断之气魄,处置朝政!
他凝目立地,静思良久。
“高力士!”
陡地,殿阶上的高力士,听见皇帝在殿堂内一声召唤,他应着声,恭谨急切地迈入殿堂,跪在御案前。
“平身。备好纸笔。记下朕的敕令。”
“奴婢领诏!”
五月,万垅麦香,顺着徐徐南风,弥漫在西京上空;
五月,由上林苑至杜陵,再顺着波浪滚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