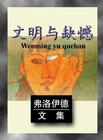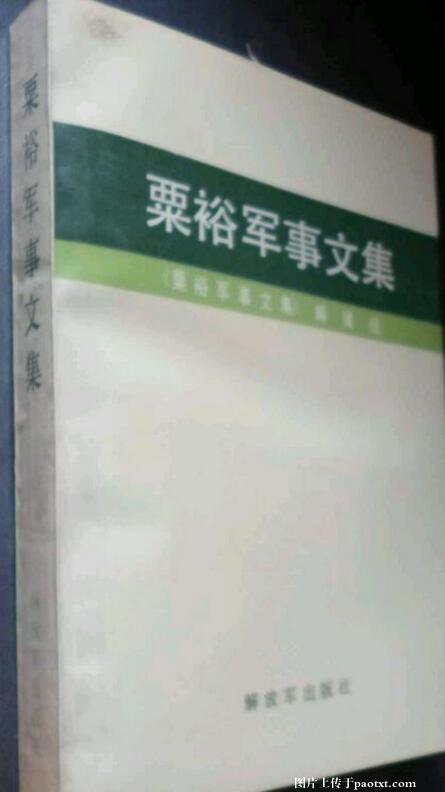石康文集-第5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块平坦的石头后面,突然听见了一阵愤怒的声音……这使我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于是我连忙退了回来。
我暗自希望斯特恩会因为擅闯圣所而受到应有惩罚。但同时,我也禁不住对他心生感激,因为他使我注意到了法拉沙人献燔祭的方式。这条线索很值得跟踪下去,因为它可能提供另一条线索,指出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与其宗教主体人群分离的日期。
我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去研究《旧约》时代犹太人的燔祭仪式这个晦涩课题。
从学术资料的迷雾中最终呈现出来的那幅图景说明:燔祭是一种不断演化的习俗,起初只是一种对上帝的简单供奉,任何人(僧俗均可)在任何设有当地圣所的地方都可以举行。但是,公元前1250年犹太人逃出埃及之后,这种相对不太规则的状况就开始有了转变。希伯来人在西奈荒野流浪期间制造了约柜,并把它罩在一个可以携带的帐篷(或叫〃会幕〃,tabernate,即可携带的神龛)下面。从此以后,所有的献祭都在这个会幕的门前举行,任何违背这条新律者都将受到被驱逐的惩罚:
凡以色列家中的人……献燔祭或是平安祭,若不带到会幕门口献给耶和华,那人必从民中剪除。(见《旧约·利未记》第17章第8…9节——译者注)
但我了解到,这条禁令其实并不像听上去那么绝对。这条律令的要点,并不是要无条件地禁止一切在本地圣所举行的燔祭,而是要确保燔祭只在作为中心的民族祭祀地(如果存在这种地方的话)进行。在荒野上,罩着约柜的会幕就是这样的祭祀中心。
后来,从大约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前1000年,在以色列的夏伊洛建造了民族的祭祀圣所,它就成了新的燔祭中心。不过,有意义的是,在几个政治动荡时期,夏伊洛曾被放弃。在这些时期中,希伯来人被再度允许在本地圣所进行燔祭。
到公元前950年前后,耶路撒冷的所罗门圣殿作为民族宗教中心的地位,已经超过了夏伊洛。然而,有证据表明,许多本地进行的燔祭还是时时出现,在那些远离耶路撒冷居住的犹太人当中,尤其如此。实际上,直到约西亚国王时期(公元前640年一公元前609年),才开始严格贯彻一条总禁令,禁止在圣殿以外举行一切形式的潘祭。
这条禁令实施得极为严格,以至于在公元前587年尼布甲尼撒摧毁那座圣殿后的10年里,犹太人都似乎没有打算在其他地方进行燔祭。在没有了民族祭祀中心的情况下,恢复在本地圣所潘祭的早期传统,这种打算似乎被无可挽回地放弃了。很简单,没有了圣殿,便没有了燔祭。
犹太人结束了在巴比伦的流亡以后,便在耶路撒冷建起了第二座圣殿,在它的区域内又恢复了燔祭的传统,同时,本地圣所的燔祭活动再次被严禁,禁令似乎得到了严格的服从。
这种仅在民族祭祀中心举行燔祭的制度,从公元前520年第二座圣殿建成后被确立下来,直到公元70年第二座圣殿被罗马皇帝提图斯夷为平地为止。犹太人再没有建造第三座圣殿的打算了,只有一批批信奉千禧年的人群怀着梦想,企盼着〃救世主再度临世〃的梦想成真。结果,从公元70年起,犹太人就禁止了在其他地点进行的燔祭。法拉沙人是这条禁律的惟一例外。
不仅如此,斯特恩的叙述还指出:19世纪他在法拉沙人当中传教时,他们在自己的所有圣所举行燔祭活动。经过一些深入考察,我证实了一点:这个传统非常强大,乃至今天大多数法拉沙人的群体都一直在举行燔祭仪式,尽管他们日益面临着现代犹太人的祭祀活动。
考虑到这个事实,我明白了对此可能做出多种解释。但最明显、最具吸引力的解释,却是一种最简单的解释——因而也最有可能是正确的解释。我在自己的笔记里写道:
今天法拉沙人的祖先改信犹太教,想必还是在允许在远离民族祭祀中心的本地圣所举行燔祭的时代。这就是说,他们是在约西亚国王颁布禁令之前改信犹太教的,那个时间不会晚于公元前7世纪,甚至可能更早。
假设,所罗门圣殿建成(公元前10世纪中期)后、约西亚国王(公元前7世纪中期)以前的某个时期,一批犹太人从以色列迁移并定居在了埃塞俄比亚。他们建立了本地的圣所祭坛,在那里向他们的上帝献燔祭,并开始改信了该国居民的宗教。最初他们也许还维持着和自己故乡的联系。但故乡相距遥遥,因此,可以做出一个合理的推断:他们最终成了完全孤立的群体。因此,他们并没有受到一次次神学思想巨变的影响,那些巨变发生在以后几个世纪的犹太人世界里。
因此,法拉沙人才成了惟一仍在实行燔祭的犹太人。他们就像被凝固在琥珀里的苍蝇,落入了时间的扭曲之中,成了现存真正的第一圣殿犹太教最后一批信奉者。
到此为止,一切全都顺理成章。然而问题是:一群犹太人为什么要从以色列迁移到埃塞俄比亚这么遥远的地方呢?我们说的是公元前10世纪到公元前7世纪发生的事情,不是发生在有喷气飞机的现代。那次迁移必定有某种极为强烈的动机,它会是什么呢?
答案是:《国王的光荣》无疑说明了这个动机是什么。
它说,这些移民都是以色列人长子中最先出生的那批人,他们陪同门涅利克来到埃塞俄比亚,和他一起守护约柜,而那是他们从耶路撒冷圣殿里扔来的。
衰微与败落
如果《国王的光荣》里对犹太教进入埃塞俄比亚的叙述是真的,那么,我想我就有希望在历史年表中找到证据,去证实一点:在埃塞俄比亚历史上,犹太人的信仰的地位曾一度比今天重要得多。如果这种信仰最初和门涅利克一世这样的王族有关,那必定更有意义。
不仅如此,我还记得,我的老友理查德·播克赫斯特曾对我提到过一件事,它与这条考察线索有关。1983年我们一起工作时,他曾告诉我说,法拉沙人在历史上曾经是个繁荣强大的部族,并且拥有自己的国王。
因此,我又给亚的斯亚贝巴的理查德打了一个电话,问他能否为我推荐一些可能记载法拉沙人衰微与败落的资料。
他向我推荐了一本书,而我对它的内容略有所知。这本书名叫《1768…1773年寻找尼罗河源头之旅》,其作者是苏格兰探险家,金奈德的詹姆斯·布鲁斯。
潘克赫斯特还建议我去查阅中世纪以来埃塞俄比亚几个王朝的〃宫廷年表〃。他说,这些文献记载了基督教徒和犹太人之间的一系列战争,因而可能会使我感兴趣。他还说:〃除了这些资料以外,我就不知道你能从哪里得到你需要的信息了。困难在于,在布鲁斯以前,没有任何关于法拉沙人的深入记载。〃
我不久就发现,金奈德的詹姆斯·布鲁斯多少算是个谜一样的人物。他出身于顽固的长老会派占主导的斯特灵(苏格兰中部的一个郡——译者注)家族,属于小贵族,继承了足够的遗产,用于毕生在海外旅行。
我起初以为,正是这种〃旅行癖〃诱使他去了埃塞俄比亚高原腹地。但是,当我开始阅读他关于法拉沙人的著作之后,便逐渐认识到:他对法拉沙人的兴趣实在是太强烈、太持久了,因此无法仅仅用一位聪明旅行家通常的好奇心来解释。他用了好几年的时间,巨细靡遗地考察了阿比西尼亚的这些黑种犹太人的信仰、习俗和历史起源。在这个过程中,他记录了许多古代传说,其中交织着不少长者和宗教人物——如果不是他,这些传统大多都会消失在历史中。
其中的一个传说讲到,阿克苏姆的艾扎那国王第一次被介绍给那位年轻的叙利亚人弗路门提乌斯时,正在阅读〃大卫的赞美诗〃,后者后来使这位国王皈依了基督教。不仅如此,布鲁斯还相当清楚地记载说,这位国王很熟悉《旧约》里的这首赞美诗,因为当时(即公元4世纪早期)的埃塞俄比亚十分流行犹太教。
我现在已经了解了法拉沙人的习俗,因此很乐于为这个论断提供证据。我认为这个论断实际上是额外地支持了我那个迅速展开的假设,那就是:至少在弗路门提乌斯到埃塞俄比亚传播基督福音之前1000年,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就有了一种结合了古代血祭传统的信仰形式。
不久,我又在一部珍贵的埃塞俄比亚古代手稿里找到了进一步的证据。那部手稿被保存在提格雷人的马格达拉要塞里。19世纪时,内皮尔元帅(罗伯特·科内利斯·内皮尔,1810…1890,英国陆军元帅,又名〃马格达拉的内皮尔一世男爵〃——译者注)率领的英军曾攻占并洗劫了该要塞。这部手稿的标题是《古代国王的历史及谱系》,其中的一段写道:
基督诞生后的331年,基督教被阿布纳·萨拉玛引入阿比西尼亚,此人原名〃弗路门托斯〃或〃弗路门提乌斯〃。
当时,埃塞俄比亚的国王们统治着阿克苏姆。基督教出现在埃塞俄比亚之前,那里的半数居民均为犹太人,遵守着法律,另外半数居民则崇拜神龙桑多。
这里提到了〃神龙〃(或许是一切原始动物神的统称)的崇拜者,这的确很有意思。它表明,犹太教曾一度成为埃塞俄比亚惟一的国教,并且,在前基督教时代,法拉沙人也曾像各地的犹太人一样,容忍许多异教信仰。
但我认为,随着武装传教的单一神教教徒(例如基督教徒)的到来,法拉沙人必定对异教有所警惕,并且曾试图放弃他们传统的宽容,因为他们很有理由把这些人看作对自己显要地位和信仰的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阿克苏姆国王皈依基督教可以被视为厄兆,从此,犹太人与基督教徒之间很可能不知不觉地产生了永无休止的残酷斗争。
布鲁斯记载下来的传说里,有许多都能证实以上的分析。例如,这位苏格兰探险家强调说,法拉沙人在皈依基督教时(或者用术语说是〃叛教〃时),仍然非常强大。当时,他们宣布确立一位犹太部族的王子作为他们的国王,〃他属于所罗门和门涅利克的种族……这位王子……拒绝放弃其先辈的信仰。〃
布鲁斯还说,这种事态必定要导致冲突,因为基督教徒们也宣布自己的国王属于所罗门的世系。这场冲突一爆发,就陷入了纯粹世俗的种种计较当中:
宗教信仰的不同虽然导致流血冲突,但各个宗教还是各有自己同样自负的国王,由此引发了出于野心及对抗君主力量等动机的战斗。
对这些〃战斗〃,布鲁斯没有提供任何细节。同样,史书也对此讳莫如深,而只提到:公元6世纪,阿克苏姆国王卡列布聚集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并率领它渡过红海,去和也门的一位犹太人国王作战。我现在想知道,阿拉伯半岛上的这场战役,会不会就是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战斗的扩大呢?
在《国王的光荣》里可以找到证据,表明以上情况确实就是历史的真相。在这部伟大史诗的末尾,我看到了一章,它具体地提到了卡列布国王满怀反犹太的激情。在这一章里,没有任何明显原因,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突然被描写成了〃上帝之敌〃。不仅如此,其中还宣扬应当把他们〃碎尸万段〃,应当〃把他们的国土变成一片废墟〃。
这些都出现在卡列布国王的两位王子所说的话中。其中一位王子叫〃以色列〃,另一位叫〃杰伯拉·马斯卡尔〃(其埃塞俄比亚语的意思是〃十字架的奴隶〃)。此处,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冲突的象征极为鲜明,不容忽视,因为〃杰伯拉·马斯卡尔〃显然代表冲突的基督教一派,而〃以色列〃则代表犹太教一派。我想到了一个情况:法拉沙人从不自称〃法拉沙人〃,而总是自称〃贝塔·以色列〃,即〃以色列之屋〃;因此,这就使以上的分析更令人信服了。
因此,这里传达的基本信息已经很清楚了。不过,整个段落却被繁复而晦涩的诸多形象复杂化了。例如,段落中有时会突然冒出〃沙利奥特〃(Chariot)和〃锡安〃(Zion)这两个字。我几乎不知道、或者完全不知道前者是什么意思,但对于后者的意思我已经很清楚,〃锡安〃是《国王的光荣》里频繁用来指代约柜的几个别称之一。
我读到〃以色列〃和〃杰伯拉·马斯卡尔〃注定要交战时,一切都变得清楚了。文中继续写道:
那场战斗之后,上帝会对杰伯拉·马斯卡尔说:〃在沙利奥特与锡安中,吾选择汝。〃而上帝将帮杰伯拉·马斯卡尔拿到锡安,他将公开坐在其父的宝座上开始统治。上帝会使以色列选择沙利奥特,以色列将行秘密的统治,他将不再能被看见。
《国王的光荣》以这种方式做出了结论:
犹太人之王国将被结束,基督之王国将会形成……上帝如此使埃塞俄比亚王比世上其他所有国王都更加荣耀、美好和尊贵,因为他有伟大锡安,即上帝律法之柜。
我认为,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这里描述的是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和基督教徒之间的冲突,尽管使用了神秘的象征性语言——在这场争锋之战中,新宗教的追随者取得了胜利,而旧信仰的信徒则被征服,因而从此只得在一些秘密的地方销声匿迹地生活。同样清楚的是:约柜(即文中的〃锡安〃)是这场权力之战的核心,而基督教徒设法以某种方式从犹太人那里夺取了它,而后者从此不得不满足于拥有〃沙利奥特〃,换句话说,就是拥有次等的好东西。
然而,我的继续研究却表明,法拉沙人显然没有乖乖地屈从于销声匿迹的生活,没有屈从二等阶级的社会地位,那是基督教徒设法强加给他们的。相反,我发现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法拉沙人曾进行过反击——不仅如此,他们还曾以巨大的果敢进行过相当长期的反击。
阿比西尼亚的犹太人与基督教徒之间持续不断的战事,其最初的一则引人入胜的暗示,见于公元9世纪一位旅行家的记述。那位旅行家名叫艾尔达德·哈达尼——他的另一个名字更有名,叫〃丹〃族的艾尔达德,因为他自称属于失踪的以色列〃丹族〃(Dan)。
我们根本不清楚此人是谁,来自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