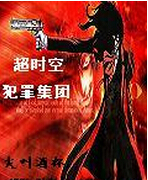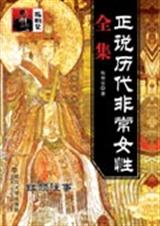季羡林文集-第8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待落了空。他写道:“我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然而到头来却是失望,没有人肯动笔写一写,或者口述让别人写。我心里十分不解,万分担忧。”此外,季羡林还有一个十分不切实际的期待。他希望那些“造反派”、“打砸抢分子”也能够把自己折磨人的心理状态和折磨过程也站出来表露一下,写成一篇文章或一本书。他说:“这一类人现在已经四五十岁了,有的官据要津。即使别人不找他们算账,他们自己如果还有点良心,有点理智的话,在灯红酒绿之余,清夜扪心自问,你能够睡得安稳吗?如果这类人——据估算,人数是不老少的——也写点什么东西的话,拿来与被折磨者和被迫害者写的东西对照一读,对我们人民的教育意义,特别是我们后世子孙的教育意义,会是极大极大的。”季羡林这个期待当然又落了空。
时间已经到了1992年,许多当年被迫害的人已经如深秋的树叶,删繁就简,渐趋凋零,而季羡林此时也已年过八旬,垂垂老矣。他不能再等了。到了此时他才醒悟过来,自己的期待实在过于天真,他写道:“我为什么竟傻到守株待兔专期待别人行动而自己不肯动手呢?期待别人不如期待自己,还是让我自己来吧!”
这就是《牛棚杂忆》的产生经过。
《牛棚杂忆》出版以后,季羡林收到了几百封读者来信。这些来信大部分都不是一般的赞扬或感想,而是联系个人、家庭及亲身经历,出自内心感谢作者“为中华民族做了一个巨大贡献”,认为这本“用血换来”、“和泪写成”的著作“说出了千百万人想说而又未说的话”,来信者,既有饱经风霜的知识分子,也有默默无闻的基层干部;既有耄耋老人,也有年轻学生。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这本书,引起的共鸣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不能不奋笔疾书,把自己心中憋了多年的话都掏出来说给他们十分尊敬的作者听。
《牛棚杂忆》的问世,打破了封冻了二十年的坚冰,开辟了反思历史的新局面,之后,陆续出版了一批思忆文学著作,让人们温故而知新,成为推动改革开放的一股巨大动力。季羡林为此作出的贡献,功不可没。
新时期文坛骁将
季羡林今天成为学界名人,被人称为“大师”、“泰斗”、“国宝”级人物,这与他的“官运亨通,飞黄腾达”其实并没有多少关系,而是与他在改革开放二十余年中,在学术园地里孜孜不倦,呕心沥血,笔耕不辍,辛勤耕耘,取得了丰硕成果分不开的。同时,这二十余年中,年逾古稀的季羡林在整个文化界成了一个十分活跃的人物,参加过众多文化学术领域的建设工作,成为学界改革开放的领军人物之一。他还以思想解放、独立思考、敢说真话、勇涉“禁区”,标新立异,而备受世人关注。
从l978年起,改革开放宛如和煦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整个政治大环境有了比较大的变化,季羡林感到“脑袋上的紧箍咒被砸掉了,可以比较自由地、独立地思考了,从而学术思想比较活跃起来。”这可以说是他在这二十余年中取得成功的客观条件。除此而外,还有一个属于他个人的特殊原因。他说:“我性与人殊,越年纪大,脑筋好像越好用,于是笔耕也就越勤了。季羡林一个晚上写成一篇两三千字的散文是家常便饭,一年完成一部三四十万字的学术著作也轻而易举。他在《九十述怀》中曾说:“从目前的身体情况来看,除了眼睛和耳朵有点不算太大的问题和腿脚不太灵便外,自我感觉还是良好的,写一篇一两千字的文章,倚椅可待。”1998年出版的《季羡林文集》共二十四卷,八百多万字,其中收录的文稿截止到1992年。从1992年到今天十年中,季羡林又写了将近四百万字的文稿,平均每年四十万字。耄耋之年的老人能有如此惊人的笔耕速度,说“性与人殊”实在是一点也不夸大。截至目前,季羡林的全部著作约一千二百万字,其中大部分是在1978年以后完成的。他开玩笑地说道:“从1978年一直到今天的二十年中,我的研究成果在量和质两方面都远远超过这以前的四五十年。我有时候胡思乱想,自己开玩笑:‘如果老天爷或者阎王爷不让我活这样大年纪,让我早早地离开这个世界,那么,我肚子里还有一些丝来不及吐出来,对于我自己,对别人是这样,岂不是一个损失吗?’”
季羡林虽然说的是玩笑话,但他若是真的在“文革”中自杀成功,早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的话,不说别的,像八十万字的《糖史》和《吐火罗文A(焉耆文)译释》这样重要的学术著作就不可能问世了。因为在当今中国,能写这两本著述的,除他以外,没有第二人。那该是多大的损失啊!
季羡林是一位“杂家”。他是语言学家、佛学家、比较文学家、文艺理论家、翻译家,又是散文家。一般人也许读不懂他的印度古代语言、吐火罗文的专著(吐火罗文在当今世界上只有不足三十人懂得),但是,读得懂他的比较文学、东西文化差异和共性的论文,更读得懂他的散文《留德十年》、《牛棚杂忆》、《清塘荷韵》、《二月兰》、《听雨》等,从而对这位“泰斗”的思想、学识和人格有所了解。这是季羡林广为人知又受人尊敬的一个重要原因。
且看季羡林在新时期的二十余年为推动学术繁荣所作的贡献,以及在此期间,他通过独立思考,提出的一些创造性的观点和“标新立异”的见解。
1、重建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源于19世纪的欧洲,作为一个有完整理论体系的学科,比较文学是在20世纪后才发展起来的。在许多国家,比较文学专家辈出,灿如列星,有的甚至形成学派。大家公认的学派有:德国学派、法国学派、西欧学派、美国学派等四个独立的学派。从全世界学术界来看,比较文学的研究在2O世纪已经成了文学研究的主要趋势之一。
比较文学在中国并不是新鲜事物。根据乐黛云教授的论点:“中国比较文学的源头可以上溯到1904年王国维的《尼采与叔本华》,特别是鲁迅19O7年的《摩罗诗力说》和《文化偏至论》。”不过,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出现则是在2O世纪2O年代末、3O年代初。当时最著名的比较文学家是吴宓和陈寅恪。吴宓在清华大学开设了“中西诗之比较”课程;陈寅恪则开设了“中国文学中的印度故事的研究”。清华大学在当时培养了一批学贯中西的比较文学学者,他们是钱钟书、季羡林、李健吾、杨业治等。三四十年代中国比较文学的实绩则是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诗学》和钱钟书的《谈艺录》。由于这些学者的努力,中国比较文学当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可惜的是,建国三十年来,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比较文学被列为学术禁区。理由是:不同阶级的文学没有可比性。无产阶级文学与封建阶级、资产阶级文学不能相提并论。不管这个理论在今天看起来是多么的幼稚可笑,在当时它却是“统治思想”。于是比较文学课程从大学中砍掉了,作为一门学科,在学术界也消失了。到“文革”结束时,这门在世界各国大学里普遍开设的课程,在中国却鲜为人知。
1980年,社会刚刚开放,人们的思想远没有今天这样解放,学术文化领域里各种禁区林立,壁垒森严,比较文学这个“禁区”,当时还无人敢于涉足。
到了1981年,我国同国外的联系逐渐频繁起来,许多国外的书刊又传了进来,其中包括研究比较文学的刊物和书籍。季羡林看了这些著作后,既感到兴奋,又感到苦恼。兴奋的是,现在终于打破了那些无形的枷锁;苦恼的是,我们白白浪费了许多时间,在比较文学研究方面已经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在当时,许多人对于打开国门让西方的思想文化进入国内还顾虑重重,最主要的担忧就是害怕国外的资产阶级思想“污染”了我们的头脑。就在许多人惊呼“打开窗户,装上纱窗,防止外面的蚊子、苍蝇进来”的情况下,季羡林决心打破比较文学研究这个“禁区”。
1981年1月,在季羡林的倡导下,北大与语言文学有关的四个系和两个研究所内对比较文学有兴趣的学者集合在一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研究会。大家一致推举季羡林为会长。研究会很快出版了《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和《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会通讯》。在北大比较文学研究会的影响下,1983年6月,由南开大学、天津师大发起,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比较文学学术讨论会。在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季羡林被推举为名誉会长。1984年,由季羡林主编的全国性比较文学期刋《中国比较文学》在上海创刋。辽宁大学、广西大学、暨南大学随后也召开了比较文学学术讨论会。不久,辽宁、上海、吉林、江苏等地也相继成立了地方性的比较文学学会。1985年以后,比较文学课程在全国各大学普遍开设起来。1987年,国家教委规定:比较文学为某些系科的必修课。
到了8O年代中期,中国比较文学已经形成了一支朝气蓬勃的队伍。同时,中国比较文学开始走向世界。1982年,三位中国学者参加了世界比较文学纽约年会,都提出了学术报告,其中一篇被载入《美国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年鉴》。1983年,中美双边比较文学首次讨论会在北京召开。1985年,杨周翰教授当选为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副会长。
季羡林不但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重新开展的发起人,也是这项学术活动的实践者和引路人。
季羡林本人就是一位杰出的比较文学研究家。在解放前,他曾写过不少比较文学论文,如:《老子在欧洲》、《“猫名”寓言的演变》、《柳宗元取材来源考》等。从1978年开始,季羡林又重新开始研究比较文学,并且写出了大量高质量的论文,如:《里的印度成分》、《在中国》、《吐火罗文A(焉耆文)与中国戏剧发展之关系》、《关于神韵》、《说嚏喷》等。季羡林的比较文学论文,采用影响研究的方法,用确凿的事实和材料说话,决不捕风捉影、牵强附会,因而令人信服。而且由于他学贯中西,能融古今东西于一炉,写起论文来旁征博引、视野开阔、切中肯綮、深入浅出,为学者们所称赞。
季羡林不但身体力行,写作了大量优秀的论文,还提出了一整套关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主张。这些主张归纳起来就是呼吁建立中国比较文学学派。
季羡林认为:我们进行比较文学研究,并不是为比较而比较。对我们来说,比较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我们是想通过各国文学之间,特别是中国文学同其他国家文学之间的比较,探讨出规律性的东西,以利于我们的借鉴,更好地继承和发展我们民族传统中的精华,更好地发展我们的新文艺。
过去一百多年以来,西方许多国家的学者进行比较文学研究,虽然成绩是巨大的,但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他们始终在欧洲文学这同一个“文化圈”内进行比较,从而逐渐形成了比较文学的“欧洲中心论”。西方学者完全忽视了东方文学的存在,这显然是片面的,其局限性十分明显。
季羡林针对世界比较文学的这种片面性,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论点:人类历史上的文化可以归并为四大文化体系:一、中国文化体系;二、印度文化体系;三、波斯、阿拉伯文化体系;四、欧洲文化体系。这四个文化体系都是古老的、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文化体系。拿东方和西方的尺度来看,前三者属于东方,最后一个属于西方。这样形成的文化体系是一个客观存在,不是哪个人凭空想象捏造出来的。既然如比,研究比较文学就必须重视东方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重视中国、印度、伊朗、阿拉伯、日本等许多东方国家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巨大影响,其中包括对欧洲文学的影响。季羡林的新理论,受到世界比较文学界的重视,特别得到亚洲各国学者的支持。此基础上,季羡林又进一步提出了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主张。他在《比较文学与文化交流》一文中说:
什么叫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我认为,至少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以我为主,以中国为主,决定“拿来”或者扬弃。我们决不无端地吸收外国东西;我们决不无端地摒弃外国东西。只要对我们有用,我们就拿来,否则就扬弃。这一点“功利主义”我看是必须讲的。第二个特点是,把东方文学,特别是中国文学,纳入比较文学的轨道,以纠正过去欧洲中心论的偏颇。没有东方文学,所谓比较文学就是不完整的比较文学。
季羡林关于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主张得到中国学者们的一致赞同,也得到国外许多著名学者的支持。
在中国比较文学发展过程中,季羡林谦虚地以“比较文学的一个没有成就的老兵”和“一个忠诚的比较文学的啦啦队员”的身分,及时指出中国比较文学发展中的不足之处,引导中国比较文学沿着正确道路前进。比如,2O世纪80年代中期,比较文学在中国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的气象,但是一些人误以为“比较文学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一时间,文坛上出现了一些乱比瞎比的文章。季羡林在读了大量比较文学论文之后,感到照这样“比”下去,中国比较文学将会出现危机。于是他写了《比较文学之我见》一文,提醒学者们注意这一不良倾向。他写道:
现在不少作者喜欢中外文学家的比较。在中国选一个大作家,比如屈原、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等等。又在外国选一个大作家,比如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等等,选的标准据说是有的,但是我辈凡人很难看出。一旦选定,他们就比开。文章有时还写得挺长,而且不缺乏崭新的名词、术语。但结果呢?却并不高明,我不说别人,只讲自己。我自己往往如坠五里雾中,摸不着边际,总觉得文章没有搔着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