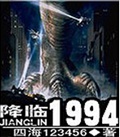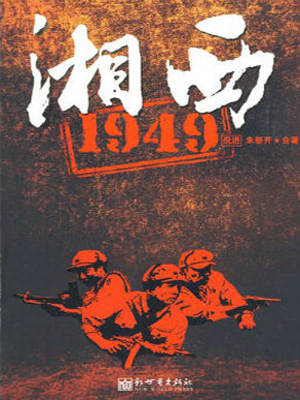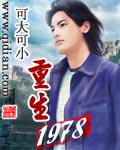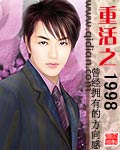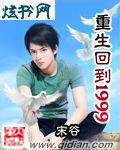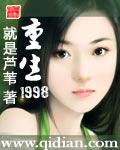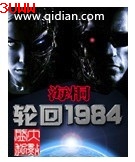贾想1996-2008-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吕新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其实讨论贾樟柯很难,他给批评家留的空间很小,因为他是他自己电影最好的理论家,他把自己的电影说得滴水不漏。我的问题是,《二十四城记》在不同的艺术媒介之间来回转换,从多个方面打破了电影的传统叙述方式。比如刻意地挪用纪录片的形式,把电影导演的角色转换为一个采访者的角色,比如镜头内外的跨越。这个跨越过程中出现了一个矛盾。当你自己把自己放进去,这是一个限制性视角,你能采访到的东西才会呈现出来,你采访不到的东西,就可以刻意不去呈现;而那些刻意不去呈现的特点,恰恰可能是电影的要点。你采用了非常传统的纪录片的方式,我只拍我看到的,放弃那种全知视角和全知叙述,回到现实性的叙述。但是这种限制性视角的刻意采用,恰恰和诗人角色的出现形成一个对比。电影中诗歌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一个先知的角色,或者说一个价值评判者的角色。诗人的预言和判断功能被你重新恢复,这一功能的恢复恰恰建立在一个全知视角和超越性视角的基础上。
整个片子是关于逝去的故事,逝去的孩子,逝去的爱情,逝去的青春,逝去的岁月??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逝去的。这些逝去的东西是看不见的,所以你特别限制表象。有的时候你好像刻意被这个东西给包围住了。这样一种伪装的纪录片,伪装的采访者,或者伪装的故事片,实际上是反故事片的故事片。还有一个小细节,电影中的人物多用方言,包括你自己的
采访也带有地方口音。可是我觉得奇怪的是,你为什么能容忍吕丽萍那么标准的普通话在这里面出现?当我听到吕丽萍声音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原来那个声音在这里断掉了,忽然变成了像电视剧里面的说话,这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在整个片子里面,这可能是一个破绽。
阐释中国的电影诗人(5)
贾:我在做这部片子的时候,希望它是一个能够跨媒介的方法。因为电影的时间性跟它的视觉的连续性,可以提供一种跨媒介的可能性,包括大量的采访是借用语言的部分,诗歌是借用文字的部分,有肖像的部分,有音乐的部分。实际上最简单的也是最初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希望通过多种形式的混杂,把一个多层面的复杂的东西呈现出来。我接触到那些记忆的时候,觉得特别复杂。记忆的呈现是特别复杂的一个过程,包括做这个采访工作的时候,导演跟被采访人物的关系,还有导演跟电影的关系,也是非常复杂的。最后我就想把它们都容纳在一起,把这种复杂性结合在一起。像吕丽萍饰演的那个片段,本来在剧情中他们是从沈阳搬过来的,普通话跟东北话有接近的地方;而且因为吕丽萍现在的丈夫也是东北人,我觉得她能说一些东北话,结果她不行,一点东北话的味道都没有。在语言上,这肯定是一个损失, 没有呈现出这种地方语言的特点,但是吕丽萍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她的讲述状态里的那种控制能力。我已经不可能找到这个当事人,因为当事人已不在人世了,这个事情讲的是这个厂牺牲的第一个孩子。我看中吕丽萍的一个地方,就是她自身是一个母亲,然后有很长时间是一个单亲的母亲,她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很牢靠,她作为母亲的感触是非常强烈的。所以我觉得有这个心理依据,她在感受这个剧本,感受这个故事的时候,可能比其他的演员要更加有优势。所以在语言方面有一些牺牲吧。
在跨媒介的方法方面,我希望能够自由,希望能够回到早期默片时候那个活泼的阶段。没有城市,也不分电影是纪录的电影,还是剧情的电影,电影就是电影。因为大家都不清楚电影 是什么东西,所以那个时候电影能够容纳很多。包括默片里面有很多字幕啊,很文学性的东西。通过这样一个努力,让我们重新审视电影现在的情况。我觉得无论是剧情片,还是纪录片,都陷入了一种类型的限制里面,是不是有一种方法可以破解?当然它不是常规的,就像你说的,它不可能把中国所有的电影陈规都打破,但是它至少有这种可能性,或者会发现一种新的可能性,但它是以一种回归默片的方式来实现的。
欧阳:可能几乎所有的诗人,都会喜欢贾樟柯这种工作方式。他的作品呈现影像,呈现记忆,他进入这个世界的角度和方式,正如安德鲁先生非常敏锐地看到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个用影像进行工作的诗人。因为诗歌有各种各样的形式,除了语言以外,它还有影像,还有声音的纪录角度。比如说翟永明,她就是想超出词语的范围、文本的范围进入诗歌,所以她也关注音乐,关注美术,关注电影。她在电影方面的经验非常丰富,这次跟贾樟柯的合作,我觉得非常成功。刚才贾樟柯讲,他原来拍了50个人,最后把那些刺激性的、个人传奇性的东西都去掉了。于坚也当过工人,他觉得不刺激,简单了一点。但是我想,正是由于这种简单,它变得抽象起来,整个电影变得从生活中突然上升起来了,到了一个空虚的高度,一个虚构的高度。这个电影最后的文本,突破了我们对电影所有的构想。它不是一个故事片不是一个剧情片,不是一个纪录片,不是一个电视剧,也不是一个口述史,它什么都不是,但是又诠释着这一切。它特别奇怪。这样一个自我矛盾的、互相诋毁的东西,被压到传奇性、娱乐性的最低限度,诗意在这个时候出现。但是诗意不是拔高的结果,而是一个压缩、削减、减法的过程。浓缩到最后,它是一个###裸的、干枯枯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历史文本,我们的记忆。
我非常钦佩达德利?安德鲁的眼光,刚才他提到的绿色,中国画家张晓刚也注意到这一点。张晓刚画1970年代记忆的系列作品,就是在画绿色。在从前苏联到美国去的诗人布罗茨基回忆早年生活的散文《小于一》中也谈到了这个遍布整个苏维埃的邮政等高线,我把它称之为邮政绿,米的邮政绿。在中国标准的高度是米,还有标准的颜色和浓度。这个邮政绿太有意思了,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产物,资本主义不可能有的,这也是几个费解的问题之一。
吕教授刚才谈到,《二十四城记》是一部关于消逝的电影,这个消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消逝。所谓消逝和失去也可能一样。比如这次金融危机,雷曼兄弟没了,很多人赚了几十年的钱
突然没有了。这个搬迁的故事,讲的是这个工厂要消失,然后另外一个新城,所谓的居住空间要起来。在商品房里住的人,他们各自的生命不发生交叉,他们只是在这儿住,他们干的事情,他们的灵魂、教育、文化完全不一样,但只要有钱可以到这儿来住。搬来的人的空间是一个独立王国,从上海、辽宁或其他某个地方搬过来,变成一个独立的文化体,跟它所在的那个城市毫无关系了。他们1950年前从自己的家乡搬来,然后没有自己的故乡,到这儿建立一个理想主义的城市。五十年以后,一切都不在了。非常有意思。
原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11月8日)
这是我们一整代人的懦弱(演讲)(1)
这是我们一整代人的懦弱(演讲)
大家好!感谢大家抽空来看《三峡好人》。刚才我也在观众席里面,我本来想看10分钟然后离开去休息,结果一直看到了最后。这部电影五月份的时候还在拍,过了三个月好像那儿的一切我已经遗忘了,再看的时候非常陌生,但同时又非常熟悉,因为我在那儿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和我的同事们工作,所以人是善于遗忘的族群,我们太容易遗忘了,所以我们需要电影。
我是第一次去三峡,特别感谢刘小东。因为这之前我本来想拍一个纪录片,拍他的绘画世界。我从1990年看他第一个个展,特别喜欢他的画。他总是能够在日常生活里面发现我们察觉不到的诗意,那个诗意是我们每天生活其中的。这个计划一直搁浅,一直推后。有一天小东在去年9月的时候说要到三峡画11个工人,我就追随着他拍纪录片《东》。
在三峡,如果我们仅仅作为一个游客,我们仍然能看到青山绿水,不老的山和灵动的水。但是如果我们上岸,走过那些街道,走进街坊邻居里面,进入到这些个家庭,我们会发现在这些古老的山水里面有这些现代的人,但是他们家徒四壁。这个巨大的变动表现为100万人的移民,包括两千多年的城市瞬间拆掉。在这样一个快速转变里面,所有的压力、责任、所有那些要用冗长的岁月支持下去的生活都是他们在承受。我们这些游客拿着摄影机、照相机看山看水看那些房子,好像与我们无关。但是当我们坐下来想的时候,这么巨大的变化可能在我们内心深处也有。或许我们每天忙碌地挤地铁,或许凌晨###从办公室里面出来坐着车一个人回家的时候,那种无助感和孤独感是一样的。我始终认为在中国社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我们都承受着所有的变化。这变化带给我们充裕的物质,我们今天去到任何一个超市里面,你会觉得这个时代物质那样充裕,但是我们同时也承受着这个时代带给我们的压力,那些改变了的时空,那些我们睡不醒觉,每天日夜不分的生活,是每一个人都有的,不仅是三峡的人民。
进入到那个地区的时候,我觉得一下子有心里潮湿的感觉。站在街道上看那个码头,奉节是一个风云际会、船来船往的地方,各种各样的人在那儿交汇,忙忙碌碌,依然可以看出中国人那么辛苦,那时候就有拍电影的欲望。一开始拍纪录片,拍小东的工作,逐渐地进入到模特的世界里面。有一天我拍一个老者的时候,就是电影里面拿出十块钱给三明看夔门的演员,拍他的时候,他在镜头面前时非常自然。当他离开摄影机的时候他一边抽烟,一边非常狡黠地笑了一下,我刹那间捕捉到了他的微笑。在他的微笑里有他自己的自尊和对电影的不接受,好像说你们这些游客,你们这些一晃而过的人,你们知道多少生活呢?那个夜晚
在宾馆里面我一个人睡不着觉,我觉得或许这是纪录片的局限,每个人都有保护自己的一种自然的一种心态。
这时候我就开始有一个蓬勃的故事片的想象,我想象他们会面临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压力,很快地就形成了《三峡好人》这样的剧情。在做的时候我跟副导演一起商量,我说我们要做一个这样的电影,因为我们是外来人,我们不可能像生活在当地的真的经受巨变的人那样了解这个地方,我们以一个外来者的角度写这个地区。这个地区是个江湖,那条江流淌了几千年,那么多的人来人往,应该有很强的江湖感在里面。 txt小说上传分享
这是我们一整代人的懦弱(演讲)(2)
直到今天谁又不是生活在江湖里面,或者你是报社的记者你有报社的江湖,或者你是房地产的老板你有房地产的江湖,你要遵守规则,你要打拼,你要在险恶的生活里生存下去,就像电影里面一块五就可以住店,和那店老板一样,他要用这样的打拼为生活做铺垫,想到这些的时候我很快去写剧本。
在街道上走的时候就碰到唱歌的小孩子,他拉着我的手说,你们是不是要住店?我说我们不住店。他问我是不是要吃饭?我说我们吃过了。他很失望,又问,那你们要不要坐车?我说你们家究竟是做什么生意的。他就一笑。我望着14岁少年的背影,我觉得或许这就是主动的生命的态度。后来我找到他,问他最喜欢什么?他说喜欢唱歌,他就给我唱了《老鼠爱大米》,唱了《两只蝴蝶》,然后我非常矫情地问他会唱邓丽君的歌吗?后来教他也教不会,他只会唱《老鼠爱大米》,所以用在了电影里面,他像一个天使一样。
在任何一种情况里面,人都在试着保持尊严,保持活下去的主动的能力。想到这些的时候,逐渐地,人物在内心里面开始形成。我马上想到了我的表弟,我二姨的孩子。他曾经在《站台》里演过签定生死合同的矿工,在《世界》里演过一个背着黑色提包,来处理二姑娘后事的亲戚。这次我觉得他应该变成这个电影的主角。我们两兄弟少年的时候非常亲密。他十###岁以后离开了家,到了煤矿工作,逐渐就疏远了,但是我知道他内心涌动着所有的感情。每次回家的时候我们话非常少,非常疏远,非常陌生,就这样看着偶尔笑一下。想到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就想到他的面孔。我每次看到他的面孔,不说什么,但我就知道,我为什
么要一直拍这样的电影,为什么十年的时间里我不愿意把摄影机从这样的面孔前挪走。
我们太容易生活在自己的一个范围里面了,以为我们的世界就是这个世界。其实我们只要走出去一步,或者就看看我们的亲人,就会发现根本不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拍,不能那么容易将真实世界忘记。
我表弟后来来到剧组,我觉得演得非常好。一开始的时候,我特别担心他跟很多四川的演员搭戏搭不上来,怕语言有问题。他说,哥,你不用担心,我听得懂,我们矿上有很多陕西四川的工人,所以陕西话、四川话我全部能听得懂。他沟通得确实很好,跟其他当地的演员。特别是拍到他跟他的前妻在江边聚会的那场戏。他的前妻问他一个问题,16年了,你为什么这个时候到奉节找我了?我写的对白是,春天的时候,煤矿出了事情我被压在底下了,在底下的时候我想,如果能够活着出来的时候我一定要看看你们,看看孩子。这个方案拍得很好,第一条过了。他拉着我说,能不能再拍,我不愿意把这些话说出来。为什么把这个
理由讲出来呢?因为他说在矿里面什么样的情况谁都了解,如果讲出来,感觉就小了,如果不说出来感觉就大了。
他说得非常好,生活里面那么多的事情何必说那么清楚呢。就好像这部电影其实有很多前因后果,没必要讲那么清楚。因为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