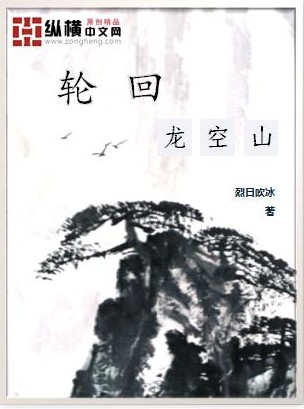空山疯语-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进击。
棋在盘外。
(此文收入《百年烟雨图》)。
史成芳与保尔
《北大往事》一书中有很多好文章,我个人感触最深的是王岳川的《生命与学术》和周阅的《向死而生》,这两篇文章都讲到史成芳博士身患癌症顽强不屈的事迹。而今,史成芳以34岁的英年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当我在八宝山向史成芳的遗容望上最后一眼时,一句熟悉的话蓦地袭入我的耳鼓:“要赶紧生活!”
这是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保尔·柯察金所说的一句名言。不久前我看到有人撰文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部坏书,因为它是斯大林时代的伪文学。我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斯大林时代是不是应该全盘否定,这首先是一个大问题,就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是不是应该全盘否定一样。如果没有斯大林使苏联在三个五年计划内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强国,如果没有斯大林率领苏联人民以神圣的毅力和巨大的牺牲抵抗和消灭了法西斯,如果没有以斯大林精神创建的华约组织与美帝国主义的北约组织对峙了几十年,那么恐怕中国早已亡国灭种,轮不到任何人来对着伟人的背影指指点点了。与斯大林所保卫和拯救的人群相比,他的专制、他的内部清洗,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罪过,毕竟是第二位的。更何况在斯大林时代,涌现出人类文学史上一批最壮丽的诗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之所以使千百万人流下热泪,并不是它宣扬了某种政治意识形态,而是它讲述了一个人如何面对生命——这一普通而又伟大的真理。保尔·柯察金是不是共产党员,这并不重要。退一万步说,即使他是一个纳粹法西斯,就凭他面对多种病魔,面对死亡,仍然为自己的理想而战斗不息,这本身就是值得尊敬的。对真诚和勇敢没有感情、没有体会的人,是理解不了保尔的,当然也理解不了今天的史成芳。
史成芳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纳粹。但是他最懂得要赶紧生活。我们北大中文系93级博士中共有黄凤显、漆永祥和我3名共产党员,我们都经常与史成芳谈笑。我向他请教过关于弗莱、关于本雅明等西方诗学问题,我们还一起探讨气功、八卦等中国古代文化。他身高骨大,长胳膊长腿。阿城的小说《棋王》中有个人物外号叫“脚卵”,我觉得放在老史身上也挺合适。我们几个党员都爱开点不甚高雅的玩笑,老史的笑容总是一半很开心、一半很腼腆。我们那时都认为一位叫“老淫”的同学身体不好,谁也没有想到病魔会选中老史。当黄凤显书记告诉我时,我马上就联想到“残酷无情”几个字。因为那时我已经知道了史成芳和周阅不容易的婚姻生活。尽管我们这些已经成了家的博士生都不容易,各有一本或数本难念的经,但老史和小周的经要比我们更难念一些。同时我又想到史成芳的学术课题恰好是研究时间意识,而今时间意识真的向他本人敲门了,我不知道这是上帝对他的奖赏还是惩罚……
第一次手术据说很成功,但他毕竟不能如期完成论文了。那段时间他常来找我下围棋。他把“下棋”叫“打棋”,常在楼道里半从容半急迫地叫:“老孔,打一盘棋。”他的棋风可以用“赶紧生活”来概括,总是恨不能一举歼灭我某个方面军,时时企图与我大部队进行战略决战。我知道他们学过当代文学的人下棋都是力战型,而我则是追求所谓“大局观”,喜欢不战而屈人之兵。而老史无论在何种恶劣的情势下,都坚韧不拔,从不主动推枰认输,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做百分之百的拼搏,结果真的有好几次被他扭转乾坤,反败为胜。事实逼得我向他的棋风靠拢,但我总不能像他那样专注。我有时意识到自己是在逃避时间,我在25岁以前是不逃避的,也像老史一样,一刀一枪地捉定每一个虚拟的对手。为什么在我25岁以后,整个中国文化界都陷入了对时间的逃避呢?史成芳有一篇文章可以提示我们,文章的标题叫《历史的坍塌》。当无边的岁月坍塌到我们有限的生命之上时,正需要挺立起千百万个保尔。而可恨的中国现状是,满街甫志高,遍地余永泽,一个个西装革履或者是青鞋布袜,一边嘲笑着保尔和江姐,一边叫卖着他们的逃避哲学。
身边的年轻生命已经逝去很多了。我有时便会想,也许癌细胞已经繁殖在我体内的某个脏器,也许某一天我偶然体检时被医生告知:你还能活一到两年!当我骑车穿行在毫无交通秩序的下班车流中,随便一个司机的疏忽就可能使我再见不到我的妻儿老母。这时,保尔的“虚度年华”和“碌碌无为”的告诫便回响在耳边。
老史病危期间,我没有去医院看他。我不知道该对他说些什么,因为他是那样的清醒,那样的坚强,巨痛之下不要求使用镇静剂,也不喊不叫。他既不需要安慰,也不需要鼓励。我只能期待他再一次走出医院,叫道:“老孔,打一盘棋!”当我从山西开会归来,我爱人让我镇静一下,告诉我一件不幸的事,我一下就预感到了……我当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代北大全体93级博士拟了一副挽联:“三载同窗如梦,隽语欢颜都入史;一盘妙弈常新,英才伟志尽成芳。”
自从史成芳动手术,自从得知中关村一带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只有50岁出头,我就到处宣传要从30岁开始保重身体。那天与周阅握手时,我也说了一句“保重”。但今天我想向所有60年代出生的朋友们补充一句:“要赶紧生活。”
(此文发表于《中华读书报》1998/9/9,引起较为广泛的反响,其中“满街甫志高,遍地余永泽”已成为流传大江南北的警句,到处被转述引用。
我看钱理群
现在就要企图全面地臧否一下钱理群,似乎为时过早。因为他不是那种从南坡爬上山顶就从北坡坐缆车下去的人,他是上了山顶就不打算下去,要在山顶搭台唱戏的人。尽管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即他最好的戏已经在登顶的过程中唱过了,但在山顶上将要演出的戏绝对不会令人失望,则是基本没人怀疑的。
钱理群是一个具体的人,但又具体得很“抽象”。“钱理群”三个字对于认识他的人来说,已经成为精神内涵比较丰富的某种意象。我读过的评论钱理群的文章如王得后、汪晖、陈思和、薛毅等人之作,普遍对那种意象有所触及。我自己写的关于钱理群的文章,也试图把握那个意象,但却总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觉。看来意象是不好强行把握的,还是循规蹈矩地有啥说啥为好。
对于我们这一代成长于80年代的青年学生来说,钱理群首先是一个青年导师。陈平原老师曾戏言钱理群是“好为人师”,我觉得这不但抓住了钱理群的最大特点,而且说到了钱理群最根本的生存意义上。钱理群可以不当学者、不当教授,但绝不能不当老师。不当老师的钱理群不是钱理群。我认为毛泽东骨子里也是“好为人师”,他也是什么都可以不当,但一定要当老师。毛泽东说过“四个伟大”的赞颂里他只同意“伟大的导师”一条。钱理群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批判研究迟迟难以展开,我觉得有一个内在原因:钱理群和毛泽东的性情是有很多相通的,他们都是启蒙家。就对于启蒙的热情来讲,恐怕鲁迅也要逊于毛泽东。只是毛泽东的启蒙越到后来,越借助了思想之外的力量——进而直接将启蒙变成了“改造”。而鲁迅和钱理群这一类人,由于基本没有思想之外的力量可以借助,所以一方面保持了启蒙的纯洁,另一方面则使本人乃至包括启蒙本身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不过即便如此,学生们也反对让钱理群去当官,他们喜欢只有思想的钱理群。学生们宁可自己去当官去赚钱,也要保护钱理群这个纯粹的“人师”形象。
我第一次见到钱理群,他40岁出头,貌似一个年富力强的恶僧,风风火火地走来走去。我以为这是一位很勤勉的进修教师——若干年后,我也曾被误认作进修教师,然而是不勤勉的。及至慕名去听钱理群的课,发现原来就是那个恶僧,不禁心中一动。他一张口,我就被吸引住了——我欣赏的老师甚多,但能这样吸引我,使我在课堂上基本不做其他事情的老师,仅此一位。他汹涌的激情,在挤满了几百人的大教室里奔突着,回荡着。他深刻的见解,时而引起一阵急雨般的掌声,时而把学生牢牢钉在座位上,全场鸦雀无声。即使在冬天,他也满头大汗,黑板擦就在眼前,他却东找西抓寻不见,经常用手在黑板上乱涂着他那奔突又奔突不开,卷曲又卷曲不顺的字体。听他的课,我不坐第一排,即便坐第一排,也坐在边上。这样才能抵御他思想的巨大裹胁力。保持一份自我的思索和对他的静观。我发现自己越是上喜欢的老师的课,越爱给老师起外号或者挑语病,大概就是出于这种潜意识。
钱理群的思想,通过北大和其他学校的课堂,辐射出去,影响了整个80年代的中国青年界。他的专著出版很晚,但他的鲁迅观,他的周作人观,他的中国知识分子观,他的现代文学史观,早已成为一代学子共同的精神财富。如果将来有人以钱理群为研究课题的话,我先提醒一句,他的书是第二位的,他的课才是第一位的。“课堂”研究有朝一日应该成为我们的学术话题。无论从投入的热情与精力,内容的精彩与饱满,得到的反响和愉悦,钱理群的课都比他的书更重要。听过他课的人再拿到他的书,不是有一种急于打开的冲动,而是有一种再三推迟打开的眷恋。中国80年代不乏比钱理群声望更高的思想家和启蒙者,但他们留给青年的只是一些概念和判断,而钱理群给予青年的是一团熊熊燃烧的活的启蒙精神。他的启蒙不是“最高指示”,也不是大鸣大放大批判,而是用自己的生命去体会和言说他所敢于直面的世界。所以他思想的感人程度是既深且远的。
钱理群的思想方式一是深刻的怀疑精神,这很明显是来自鲁迅。鲁迅的怀疑精神被埋藏了许多年,钱理群把它从尘封中掘出,高高地扬起,为之再三咏叹。于是,学生们都习惯了怀疑,不但怀疑“历史”、“学问”、“道德”,而且一直怀疑到鲁迅,怀疑到钱理群本人。当钱理群学生的一大好处就是可以不听他的话,反驳他的话和说他的坏话。
其次,钱理群的思想方式有一种“大”的力量。他视野开阔,善于捕捉重大的话题,善于从大处着眼,善于小中见大,化微为著。钱理群十分注意一个具体学术问题的“时空坐标”。他笔下经常出现“20世纪”、“中国”、“中西”、“大”等词汇,这些词汇今天已经成了青年学者文章中的常用词。这种大思维方式既是得益于马列主义的基本素养,更是决定于对自身生存境况的强烈关注。钱理群经常号称自己善于从别人那里“偷”各种理论和方法,他的论著中也的确什么顺手用什么,从精神分析、原型批评、神话理论到接受美学乃至女权主义,但是他用来“偷”这些和驾驭这些的最基本的功夫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和思辨哲学,包括从人的基本生存境况出发去研究人的精神产品,从上层建筑各部分的互动关联中去考察文学等。所以他的思想始终具有一种高屋建瓴的“大”的气势。
钱理群思想方式的第三个特点是善于抓取“意象”。即研究客体中反复出现的那些最能表现“本质”的典型语汇。这种思想方式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需要有极强的“悟性”。而这所谓“悟性”不是神秘兮兮自欺欺人的,它实际就来自对自己生活的切肤体验并把这种体验投射到研究中去。如钱理群在鲁迅身上抓取了“绝望”、“抗争”,在周作人身上抓取了“苦住”、“兴趣”,在话剧问题上抓取了“大舞台”和“小舞台”,在40年代文学中抓取了“流亡”和“荒野”,在1948年文学中抓取了“生存”和“挣扎”,……这些意象的选取事实上都是一种主客观的契合。当不能找到合适的意象时,钱理群的研究就不能深入进行下去。一旦找到了合适的意象,则如同杠杆找到了支点,“成吨的钢铁,它轻轻地一抓就起来”。这种研究方法是钱理群在学术实践中自己摸索形成的,但还没有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得到系统的总结和推广。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这种方法具有将“现象学”和“历史主义”结合起来的特点。但它同时又带有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诗学的某种气息。或许不必急着去总结它,让它在流动中发展下去更好。总结常常意味着凝固。
除了是一位优秀的学术研究者之外,钱理群还是一位卓越的学术研究组织者,或者说是学术战略家。钱理群经常宣布他的研究计划,经常为别人和整个学科策划研究步骤。他对自己的专业有着良好的把握,不但熟悉各个具体研究对象,而且熟悉研究队伍,他心中装着一幅详细的学术导游图。他对别人的生活也许不大懂,但他知道谁研究什么最合适。他对专业研究的进展保持着比较宏伟的构想,比如他认为目前应当进行出版研究、校园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研究、文学与政治研究等等,他已经把这些研究课题布置或建议给其他的研究者。在他周围,出现了一种“规模研究”的集团优势。这对于今后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启示意义。
钱理群目前无论在专业领域,还是在整个知识文化界,都已经获得了比较高的声誉。声誉高了,自然也会使不同角度的人觉得他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在我看来,钱理群的研究似乎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一是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平衡问题。在80年代就有人对我说:“你干吗跟钱理群学呀?钱理群不是搞文学的。”这话显然是把“文学”看得太窄了,但它曲折地表达出了一种感觉。钱理群的历史唯物主义有时不能与他的意象法结合得天衣无缝,的确有现实关怀的激情不是从文本分析中得出来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