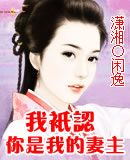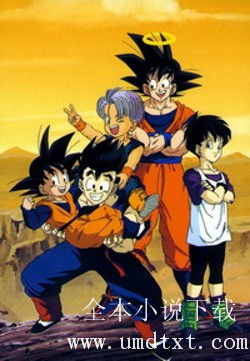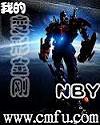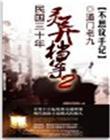我的三十年·百姓影像-第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何:一开始我们都不知道画也是一种商品。最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有台湾的收藏人士到内地收画,我在美国的时候就认识了这些收藏家,那时候就卖出了自己的第一批画;回国后发现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已经开始形成了。那时候画廊还很少,买家一般直接找画家去买,且以个人收藏为主。
牛:据说你在美国还很反感商业绘画?
何:对。我很不适应画那种商品画,还给朋友写信谈了这个问题,在国内一些刊物上也发表过这种看法,对绘画的商品化与市场化进行激烈批判。现在看来是非常偏激的。
牛:你是希望保持绘画的纯粹性?
何:想为艺术而艺术。(笑)我对绘画理直气壮地成为商品很不适应。当时的确很幼稚。现在看来,既然有人消费绘画,消费艺术,那它就是一种商品。在国外,艺术品分了很多市场,绘画也分了很多档次,每个档次都有自己特定的消费群,最后形成了一个很完善的绘画市场。
中国绘画市场的形成也很快,从只有画家开始,很快就有了一切。既然全球化的过程开始了,绘画也不可避免地进入了经济领域。短短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就形成了当下的格局。
牛:你算是较早一批被画商看中的画家吧?
何:算其中之一吧。其实陈丹青、艾轩他们更早一些。那时候已经有画商在收藏中国画家的作品了,价格很便宜。那些收藏家和画商收的种类也很多,有些着重收中国的观念性绘画,着眼于美术史;有些看重的是中国绘画的写实性;也有对中国民俗感兴趣的,对中国乡土感兴趣的。每个品种都有它的市场。不过因为买家是他们,所以他们的兴趣和倾向也影响了一些中国画家的题材与技法。中国大的社会背景、传统符号都容易受到国外收藏家的关注。当时一流的作品很多都外流了。国内也没有够实力的收藏家,开价太低了买不到画,美术机构也不能左右画家的作品。
牛:你的作品里对个体的描绘很多,你也说过自己基本上不关注群体,是不是和你个人的审美取向有关?
何:我主要是对细微的东西感兴趣,不喜欢喧嚣,不喜欢刺激,不喜欢大的场景。宁可画一些肖像性质的作品,很安静地画,让人也可以很安静地看,冷静地看,探索这种细节和人的内心世界。而且(主角)以女性为主,因为女性在这方面表现得更充分,表情和肢体语言都特别微妙,也很唯美,画起来难度很大。我喜欢向自己挑战。这些东西最后就成了我绘画的内容,形式和内容结合起来了。
我把自己的绘画看成是独立的领域,我刻画的是内心世界,甚至不是我自己的,是虚拟的某种内心世界。我把它看成是至高无上的,我自己的情绪都不一定进入我的绘画。我想它是一种更高的东西,高于现实。
何多苓:享受着绘画、诗意以及边缘(4)
牛:你把创作和现实分得很开?
何:和我的生活也是分开的。
牛:整个90年代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呢?
何:当然是艺术品市场的形成。从绘画成为商品,一直到各种拍卖、收购,甚至有时候市场到了一种疯狂的地步。中国美术界也就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画家群体,追名逐利、风起云涌,同时也涌现了很多优秀的画家和作品。对我个人而言,倒是一个平静的过程。尽管自己在美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始终还是超然于潮流,还是以旁观者的心态在看时代。
参加展览,办个展,对我来说这不是必需的,只是个人绘画创作的一个副产品,不是我追逐的目标。我的目标还是画画,让自己身心愉快。
个人年代:特立独行的旁观者
牛:在早期你还有一个重要的作品《小翟》,主角就是翟永明。当时创作的背景是怎样的?
何:她给了我很多启发,她的形象也具有很大的表现力。《小翟》这幅画是和凉山的背景结合起来的,体现了当时她诗歌中强烈的意象主义色彩,也是我的一种形象化的表现。后来还画了一系列的画,我觉得都表现得比较成功。
牛:现在很多人把《小翟》的形象作为你画里面的一个特定的符号了,那种情绪、意象、女性的敏感。90年代后,你的作品是否也更多地着力于此,沿袭着这种细腻与敏感?
何:一直都是这样的。90年代末,我更是放弃了80年代那种严谨细致的画法,进入了一种比较流畅和写意的画法。我想那才是我真正的内心,把绘画和某种诗意、思想都结合起来了。
牛:有美术界人士评论你后来的画风融入了一些国画的思想。
何:那的确是我有意识地做的改变。虽然我没有画过国画,但能体会它的笔触,那种下笔的流动感,它不像西画是一笔笔摆上去的,它是在笔的流动中产生很多变化。我想真正把中国元素融进去,而不是像90年代初是找一些中国符号加上去。这更多的是融入了中国画的精神和文化。我比较满意这种改变。
牛:反过来我们再看时代的进程,我们是不是从最早的那种盲目崇洋到回归中华民族一些本真的东西,再对中国和西方作一个比较好的结合?
何:其实油画的民族化也喊了很多年了,但往往只是用油画来画中国的题材。但我现在才发现,对一个民族而言,它的精神是深入骨髓的,像基因一样。我想这种中国精神,无论用什么材料和手法,它都能表现出来,都具有强烈的民族特征。这才是真正的油画的民族化。对我来说,认识到这点是很大的进步,也等于进入了一个更高级的阶段。
以前觉得西画的三维透视很精致,而写意的国画感觉很潦草,很“水”,现在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牛:你说过“技巧即思想”,怎么理解?
何:把绘画的过程、绘画的技巧以及你要表达的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当绘画完成的时候,你要表达的东西也就出来了。从某种程度来说,技巧本身就是思想。我写那篇文章的时候,引用了韩东的一句话:“诗歌到语言为止。”我觉得绘画也是到技巧为止。
其实中国的文人画,都是这样子的。它用寥寥数笔,就表达出了自己的东西。这也是中国画和西画很大的区别。
牛:去年,你和翟永明到了墨西哥,后来创作了一幅《小翟和龙舌兰——向弗里达?卡洛致敬》,和以前那幅《小翟》构成了一个奇妙的循环,有人评论说这是对以前的回忆。这是怎样一种感觉?
何:这个过程很有意思。从墨西哥回来我就构思了这幅画。以前我虽然没去过墨西哥,但一直喜欢它的文化和风土人情,对它的建筑和音乐也很有兴趣。小翟本人是弗里达?卡洛的崇拜者,很狂热。她看了很多与弗里达有关的资料,纪念馆、故居等等。我想以墨西哥的符号,表现出小翟这么多年的变化,以及她对弗里达的狂热。从某种程度来说,这幅画又恢复了我80年代象征主义的风格——墨西哥的龙舌兰、弗里达的玩偶,与小翟的形象相互穿透,有一点回归的意味。
牛:你是一个怀旧的人吗?
何:准确地说,不是。就像以前的知青生活,当时觉得很融入,但要让我现在再回去,恐怕不行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即使现在回去画写生,故地重游,但都不一样了。我的世界还是在向前走的。就像这次汶川大地震,不可能不在画布上留下痕迹。这就是我下一阶段的任务了。新闻和照片也只能表现部分,我到了灾区现场,看到了生存、生命和希望,想以自己的方式表达这些感受。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何多苓:享受着绘画、诗意以及边缘(5)
牛:从90年代末期至今,随着中国加入WTO,整个国家的国际化进程明显加快了步伐。中国画家与世界的交流更频繁了,中国艺术界也受到了更多的关注。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再也无法“独善其身”,必须与世界融为一体?
何:对我自己来说,影响不大。但对中国艺术界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它已经是国际艺术界的一部分,有独特的地位,受到了强烈关注。这种关注缘于对迅速崛起的中国的兴趣。我一样也旁观着这一切,保持信息上的同步。
牛:就成都而言,前几年影响比较大的事件是2000年搞的成都双年展,这在成都是第一次。应该说这之后,成都的装置艺术、行为艺术以及其他类型的艺术都逐渐增加,传统的绘画艺术的空间是否受到了挤压?
何:这肯定对架上艺术形成了大的冲击。但我想,对中国人来说,绘画还是主要的艺术形式,虽然装置、行为、影像在西方成为主流,但中国的绘画仍然占有统治地位,这可能和含蓄的文化传统有关。我觉得架上绘画在中国还会长期存在并且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牛:最近几年,国内的很多画家都着重在表现自己的“符号”。比如某某一直画一种类型,很执著地画,最后这种类型的画成了自己的标志。你怎么看待这种“符号”?
何:很多画家用符号化的特征,其实是为了巩固自己在艺术界的地位,让其他人接受自己,最后成为个人的标志。但对我来说,十年如一日地重复,我受不了。到一定阶段我一定会转变。画家既需要重复自己,更需要打破自己的重复。我是以年为周期。
牛:符号化的特征和现在的商品经济时代有关吗?
何:当然有关。艺术类的商品也必须有自己的“标签”,特别是艺术家靠它成名后,更离不开它。其他人也不会模仿。艺术商品化的时代,不管是符号还是炒作,都是必然存在的部分,很正常。而且有的艺术作品拍卖出了高价,说明了商业化的深入。当然,我的作品还没有到炒作的地步,更多的是被别人收藏。
牛:商业化已经完全渗透到了艺术领域,连画家的个人形象也受到了商业化的影响,现在甚至不容易看到画家留长发、衣衫褴褛、满身油彩的形象了。商业化是否有过度的嫌疑?是否会影响到画家本身的艺术创作?
何:现在画家的主流标志是光头。(笑)而且的确也不会看到过去那种穷困潦倒的画家了,都穿得很干净,像雅皮士或者白领。中国的艺术家跟世界也接轨了,不再边缘化了,成为世界艺术市场的一部分。但高速发展带来的急功近利,还是让他们有别于西方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家。西方艺术家不论是外形还是生活方式都和商人有很大的区别,个人姿态上也会远离商业炒作,即使很有钱,也愿意过一种清贫的生活,和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在中国,大家更愿意合流。西方艺术家在社会中还是一个另类的阶层,身份感是很强的;中国艺术家已经进入了精英阶层,和其他行业的精英人士混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已经没有真正的艺术家群体了,都是艺术的生产者。这就是中国艺术界的一种现状。你要说商业化对中国艺术家带来的影响,在现在尤其明显。说白点,中国人是穷怕了。
牛:矫枉过正?
何:对。现在北京某些画家开的车,恐怕比有的房地产小老板的车都好,就是一种攀比心态。我只是旁观着这一切。对自己而言,我的定位很清楚——一个画家,画画的。我不是商人,也当不来商人,也不会理财。骨子里面是很传统的中国艺术家,甚至在社会上也是处于比较边缘的地位。我很享受这种边缘,决不愿意进入所谓的“主流”。
⊙
采访手记
朋友们都叫他何多。
认识何多,最早源于他那幅著名的照片:穿着一件简单的皮夹克,何多坐在画室半高的凳子上,全身很放松,但眉宇之间透射出洞察世事的睿智,从容不迫。我以为照片好,不是因为拍得好,是因为人物本身有神。拍得好不好,在于你抓得准不准。就像肖全说的,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何多成名很早,他上世纪80年代初从川美毕业后,就已经成为无数艺术青年的偶像。如果按现在的“粉丝”标准来看,他的“粉丝”遍天下。
翟永明开了白夜酒吧后,那里便成为成都文化人、艺术家的据点。翟永明有很多朋友,何多有很多朋友,他们的朋友彼此也是朋友。在白夜我多次遇到何多,有时候聊一下,有时候喝杯酒,但都没有深谈。
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中国发生巨变的三十年。时代是有烙印的,时代也会留下伤痕,但时代同时创造着英雄。
何多说,他们那个年代就是产生英雄的年代。不管在美术界、文学界,还是电影界,只要你站对了位置,成功是很自然的事。而现代,因为太多元、太自我,信息太泛滥,只能是个人的年代。
与何多交谈时,白夜没有其他客人。何多甚至叫酒吧的小弟把音乐关了。他喝冰水,我喝花茶。
三十年,从下乡知青到美术大师,何多始终把自己定位为旁观者。绘画立足于观察,而他以为,现代的很多画家太热衷于参与。旁观者的姿态是冷静的,超然的,不太容易为潮流所动,但也不拒绝新鲜。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汇来总结,那便是——特立独行。
何多一直执著于诗意的绘画。无论是在大凉山的草坡,还是在墨西哥的荒城,都无视物质的匮乏或都市的烦嚣。他一直纠缠在画与诗的笔触中,从头到尾。
交谈中,我也就一直把他当成魏晋时代的某个画家,无视着周围的存在。
何多说起《春风已经苏醒》《青春》以及《青春2007》时,我不断地想起《恋曲1980》《恋曲1990》以及罗大佑。
诗意一直存在。
诗意仍然栖居在何多的画中。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何农:潮里潮外三十年(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