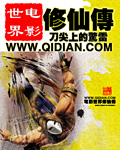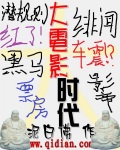低俗电影-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由于温氏兄弟既是制片又是导演,没有人敢说“不”字。当时也被列入制片人名单的布鲁尔回忆道:“对他们来说,倾听别人的意见真是太难了。‘但是,如果你执意如此,花你自己的钱好了。我们没有这方面的预算。’他们常常这样说,‘我不在乎,我不在乎从其他地方拿钱来!’但事实上根本没有其他资金来源。”西尔弗继续说:“谁也不知道预算是什么。其实根本就没有预算。完全是一团糟。即便到今天也说不上那部电影最终花了多少钱。如果说投入了800万,我一点也不惊奇。数周时间就开销几百万。”
影片投资公司派戴维·科达(David Korda)到片场以示警告,科达是导过1939年版的《四根羽毛》(The Four Feather)的导演祖尔丹·科达(Zoltan Korda)的儿子,乃著名的英国电影世家子弟。其间,J&M公司派前联美公司主管克里斯·曼凯维茨(Chris Mankiewicz)到这列逃亡列车的轨道前方拦截。曼凯维茨跟科达一样生于电影世家。他父亲是乔·曼凯维茨(Joe Mankiewicz,即约瑟夫·曼凯维茨[Joseph L。 Mankiewicz]——中文版编者注),执导过经典影片《关于伊芙的一切》(All About Eve,又译《慧星美人》——中文版编者注),而他的叔父赫尔曼·J(Herman J)则担任过《公民凯恩》(Citizen Kane)的编剧。“那是在迪克西维尔的一个见面会上,”曼凯维茨回忆道,“两个人中充当奥托·普雷明格(Otto Preminger)的哈维,这个喜欢咆哮和尖叫的家伙与鲍勃,这位顽固不化的家伙,谁也不知道该如何拍这部影片,但谁也不肯承认这一点。从这两个粗鄙的、来自布法罗的野蛮人身上看不出任何导演的才华。他们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干。倒是那种极端缓慢的生产速度和惊人的犹豫不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是一部剧本完全经不起推敲的影片,是一笔可怕、乏味的搞笑买卖。温氏兄弟要导弗兰克·卡普拉式喜剧,完全没门。我认为他们属于假冒内行的骗子。我不相信谁会给这种人投钱来拍电影。在那个年代,作为客户他们算是很残忍的了。每次哈维碰上我都要戏弄一番。再也没有什么比一场温斯坦式的嘲弄更让人愤怒不堪的了。他非常无情。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很像迈克·泰森(Mike Tyson),仿佛他就等着比赛的铃声响起好进行一番搏斗一般,大家都会凝神屏息,心想他会把对手捏得粉碎。我从来没有碰到过像他这样牲口般强硬的人。”
美国制造 1989(16)
“印象中哈维对电影也没什么特别的兴趣。他对电影的历史或者自己推崇的电影什么也说不上来。”曼凯维茨接着说,“可以想像得出,他在科达或曼凯维茨家人旁边永远不会问:‘给我讲点你爸爸或叔叔的事情吧。’我认为他对戴维·科达家族或者我们家的背景一无所知。我从小就认识许多伟大的编剧。他们身上散发出一种诗人或者作家的气质,有一种艺术情怀。你永远无法把哈维跟缪斯联系在一起。不管他是去拍电影、做面包或者生产枪械零部件,在他眼中这一切都不过是一种商品,是为了满足一种雄心勃勃的感觉。他也不过借此找口饭吃或者想发一笔横财而已。”
影片的拍摄工作一拖再拖,计划封镜的日期已经过了几天、几周,直到48天以后,电影投资公司要求在1984年11月10日封镜。据马丁·刘易斯说,温氏兄弟知道电影拍得不好:“他们想拍得更好一些。但他们把工夫都下在音响上了。他们发动了天主教区和犹太人区的热心者来帮忙。他们找到了汤森,皮特·汤森!从他那里搞到一首Life to Life的歌曲。他们还搞到菲·科琳斯的一首歌,虽然是从专辑里挑出来的,但那首歌本身并不坏。这两个家伙还不满足。他们还想讨好更老的人群,于是又找到了彼得·弗兰普顿(Peter Frampton)。他们还想讨好非裔美国人,于是又找到斯莱兹姐妹组合(Sister Sledge)。他们覆盖了人类所知的几乎他妈所有的人群统计样本。他们献出歌曲,完全是因为受到无情的魅惑、强迫和哄骗。‘就请帮我们一个忙吧,我们拍了一部电影,需要你帮一把。’他们在这方面的创造性本领远在做导演之上,但你不得不佩服这点。如果对方不肯答应,他们是不会走的。他们就像终结者,绝不轻易罢休。”
哈维把罗伯特·纽曼和他在布法罗时代的伙伴吉姆·多伊尔(Jim Doyle)留在纽约照看生意。但是;少了温氏兄弟的悉心关照,工作干得很艰难,尤其由于剪辑工作一直拖到第二年,《见者有份》又在消耗生命资源,更不用提现金了。布鲁尔说:“《见者有份》绝对削弱了米拉麦克斯的财力,使它陷入捉襟见肘的境地。当时的形势极其严峻可怕。”刘易斯字斟句酌地补充说:“他们一心想把《见者有份》做成功的激情跟这部影片的质量完全不成比例,比他们跟我的关系还要紧张得多。我没有感觉到灼热,而是一种伤害。当你打算举办一个聚会,每个人都邀请到了,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就绪,这时,你会坐下来说:‘可以了,只能如此了。’但温氏兄弟却不会就此罢休。他们不会停下来。如果要取得成功,那必须是大获成功才行。他们一直在追逐那种成功。”
也许是其音轨的缘故,环球公司在弗兰克·普赖斯(Frank Price)王朝日渐式微的日子里捡起这部影片,然后又随便地将其扔掉。普赖斯的继任汤姆·波拉克(Tom Pollock)说:“它的命运就像哈维处理的其他许许多多影片一样。”刘易斯接着说:“恐怕只有傻瓜才会说这部影片有多了不起,环球愚弄了我们一把。我们要再拍一部。于是就有了《见者有份2》。然而他们却说:‘我们不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我们得寻找适合自己的路子。’他们的特长在于,他们懂电影,对电影满怀激情,可以把电影推向市场。他们一直走那条路线。”
哈维和鲍勃回到米拉麦克斯,但公司已经面目皆非。米拉麦克斯为《见者有份》付出惨痛的代价。正如为温氏兄弟剪预告片的埃德·格拉斯(Ed Glass)所说:“那部影片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般打个不停,拍摄、剪辑、补拍新戏、又重新剪辑。经历数不清的咆哮和叫骂后温氏兄弟互相打得不可开交。它几乎伤害了每个接触过这部影片的人。”最后,公司原班人马逐渐凋散。据多伊尔回忆:“影片发行后过了几天或者几周,大家一个接一个离去。哈维和鲍勃对这部影片的失败十分恼火和失望。毕竟他们也曾经为之付出过辛勤劳作,但是那段时间确实太恐怖了。”从高中时就跟哈维相识的布鲁尔走了。刘易斯也走了。多伊尔接着说:“纽曼也决定不再介入,他也走了。我经常听到他们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鲍勃这样说,哈维那样干,我真受不了,吉米,我想走了。’现在只剩下我了。其他人也愤愤不平。于是我说:‘我也不想干了。’”米拉麦克斯飞速上升的第一阶段就这样谢幕了。
美国制造 1989(17)
《见者有份》溃败后,温氏兄弟又开始发动这驾马车。他们推出的第一举措是补充公司已经所剩无几的员工队伍。温氏兄弟已经穷得雇不起有经验的员工,他们只好聘用年轻、廉价、从大街上随便抓来或者刚出大学校门的毛孩子。温氏兄弟牢记刘易斯的教导,确保要笼络到一批媒体人士,至少达到公司人员规模的两倍。他们是闪电奇兵,是海军陆战队,是冲锋陷阵和引发舆论促销电影的首要力量。一旦打开热闹局面,广告费就会随之而来,先是从本地开始,如果电影流行起来,广告效应就会遍及全国。作为一线力量,他们的压力很大,而且必然会释缓那种压力。这些主要是女性的群体被称为“独怒者”(Furies)。
第二项措施是找到一个新的罗伯特·纽曼撑起发行部。在纽约城独立电影的最高展映地丹·塔尔博特(Dan Talbot)的林肯广场剧院的后排,在黑暗中,鲍勃来到宾厄姆·雷身边,问他是否有意干这份差事。雷拒绝了鲍勃,推荐了杰夫·利普斯基的小兄弟马克。马克对米拉麦克斯不太了解,只是知道这个公司由两个疯狂的兄弟经营着。他回忆道:“我给在生意中认识的每个人打电话,征求意见,我打电话的人里没有一个不说:‘你干什么都行,千万别给他们打工。’”但当鲍勃提出让他干这份差事时,他接受了。
没进去多久,利普斯基就发现米拉麦克斯已陷入绝望的峡谷。他回忆道:“我们出不起钱,哪怕连一家纽约的放映室都进不去。我就曾被一家影院这样拒绝过:‘带一张支票再来。’”负责后期制作的斯图尔特·伯金(Stuart Burkin)补充道:“如果你说在米拉麦克斯工作,人家就会关上门。当你想预定一个舞台,或者找个演员来配音,你只有对人家说:‘我们需要回去重新录制一下你的声音,但是我们出不起钱。’‘你是谁?米拉麦克斯?噢,哈维·温斯坦还欠着我的钱呢!’”而且,温氏兄弟对于企业经营一窍不通。“回电话简直就像一场噩梦。”利普斯基说,“温氏兄弟不让员工做应该做的工作。大多数人在做着同一件事,这些事被反复做来做去。他们如果肯花500美元修一门邮件管理课的话,收入一夜间就会成倍增长。”两年后,他们聘请马蒂·蔡德曼(Marty Zeidman)负责发行工作,也就是向电影院推销影片。他妻子曾经在那里短暂工作过,她发现,办公室一张桌子上堆满了没有拆封的信件,里面装满支票。据她回忆:“那些东西在那里一堆就是数月,甚至也没有人拆看邮件。”
同年,即1986年,米拉麦克斯招来伊芙·奇尔顿(Eve Chilton),这是一个来自老派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新教徒(WASP,即美国的主流阶层——中文版编者注)家庭的金发女郎,在玛莎葡萄园(Martha's Vineyard)的West Chop有一幢别墅。伊芙相当迷人,形象无可挑剔,脸颊一侧有一小块葡萄酒色的胎记,略微破坏了一点相貌。她当了哈维的新助手,哈维一下子就陷入情网。据利普斯基回忆:“大概有两个星期或者更长时间,我们一走进他的房间谈工作时就能看到桌上有一打的玫瑰,于是我们不得不当面对他说:‘你不能这样,这里是办公室,不是你的私人性爱乐园。’他很快就带上伊芙参加威尼斯电影节或者某个欧洲营销会场,从那时起他们就形影不离了,犹如一道既强烈又迅捷的闪电。”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米拉麦克斯这个猪窝里,奇尔顿完全出污泥而不染,大家都很喜欢她,虽然她羞怯、安静、保守,不允许任何人靠近她。她并不利用与哈维的关系,这点大家很欣赏,但并不因此对他们的关系就没有批评之词。像伊芙这样漂亮的女人到底看上哈维这样一个男人什么呢?谁都感到不解。大家同样不解的是他为她魂不守舍。似乎脸上那个缺点使她更为人性化,让她更容易接近,给了哈维一种控制她的可能。大家背地里称这对夫妇为美女与野兽。
相信被哈维招来负责购片工作、从小就在北卡罗莱纳州长大的南方女孩艾丽森·布兰特利(Alison Brantley)能够理解。“我想他们是真心相爱的。她遇到哈维的时候,后者正处于艰难奋斗的时候,完全是一个无名之辈。哈维身上的某种东西打动了伊芙。哈维有一种内在美。”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能体会到那种气质。布兰特利这样描述:“如果你走进哈维的办公室,还感觉不出他在想方设法地压榨你,你就是个傻瓜。而这正是他魅力的一部分,也是伊芙喜欢他的一点。”
美国制造 1989(18)
他们的关系在如火如荼地发展着,哈维不断提携伊芙,派她负责儿童部的工作。最后,哈维和伊芙于1970年代在东岸一个时髦的俱乐部举行了婚礼,随即就去圣巴特()度蜜月了。
奇尔顿是帮助哈维从他成长的皇后区那个小地方脱颖出的第一个阶梯,新招聘来的人员中似乎映射着温氏兄弟试图给米拉麦克斯打上某种阶层标志的欲望。除了布兰特利,温氏兄弟还招来特丽·霍温(Trea Hoving)进入采购部。她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馆长汤姆·霍温(Tom Hoving)的女儿。布兰特利本人来自格兰纳达(Granada),那是一家很优秀的英国制片公司。她回忆道:“我的背景跟他们截然不同,我甚至觉得自己像是走进了原始丛林。那里有许多狮子,我正好就是他们想吃掉的动物。但是,从见到哈维的那刻,我就爱上了他。我很喜欢阿兰·科尔诺(Alain Corneau)那部叫《印度小夜曲》(Indian Nocturne)的影片。哈维放映完这部影片后没有冲我叫骂‘你疯了吗?’之类的话,而是说:‘你知道,特丽,有时你喜欢上一部电影,这就够了。不要害怕运用自己的直觉,也不要总想什么都正确。正因为这样我们才需要一个团队,我们才要讨论它。’他鼓舞了我。我从不害怕说出自己真正的想法,因为我知道,他付给我薪水想得到的就是这个。无论他怎样威胁我,都不会阻止我。”
1986年5月,哈维和鲍勃赴戛纳参加电影节。在派迪特·卡尔顿(Pedit Calton)的酒吧,哈维跟一个名叫尼克·鲍威尔(Nik Powell)的高大、蓬头垢面的电影小子无意中交谈起来。鲍威尔跟他的合伙人史蒂夫·伍利(Steve Woolley)负责经营皇宫影业公司(Palace Pictures)。伍利很聪明,是个长着一副娃娃脸的年轻人,形象不错,把褐色的头发扎在脑后。这家公司比米拉麦克斯还像米拉麦克斯,完全没有固定目标,什么都想尝试。伍利和鲍威尔在电影鉴赏方面目光犀利,颇有天分,在1980年代为英国发行公司挑送了大批形形色色的好影片,比如《街童》(Pixote)、《恶魔之死》(The Evil Dead)、《首席女主角》(Diva)、《血迷宫》、《圣诞节快乐,劳伦斯先生》(Merry Christmas )、《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