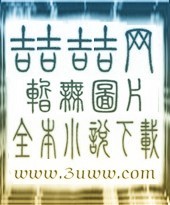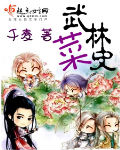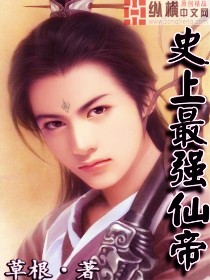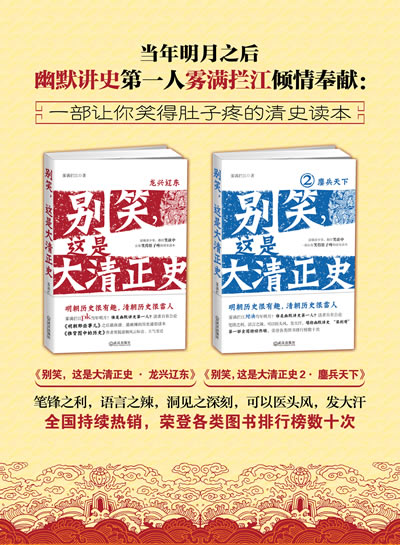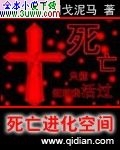首富进化史-第1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有情,有爱,我的情和爱,在我的家乡,根蒂那么深刻。我的家乡说不上水肥土美牛羊壮,可它辽远,旷达,阳光!哪像了这里,睁眼是山,闭眼是山,起点是山,终点是山,又冷又硬……
他的最后一封信,只有三两句:你以为像你这样的,户口迁移过来了,也参加中考了,考分也够高了,然后你就可以被顺利录取飞黄腾达了?错,只要有人去检举,你的成绩就等于零。他甚至把红姐写进了信里:包括你贵阳学校的同学,一样,只要一封信,她就哪里来哪里回。
我决定哪里来哪里回了。红姐二姐周校长,他们要留我,可是我不能留我!
没给二姐说。第三天我就起身了。
眼镜怎么就知道了我要走呢?尹老师告诉他的?
我走的那天是个星期六,学校里好像只有他和我两个人。
一身白衣白裤(那年兴那样穿),坐楼梯间,怀抱吉他,忧郁着看我收拾衣物,这个印象很深,一直弹《站台》,一直弹。
当我经过他时,他干脆把腿支起,抬眼望我,说,你还转来吗?他居然泪下了。
怎么不孤独?怎么不孤独得下泪呢?眼镜,最起码他是从县城的师范校出来的,来这里,明晃晃的闭塞,冷清,他也就十*岁,或者二十出头吧,但他示好的方式,却是如此的幼稚,可叹,可怜。
松花至遵义客车启动的那刻,我就知道,我是转不去了,像二姐的话:回不去了。觉后来周校长和红姐和二姐都失望了,我觉得对不起,伤害了他们,对自己的话没能负责!
我的中考移民,就这样从开始到结束,为时两个月,短暂而漫长。
回到家里,母亲自是欣喜的无语凝噎,她其实已经后悔让我去了遵义。父亲坐地坝埋头裹叶子烟。除了吃睡,我几近自闭,轻松不起来,想起前尘后世,路在何方。
次年三月,阴差阳错或说机缘巧合,我入读了县凌云职业中学幼教专业,1992年7月顺利毕业,从此与幼教结下了一生的缘分。2000年9月,我开办了属于自己的幼儿园。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塞林格:不仅仅是青春(1)
塞林格:不仅仅是青春
子默
他是一个拒绝公众的作家,这使得在他去世之际,悼念文字或追思文字都显得不合时宜,而此时若再拿来他的作品做一二三条的分析综述,更要成为“守望者”老霍尔顿口口声声的“混账东西”。
对塞林格而言,一条讣闻便已足够。
然而,绝少有哪个作家像塞林格一样,他的离去可以让异国他乡的那些已在而立之年左右逡巡的人,被一种确实的忧伤情绪招惹--这与青春有关,又固执地浅浅呢喃在成人世界。
时代观察者
塞林格小说的强烈情绪和肆无忌惮的语言风格,常会让人误以为这只是富二代青春期特有的聒噪和张扬。然而,完全个人化的世界不会具有文字传播所必需的公共性。塞林格,富裕犹太商人的儿子,母亲生于苏格兰,这组成了美国社会里的一个标准移民中产家庭。少年时期他辗转退学转学于数所学校,二十三岁参军,并在军队服役五年之久,这些经历都成为塞林格日后创作中不竭的题材与体验,也使得塞林格成为一个时代的溺入者与观察者。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社会的诸多方面正处于时而平缓时而激进的变革之中。经济上,大萧条的阴影得以摆脱,军工生产退居其次,消费社会的形态初步形成。《美国现役陆军人员*法案》(G。I。Bill of Rights)的通过,使得大批刚刚退役回来的年轻人获得大学学士学位,从而享有了经济与社会地位上的优势。在物质繁荣、政治高压的环境中,美国的青年一代表现出广泛的“从众”趋势,他们往往被称为“沉默的一代”,美国的当代史学家也常因此将美国的五十年代称为“静寂的五十年代”或“怯懦的五十年代”。
战争的阴影依然存在,原子弹的发射和冷战对峙为这个欢乐的国度蒙上一层挥之不去的末世薄纱,发生在奥斯维辛和广岛上的惨剧,使这个时代的作家们更加关注文明的局限而非希望,更加关注人类内在混乱危机四伏的精神状况。美国其时的文化基调成为存在主义和危机神学,罪恶感与荒诞感取代约翰·杜威(John Dewey)式的实用主义的社会希望以及对改革的信奉。《梦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和《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受到追捧,美国似乎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成功,文化界和思想界却比任何时期都更对它感到不满,“真正的艺术家与美国人的粗俗情趣格格不入,他们追求欧洲式的复杂性与微妙性,他们在国内往往感到被人视作异己。”
五十年代由此催生了另一个关键词:焦虑,一种新的青年文化也随之出现。在小说创作领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盛行的社会题材小说被具有特定样式的寓言小说取代,它们向读者展示狂人、冷眼旁观者、不合时宜的人以及原始派艺术等各种人物形象。疏远的情感和激进的锋芒并存,这一切又自然地与垮掉派诗人、抽象派画家、爵士音乐家以及摇滚歌手联系起来,美国文化中敢于说“不”的形象系列跃然而出。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在《欲望号街车》(A Streetcar Named Desire,1951)与《野性的一群》(The Wild One,1953)中以一系列危险的原始人面貌示人的形象,引导了令老一辈美国人深感恐惧的肇事者形象风潮,成为那个时代的青年偶像。父母成为压迫者,颂歌唱歌反叛的青年一代,damn和shit成为年轻人的必备口头语,时代改变了。
塞林格:不仅仅是青春(2)
对时代气息的敏感,被塞林格捕捉在小说语言中,它们是对非正式的、口语化的美国青少年语言习惯的真实展现,粗俗化、俚语化,缺乏准确性又不失创造性。人物张嘴闭口都是“damn”、“goddamn”(他妈的)、“hell”(该死的),曾有统计,《麦田里的守望者》总字数为约7 万3 千字,诅咒语、粗俗语则共有796个。而附着语如“and all”、“or something”、“or anything”等的大量运用,使小说充满了扑面而来的青春无谓气息:“I thought I was going to choke to death or something。”“Then I finished buttoning my coat and all。”
这使得《麦田里的守望者》于1951 年发表后, 被认为充满亵渎神灵、猥琐粗陋的语言,并一度被提议列为禁书。这不能阻止该书的迅速传播--出版后在半个月内先后印刷了五次,甚至到1989 年它仍高居畅销书榜首。以至有“如果塞林格不能算是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作家, 那么他一定是被阅读得最多的经典作家”之说,以至有人认为要想了解那一时期的美国历史和文化,《麦田里的守望者》是一本必读书。
极端的纯洁
迪克斯坦曾谈到塞林格小说那种淡淡的犹太悲喜剧人物痕迹:“他(霍尔顿)的心中充满了焦虑,而他又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他的不幸是这双重因素混合在一起所造成的,他的失败证明了他品质的高尚,而正是他的失败使他与众不同,有一种特殊的命运。”
虽然塞林格不像索尔·贝娄或菲利普·罗斯这样大名鼎鼎的犹太身份作家那样,使人一眼便可看出某种民族的精神风格,但此书在同时代那些同样充满着焦躁气质的诸多作品中脱颖而出,并跻身于经典行列,与塞氏那颇具犹太气质的忧郁和精神向度是分不开的。
他毫无疑问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反正统文化运动的重要旗帜,但他的文化取向却并非性或毒品,他的创作气质也并非那种美国式的强健奔突的生命力,而是力图保留精神的天真神话,由此最终走向内省,走向宗教。
这也在另一个层面上显示出,塞林格对美国式物质文化的鄙薄与反对,对中产规范社交礼仪的唾弃,远不仅仅是一个青春期孩童的毫无目的性的反抗,它来自于一个曾经热衷于传播教义的犹太家族,某种文化和精神的基因使他与这个大众文化泛滥、成功学流行于世的国度相疏离。他的内心深处一直为那种深邃的训诫所召唤,而他的身体却太过年轻也太过孱弱。
塞林格对宗教的态度是很有趣的。他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开始关注佛教,之后又转投罗摩克里希那的印度教,甚至还尝试过包括基督教科学教派和针灸、禁食、呕吐清洁法等等,但塞林格终其一生又始终是个无神论者。事实是,与其说塞林格努力做个宗教徒,或是尽可能让自己往形而上的路途上走去,不如说,某种恍惚但又能确实为人体验并确信的宗教性成为塞林格依托并抗拒“堕落”时代的依据。
与为反抗而反抗者们不同,塞林格的反叛从来都有着明确的指向性,他吁求真正诚实的道德,渴望真诚交心的相处,而不仅是千人一面的“见到你很高兴”,他信赖灵魂的纯洁和灵魂所能到达的深度--精神的升华与净化是塞林格一直追求的,这种理想化的浪漫主义碰壁之后,便成为强烈愤慨的反弹。
塞林格:不仅仅是青春(3)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成名以后的塞林格选择了隐居,主动将自己隔绝在公众视线以外,这也可以使我们理解塞林格在爱情婚姻中的态度:他似乎只喜欢与年轻女孩书信交往并恋爱,而据一个十八岁时与他同居过的情人回忆,分手多年后意外重逢,塞林格不仅立刻将她赶走,而且指责对方心中充满了“贪婪、渴求和攫取的欲望。”极端的纯洁,这是塞林格真正信奉的宗教,它不属于任何一个教派。
不仅仅是青春
但纯洁与英雄无关。
塞林格小说的流浪汉体例与人物塑造总令人想起美国文学史上另一位优秀的作家,马克·吐温,后者将赞美与观察世界的眼光毫无保留地送给哈克这个小男孩,这也成为美国小说中最早的“反英雄”形象。事实上,欧美文学中的英雄主义观念并非在某个时代遭遇突如其来的变故,自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时期以来,我们看到的不再是救民于水火的史诗英雄、悲剧英雄或者带有东方色彩的集体主义英雄,相反,主人公们往往处于某种现实和精神的困境中,充当受难者和牺牲品,在窜动的生命火山口处徘徊。失败者和零余者大量涌现,这不仅是时代状况的转变,还是人类在自我探索认知过程中达到的一个更为审慎的阶段。
“亲爱的上帝,生活是地狱。”《为埃斯米而作》里正在接受情报部门训练的军人X,瞪着一位纳粹低级女军官在某本书的扉页上写下的这行字,“苦苦地抗拒着巨大的吸引力,不让自己为之所动。”接着,他在下面写道,“我认为因为不能去爱而受苦,这就是地狱。”作为一个曾奔赴二战前线的退役军人,塞林格曾对女儿说:“无论你活多久,人肉燃烧的味道都无法从你的鼻孔里消散。”而霍尔顿的出走、追寻和回归,在形式上或许正符合传统英雄模式的三阶段,在内容和实质上却是对英雄原型的彻底解构。在霍尔顿的升级版中,格拉斯家族的早慧孩子西摩,带着战争的烙印,和小女孩西比尔进行一番颇有意蕴的交谈后,返回旅馆,看着熟睡中的女友,开枪自杀。一个曾经的孩子死了,另一个孩子继续生活。
但我们能要求塞林格除了守望或捉住麦田中嬉戏的孩子外,再给我们开出怎样的生活希望清单吗?事实是,作家不需要充当导师,不需要给出答案,他只能让那些需要的心灵不再孤独。而生活的路将继续着,在最终的意义上,我们都是互不相干的个人,去面对最后最真的叩问。
正是在与老霍尔顿们分离若干年后,我才渐渐明白,这世界上有一些人,他们总是可以从目中所及的石头缝中栽培出野草来,并以之为最重要的精神食粮。总有一些人,他们冷漠而愤世,他们甚至选择离群索居,因为他们坚信大多数交流是无效而不必要的。他们热爱极致,热爱灵魂的冒险。他们知道这世界上也许存在所谓健全的理智与美好的生活,但他更愿意唠唠叨叨谈论他没完没了的不满。
也许,只有这般精神的不满不满和更多不满,方能使人类在自我认知的世界艰难前行,在灵魂的危险地带踟蹰或纵身而入,也摸索出了我们所能达到的精神勇气。这种勇气,不应当仅仅属于青春。 ■
(作者系文学博士,供职于浙江文化艺术研究院)
1961年9月,塞林格在家里。他常年隐居山中。图/CFP
201年1月27日,91岁的塞林格去世。
迄今,《麦田守望者》的全球发行量超过6000万册。
。 想看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