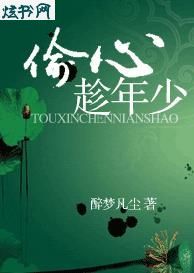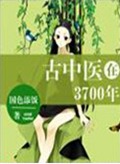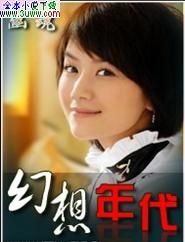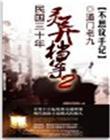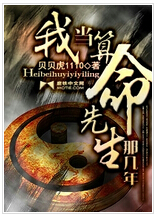我这九十年-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928年农历四月八日,父亲送济世到了浮山公学。当月二十七日他给母亲信说:“我送济孙往桐校,系本月初七由汉口动身,初八日即抵安庆。将济孙安置妥当后,当即就近至上海一游,在群士先生处住七八日。”信里所说“群士先生”,是刘积学,号群士。当时刚卸任北伐军河南宣抚使职务,寓居上海。
那以后,二姐知道济世在浮山受到房师亮照顾,很是稳妥,便跟房师亮联系,受邀前往。当时在四川南溪,以前与孙炳文为敌的豪绅,正勾结地方驻军,想加害二姐。二姐带着维世、名世,从南溪到武汉,接上宁世,同往浮山。房师亮很照顾烈士遗孀和孩子们,他父亲房轶五先生安排我二姐做了图书馆管理员和教师,并安排了孩子们的学习。一年后,房师亮携妻子同赴德国再次留学,二姐和孩子们因此离开浮山,房师亮夫妇把她们护送到了上海。流亡欧洲的邓演达,来函拜托朋友照顾二姐母子。在朋友的帮助下,二姐出任明浚小学校长。后来几个孩子陆续都安排在开封、北京上了学,宁世还曾到日本去读大学。
邓演达回到上海被蒋介石杀害后,二姐回了河南。那之后,她很多时间都在开封或新蔡老家。1932年秋,她去北京办了一所“北辰中学”。她任校长,我三姐夫冯友兰为支持帮助她,出任董事长。除了他们俩,学校的教师和干部,都是邓演达生前建立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人。这所学校办在西单北前英子胡同里的一个小院内。二姐约请冯友兰和别的同事一起开会,谈她对办学的想法和意见。当时只办了一个初中班、一个高中班。校内很有*气氛,师生融洽。学生们因此很活跃,办演讲赛、学科讨论会,出墙报,成立班会、学生会,还编印校刊。因为学生少,收费又比较低,半年后就开支困难了。因经济来源不足,不得已学校停办了。
二姐任锐(任纬坤)的一生:发孙炳文未竟之志(5)
1935年,二姐从开封带着我和维世去上海,安排我们学了两个多月话剧。学完后,我们三人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一起回到开封。过几天,维世回北京上学去了,我和二姐留在开封,我在静宜女中读书。
秋季的一个星期日,二姐要带着我出门。我见她从行李里提出一只挺大的瓦罐。那瓦罐差不多一尺半高,尺来粗,封着口。见她把瓦罐抱在怀里,我问这是什么?二姐说:“这里面是你二姐夫浚明兄。”我很吃惊,这才知道,二姐把孙炳文的骨殖装殓在瓦罐里,从上海带到开封来了。现在她要让二姐夫入土为安。原来,我们这是要去安葬我的姐夫。
二姐只带着我一个人,抱着瓦罐,雇了辆人力车,出了开封城宋门。我们往东走,又向南拐,跨过陇海铁路,又穿过白塔村,再往南就到了一片叫做“四川义地”的墓地。二姐一路伤感地跟我说浚明兄,说他是共产党,是好人,让我别忘了杀害他的人。那时二姐生活艰苦,没有钱。孙炳文是四川人,二姐却无力送他回归故土,只好把他的骨殖埋到了不要钱的四川义地。在那里的一处边角之地,二姐请人给挖了个坑,不太大,但挺深的,将瓦罐埋葬进去,盖上了土,又堆起个小坟头,还立了一块很小的碑。二姐面对那块碑,跪了很久。我随着二姐,给孙炳文磕了头。
那块碑,只有一尺三寸高,七寸宽,比现在的一本杂志大不了多少。上面刻着:
孙炳文之墓
民国廿四年八月廿五立
1935年8月25日,是二姐带我在开封四川义地埋葬孙炳文骨殖的日子。如果这是农历,这天就是公历1935年9月22日。
我不知道二姐是怎样找到孙炳文遗骨的。有一种说法是,孙炳文有一个表兄——他姑母的孩子,叫欧阳竟文,当时在上海三友实业社工作。孙炳文遇害后,欧阳竟文安排人偷偷给埋葬在了一处叫“十四埔”的地方。从我二姐数年以后能带回遗骨——她确认无疑才会把丈夫带回开封安葬——来看,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可信的。因为,二姐曾随孙炳文在四川生活多年,与夫家亲戚多相熟识。而且,应该是有人指引,她才可找到并且辨识夫君遗骸。
那个四川义地,后来好像归入了开封烈士陵园的范围。如果是这样,如果没有过什么施工,孙炳文就一定还埋在那里。
从小,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二姐。那时我已经知道二姐夫是被蒋介石杀死的。二姐总悄悄跟我说共产党好,讲人人平等的道理和共产党实现*的理想,讲劳动神圣、年轻人应该能吃苦耐劳什么的,还嘱咐我别出去说。我那时知道她是共产党,也知道不能对别人说。那时,我在学校有个姓杨的同桌女生,很信任我,老悄悄跟我说,昨天什么地方又枪毙了共产党、共产党都是好人什么的。一天她红着眼圈小声告诉我,她有个表哥是共产党,昨天也被枪毙了,让我别跟别人说。那时候的政府呀,老杀共产党。
抗战爆发后,我随二姐参加了她组织的妇女救护队,在郑州帮助救护从前线下来的伤兵。在郑州时,开始二姐带我们全队女孩子住在刘积学家。刘积学也是新蔡县人,做过我父亲的学生,是清末举人、老同盟会员。北伐时,他做过河南宣抚使,后来当过河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他家院子大,房子多,住得下我们。过些天,二姐带我们搬到了另一个住处。有一天我们出去救护,赶上日本飞机轰炸。回来时一看,住的房子被炸塌了,没地方住了。刘积学听说后,非常着急,派人到处找我们。我知道了,就赶紧去他家。见到了我,他才放下心来。他让我坐下,跟我说了半天话。其中,他感慨地对我说:“你们姐妹几个都好啊!你们姐妹几个都好啊!”我们的救护队解散后,二姐就北上山西了。 。 想看书来
二姐任锐(任纬坤)的一生:发孙炳文未竟之志(6)
父亲送我到延安时,二姐和她的女儿维世已经在延安了。她们母女先在抗日军政大学同学,又在马列主义学院一起学习。母女同学,在延安一时传为佳话。大家都很尊敬她。于是,因为维世叫她“妈妈”,其他学员也就随着维世,叫她“妈妈同志”。
久别重逢,大家都很高兴。一段时间,宁世也在延安,我们经常见面。二姐的孩子都有才华,有能力,大家都喜欢他们。朱老总在1939年2月17日写给与他和孙炳文相熟的四川老友张从吾的信中说:“浚明亡后,其全家均能继续革命。孙泱即宁世现在我处工作,有父风,颇过之,母不及。济世在河南亦是干才。维世(女)亦聪明绝顶。后生可畏,革命必期成功就在此。浚明夫人任同志亦到延工作,特此告。”
后来二姐被派去四川工作,维世跟我一块儿,流着泪把她送上汽车。第二天维世就去苏联了。二姐先在壁山县的战时儿童保育会直属第五保育院工作,呕心沥血地照顾战争孤儿们,后来累病了,被调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图书馆工作。1939年12月3日二姐给我的信里说:“我因病已从保育院回到重庆来了。那里工作时间太多——工作每日十二时,夜间还得起来一两次,给孩子们盖被子——我经不起,所以病了。现在已痊愈,请勿念!”二姐信中还说:“兰(维世乳名)走了之后,一切东西你去收拾没有?尤其是那包文件太重要了,希望你替我保存起。我出来的时候,只带一床很薄的棉被,现在不够用,请你设法把那床厚而软的棉被托人带给我。交重庆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陆竟如转我。”
二姐离开了延安,维世又去了苏联,她们娘俩儿的东西都留下了。我那时没想着她们可能还会回延安来,结果把她们的东西都送人了。有人没被子,我就说这儿有,让人家拿走了。二姐写信让我给她带被子去,我拿不出来了。当年冬天二姐回来,仍没被子盖,笑着说我:“傻丫头,你没想想,我还得回来呢,我回来用什么?”二姐在重庆时,曾经把她的薄毛衣等好东西,托帅孟奇帅大姐带到延安给我,说我穿上薄毛衣演出,可以显得苗条。
二姐回延安后,是托人告诉我她回来了的。一天,一个同志对我说:“你姐姐回来了,叫你去呢。”我一听,喜出望外,赶紧跟院务处借了匹马,背个小红布书包,快马跑去看二姐。那时二姐住在北门外的一个招待所,见了面,特高兴。二姐让我把马拴在他们那儿的马槽,让我住在她那儿,说了一晚上话,第二天才回去。
我和二姐在延安时,父亲曾经给我们往延安寄过一次钱,三百元票子,我们俩一块儿给花了。那时洗衣服没有肥皂,大家都用淋下的炭灰水洗衣服。木炭的灰,泡在水里,泡出碱来,就可以洗。我们还用它刷牙洗头。父亲寄来钱,我们可高兴了。二姐给我买了肥皂、牙膏,还买了一块布,让我做了一条蓝裤子,穿上美得不得了。
二姐先在*部工作,后来调到边区政府。她参加革命早,资格老,是吃小灶的,但把面粉什么的都接济别人了。她自己一点东西都不留,永远都是给别人。那时一天两顿小米饭、野菜,一点儿油都没有。谁那里要是有一瓶子猪油,大家都过去抢着拌小米饭吃,觉得特别香。一次二姐带我去续范亭家做客,饭桌上的东西,在当时的延安,属于“吃好的”。我在延安很长时间吃不到“好的”,坐在这桌前,一下子吃到嗓子眼儿。那以后,二姐好几次带上我去做客,如在王家坪的滕代远同志家等等,每次,我都能吃到嗓子眼儿,痛痛快快地解回馋。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二姐任锐(任纬坤)的一生:发孙炳文未竟之志(7)
二姐在*部工作时,住在杨家岭,我常去。一天下午,我从乔儿沟走十几里路到了杨家岭,人家却告诉我二姐已经调到南门外边区政府去了。那时没电话,二姐没法儿通知我她换地方了。我又从杨家岭走十几里路到市场沟去找二姐。我老去二姐那儿,边区政府那院里住的董必武夫人何莲芝、谢觉哉夫人王定国,还有冯韧等几位大姐,也就熟了。尤其是天暖季节,我去时,常遇见她们在院中。那时何莲芝大姐养了只猪,在窑洞里哼哼唧唧进进出出的。她是长征到陕北的老红军,对人特别和气,见到我总是说:“你来玩儿嘛。”每次都是,“你来玩儿嘛。”过了几十年,“*”结束后,在北京八宝山举办孙维世告别仪式时,她也去了,见到我,还是说:“你来玩儿嘛。”她非常怀念我二姐,每次见到二姐的小女儿粤生,总会谈起我二姐,总会难过地落泪。
建国后,一次在北京广安门医院看病,忽然一个老太太叫我:“仍浚!”我一听,这是叫我的名字“任均”,是陕北口音。我不知道她是谁,问:“您是……?”她说:“你是仍浚。鄂(我,陕北音)是刘子丹婆姨。鄂认识你,你不认识鄂。在延安,你去看你二姐,鄂常看见你。鄂认识你。”我想起来,二姐当年指着一间窑洞给我说过,那里住的,是刘志丹的夫人。我和刘志丹婆姨在广安门医院聊了半天,她又跟着我到了我们家。那时我家在广安门内的一个四合院里。可那会儿我不懂得留人吃饭,聊了一会儿,就送她走了。
1945年秋,二姐的三子名世从国统区转到了延安,住在南门外边区政府他妈妈那儿。我每周都去那里,大家见面。那时,宁世去了东北,维世还在苏联,我和一达在延安平剧院。组织上为了照顾二姐身体不好,身边又没有孩子,就让名世留在延安工作。但二姐说不用,前方更需要人。名世便被派到牡丹江炮兵部队去了。
名世走前那几天,二姐牵肠挂肚,给他缝缝补补,没休息好。送走儿子,二姐就病倒了,一个人在窑洞里躺了好几天。她的心情很不平静。国家动荡,战事不宁,自己在颠沛中,拉扯大几个孩子,又舍家抛子,投身革命。身为母亲,哪能不时时挂牵骨肉?与小儿一别数载,相聚仅月余,却又命他去冲锋陷阵。母子情深,焉能割舍?何况这是最小的儿子。孩子此去山高水远,何日才能再聚膝下?二姐心绪起伏,写下一首诗:
送儿上前线
送儿上前线,气壮情亦怆。
五龄父罹难,家贫缺衣粮。
十四入行伍,母心常凄伤。
烽火遍华夏,音信两渺茫。
昔别儿尚幼,犹着童子装。
今日儿归来,长成父摸样。
相见泪沾襟,往事安能忘?
父志儿能继,辞母上前方。
二姐再没有见到小儿子。1946年秋,名世牺牲在东北战场。
那年,有一次我去找二姐,准备晚上一起看演出,碰上柯仲平同志去看我二姐。柯仲平是诗人,那时在陕北搞民众剧团,发展秦腔,还当过我们延安平剧院副院长。我们一起吃完饭后,二姐不想去看戏了。柯仲平却还想去。他为人热情,说:“我和鲁妹一道去哦。”二姐管我叫“六妹”,他便也叫我“六妹”,但他是南方口音,把“六妹”说成“鲁妹”。路上,他跟我提起,二姐了不起,他很佩服。他说,前些天梁漱溟到延安时,去看望我二姐,被二姐严厉批评了一通,说他“你对不起炳文,对不起共产党。”
二姐任锐(任纬坤)的一生:发孙炳文未竟之志(8)
民国初年,我二姐和梁漱溟都在报馆里,跟孙炳文一起办《民国报》。他们都是京津同盟会会员,孙炳文对他们很好。大家投身革命,一起奔*共和。梁漱溟用了一辈子的名字“漱溟”,就是我二姐夫孙炳文那时候给他起的笔名。后来社会变迁巨大,梁漱溟潜心佛学、儒学,搞乡村建设,渐自走向思想独立,孙炳文则与朱德、周恩来一起成为*重要干部。蒋介石清党时,把孙炳文抓住杀害了。二姐与梁漱溟,已经多年不见。1946年梁漱溟为国共和谈的事情,到延安劝和时,去看望了我二姐。他那次去延安,急着想出和谈成果,就主张让一让,不打仗,受一个政府领导。当时那种条件下,这使人觉得他是想让共产党放下武器,让出地盘。虽然他的出发点不一定是这样的。
当时跟二姐同住边区政府院里的冯韧大姐说,梁漱溟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