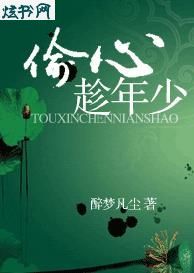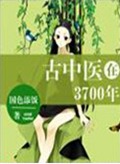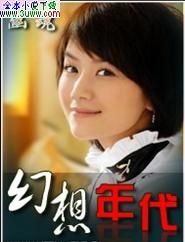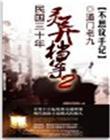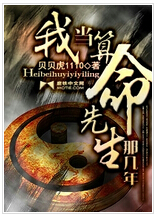我这九十年-第1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战内容的独幕话剧。那时,虽然我的戏剧知识很少,演得很一般,但我明确地开始追求话剧了。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话剧才能引领时代风气之先,才具有革命性。所以,到延安参加革命队伍后,我直接就进入鲁艺学话剧了。
不料,虽然不是我的本意,我却从1939年春天开始,到1949年初,一直从事延安的京剧工作,整整十年。
1。 在鲁艺戏剧系学话剧,却老去演京剧
1938年冬,我父亲任芝铭亲自送我到延安参加革命。孙维世建议我进入鲁艺。我父亲知道他的外孙女孙维世走的是话剧、电影的路子,搞的是新事物,也知道鲁艺那时候不设戏曲课程,便同意维世的意见,让我考进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第三期戏剧系学习,开始系统学习戏剧基本知识,学习话剧表演艺术。
那时,院长周扬给我们全院上大课,讲《艺术论》,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美术系的所有学生都来听。那会儿没有礼堂,所有人都在院子里黄土地上坐着,听他有声有色地讲课。周扬同志虽然是领导,但并不摆架子,见谁都打招呼,还好开个玩笑。我在大家眼里是个小女孩,在他那儿也不例外。1942年我离开鲁艺去了延安平剧院。过一年再回去时,我已经结婚怀孕大腹便便了。周扬同志看到我,笑说:“任均都要做母亲了啊?”我不是他以前看到的女孩子了。
后来, “*”后期,他不挨整了后,住在中组部招待所,我和王一达曾跟冯牧、戈扬、张梦庚等同志相约,去那儿看望他和他夫人苏灵扬。我跟戈扬是60年代在东北相熟的。她被打成右派后下放辽宁,60年代初到省作协工作。那时她上班的地方在张学良故居,我去她那儿时,见那房子很漂亮。后来大家都回北京了。80年代,我二儿子想调动工作时,单位不放,我跟戈扬说起,她去帮着问了,笑着跟我说:“这么好的干部,要是我也不放啊。”她和冯牧给帮了忙。一起去中组部招待所看望周扬同志时,“*”还没结束,但周扬和苏灵扬都很乐观,谈笑风生的。后来大家说,周扬同志是“*”前整人,“*”中挨整,“*”后大彻大悟了。我相信,他的乐观积极来自他的大彻大悟。一次在王府井东安市场里,我遇到周扬同志,他在等苏灵扬买东西。他问我:“一达回北京了吗?”我说还没有。他又开玩笑说:“王宝钏十八年,任均你多少年了?”说得我哈哈大笑。
在鲁艺戏剧系学话剧,却老去演京剧(2)
在延安,张庚同志是我们鲁艺戏剧系主任,给我们讲《戏剧概论》。除了课堂授课外,他要求我们阅读苏联经典名著,以提高艺术修养,如《安娜·卡列尼娜》、《复活》、《被开垦的处女地》等。鲁艺书少,大家你一本我一本换着看。那时,我跟戏剧系的同学们一起演过两个话剧。一个是崔嵬编导的独幕话剧《被蹂躏的女性》,由我主演,同台主要演员是王一达和柳岸。另一个是姚时晓导演的日本话剧《婴儿杀害》,我扮演警官的女儿,同台主要演员有黄灼和方深。我还曾参加排练曹禺话剧《雷雨》,扮演四凤。我那时是第一次系统学习戏剧理论,并尝试着与戏剧实践结合,所以,那个时期的学习,很有收获。张庚同志一直关心我们这些学生,到2003年一达去世时,他都九十多岁的老人了,还送来花篮,并自己打来电话安慰我,叫我节哀、保重身体等等,让我很感动。
我在鲁艺学的是话剧,但出乎自己意料的是,我演得多的,却是京剧。在戏剧系学习话剧期间,因为我有一些京剧演唱的基础——在老家时跟着唱片学了些,还曾在北京向刘凤林学了全部《鸿鸾禧》,所以,从1939年春天开始,参加了多次临时组织的京剧演出活动。最初参加演出的是传统戏《鸿鸾禧》的前两折,只演到“拜杆”。说是传统戏,但我们是穿着现代服装演出的,因为当时延安还没有戏箱(京剧演出的戏装、行头等),只能有什么就穿什么演。《鸿鸾禧》讲的是女孩金玉奴和她父亲讨饭资助一书生赶考,书生得中后忘恩负义的故事。我扮演金玉奴,同台主要演员是我们戏剧系的同学展宇和石畅。我第二出戏演的是说萧氏渔家父女不堪土豪勒索杀其全家的《打渔杀家》,阿甲主演肖恩,我扮演肖桂英,崔嵬演教师爷,同台主要演员还有石畅等。这个戏我们也是穿着现代服装演出的。这两个戏,本来都是古装传统戏,穿着现代服装演出,还拿腔拿调地唱念,不伦不类。尤其还要做传统戏曲程式动作,感到很别扭。
我到延安之前,延安已有少数懂得一些京剧的同志编演了为抗战服务的京剧现代戏。那时或由综合性表演团体演出,或临时抽调人员排演。在延安率先演出京剧的是西北战地服务团第二团,演出了现代戏《清明节》。鲁艺演出的第一个京剧现代戏,是为纪念抗战一周年,以传统戏《打渔杀家》为模子改写的《松花江上》,由阿甲和江青主演。虽是“旧瓶装新酒”,但比较成功。那时候创作现代戏,多是找一个传统戏为模子,把新内容往里套。鲁艺成立实验剧团后,主要是演出话剧,同时也演出了自己创作的京剧历史剧《松林恨》等戏。
在延安早期参加京剧工作的,有阿甲、张东川、李纶、王久晨、卜三、齐瑞棠、方华、罗合如、陶德康、任均、石畅、王一达、石天、陈冲、王铁夫、孟刚等同志。另外,崔嵬、朱丹、陈叔亮、华君武、刘炽以及其他一些同志也曾多次参加京剧演出活动。
。。
曾进鲁艺旧剧研究班,看到毛主席最爱古装戏(1)
最初大家都是业余参加京剧演出。1939年春夏之交,鲁艺成立了一个旧剧研究班,研究平剧——京剧,任务是研究京剧如何为抗战服务及其将来的发展前途。这是延安的第一个京剧组织,由少数懂些京剧的同志组成。最初,成员只有阿甲、罗合如、石畅、张东川、李纶、王久晨、方华和我,八个人。别的同志开玩笑说我们这八个人是“八格牙路”。后来陆续增加。最后也不过十几个人。那时曾进行了一些研究、创作,也在别人协助下组织过演出。但是力量薄弱,又有几个人被调往敌后根据地,因此不久就撤销了。虽然如此,它却是延安第一个从事京剧工作的专业组织。这个组织撤销后,我又回到戏剧系。但课余演京剧一直没断。
1939年秋天,我参加演出了阿甲编剧并主演的京剧现代戏《钱守常》,我扮演钱守常的女儿,同台主要演员还有任桂林、王一达、罗合如、石天。这个戏的故事是讲一个老知识分子在沦陷区不堪日寇压迫,起而抗争,投身了游击队。那时,这个宣传抗战的戏,仍是传统戏的“一桌二椅”和“自报家门”,但改变了一些旧的艺术形式,所以演起来时,新内容和旧形式比较协调了。早期,在没有改变旧的艺术形式时,延安的现代戏是纯粹的“旧瓶装新酒”,就是形式全是旧的,人物和剧情却是新的,非常不协调。比如扮彭德怀的花脸演员,穿着八路军军装,却迈着戏曲方步上台来,手拿马鞭,自报家门:“我乃彭德怀是也!”这种自元杂剧以来就有的戏曲程式,拿来演彭德怀,怎么看都别扭。还有个女政治指导员的角色,也是穿着军装,道白却是:“待我宣传鼓动一番便了!”而戏里的八路军战士,全跟传统戏里的短打武生一样扮相。
从西北战地服务团二团演出《清明节》起,到鲁艺演出《钱守常》止的两年多时间里,除了我参加的穿现代服装演的《鸿鸾禧》前两折和《打渔杀家》外,由于没有戏装行头,延安一直没有演出过其他的传统剧目。
为了让延安能排演传统京戏,1939年党中央决定,把毛泽东、王明、董必武、邓颖超等人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所得的车马费两千银元拨出来,让鲁艺派人去西安采购戏装。冬天,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和任桂林同志以前在西安唱戏时认识的关系,阿甲和任桂林前去买回了一副不完整的旧“戏箱”。他们雇了三辆骡马车,拉着戏箱,走回了延安。这实属不易,大家都很兴奋,围上去左看右看。虽然还缺很多服装道具,但勉强够用了。有了行头,我们马上就开始排演古装传统戏。从1940年元旦那天起,延安真正开始了古装京剧传统戏的演出。
1940年元旦,我参加演出了延安的第一场京剧传统戏全本《法门寺》。《法门寺》演的是明代故事,讲民女宋巧姣为未婚夫申冤,上告到大太监刘瑾那儿,使真相大白,得以夫妻团圆。这样的戏曲演出,并没有政治意义,只是为了满足那时候饥渴的文化需求。在剧中,我扮演宋巧姣,阿甲扮演赵廉,石畅扮演刘瑾、王一达扮演贾桂,石天扮演刘公道,齐瑞棠扮演刘媒婆,张东川扮演刘彪。在当时延安的条件下,这个演员阵容,是最整齐的,已经可谓强大了。乐队那边,鼓师是精通戏曲的陈冲,琴师是华君武,陈叔亮和刘炽都演奏打击乐器。乐队虽小,力量却很强。这几个人,不但器乐奏得好,而且个个才华横溢。后来,华君武成了漫画家,陈叔亮成了书法家,刘炽成了作曲家。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曾进鲁艺旧剧研究班,看到毛主席最爱古装戏(2)
华君武当时是美术系的,胡琴却拉得好,还爱说爱笑的,很幽默。遇见女同志买东西跟人讲价时,他在旁边笑着挖苦:“你们买个大棺材,还让人给赔上个小棺材呀?”一次路上遇见,他使劲儿绷着脸说:“瞧你那副骄傲的样子,见人也不说话!”说得我笑起来。有一次我们在乔儿沟演《鸿鸾禧》,也是华君武胡琴伴奏。我正唱着,他的琴弦突然断了。他马上用嘴接着“拉胡琴”,哼哼唧唧地给我伴奏,我在台上看他,他还跟我做鬼脸儿。他边哼哼,边接好了弦。
刘炽是鲁艺音乐系的,跟冼星海学作曲,也很会唱歌。在延安冼星海老师指挥演出《黄河大合唱》时,“张老三,我问你……”那段对口唱,就是由刘炽和张鲁俩人唱的,唱得好极了。刘炽年幼时,家贫无力抚养,把他送进寺庙。在庙里,他学会了很多佛教乐曲和一些器乐演奏。我觉得,刘炽后来之所以能写出几十年中国革命过程中最抒情、最动人的旋律“一条大河波浪宽……”、“让我们荡起双桨……”等,能在那样的激情年代用音乐表现出美,跟他少年时代受到佛教音乐的熏陶,大有关系。
刘炽爱说爱笑,嘻嘻哈哈,跟一达是多年的好朋友,见面就先开玩笑。他自己姓刘,就管王一达叫刘一达,一达就管他叫王炽。我看他跟谁都开玩笑,但是从不跟我开玩笑,一辈子称呼我“任均大姐”。我和一达与他的友谊保持了终生。“*”中一达和刘炽一起被下放东北农村,一达是自己一人,刘炽是全家老小。在村里,他常常叫一达到他家去吃饭,有点儿酒有点儿肉,从不忘记一达。他夫人柳春会做菜,生活再艰苦,餐桌上也能变换点儿花样儿。一段时间,我的小女儿津津也到那里插队,也成了刘炽家的常客。“*”后刘炽常来我家串门,一次赶上津津做拔丝山药很成功,刘炽高兴地从盘子里往起挑糖丝。糖丝不断头,他就嘻嘻哈哈地站到板凳上,把糖丝挑得快到房顶了。他总保持着年轻时那种无拘无束的淘气性格。在一次会上,我们和刘炽在一起,遇见一位老友,刘炽看他缺牙,问他:“你牙怎么了?”他说:“拔了,还没镶呢。”刘炽笑说:“无齿之徒。”大家一起哈哈大笑起来。刘炽1998年突然去世,接到电话,难以置信,我和一达同时放声大哭!
可能是因为穿戏装演传统戏,比穿现代服装演传统戏好看,加上演员、乐队阵容齐整,1940年的《法门寺》演出,轰动了延安,盛况空前。当时,一天一场,京剧《法门寺》连演四天,话剧《日出》也连演四天,天天观众人挤人。毛主席和朱老总,还有其他的中央领导人,凡是在延安的,都来看了。毛主席看了一场《日出》,却重复着连看了四场《法门寺》。全本《法门寺》比较长,他每天来看,一坐就三四个小时。看得出来,他最爱看古装传统戏。一天演出时,剧场外面的土围墙被观众挤塌了一段,乱了一阵。毛主席扭头看了看,又笑着回过头来接着看演出,看得聚精会神的。
接着演的传统戏是全本《鸿鸾禧》,也叫《棒打薄情郎》。我还是扮演金玉奴。同台主要演员是陶德康和王一达。这出戏也很轰动。全本《鸿鸾禧》里金玉奴的唱腔和表演,我都是在北平时向刘凤林学的,是我当时最熟悉的一出戏,所以表演起来比较自如。当时,周恩来副主席刚从苏联治疗伤臂回来,看了我们演的《棒打薄情郎》。过两天,我收到他写来的信,里面提到我这次演出,说“前晚看了你的拿手戏,赞佩不已!”那几年,周副主席常驻重庆,每次回到延安时,无论我们演什么戏,他都来看。十八年后,1958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即将赴欧洲各国访问演出的“中国戏曲歌舞团”时,还对负责人吴晗、张东川、王一达和主要演员们,谈起他1940年在延安看的《棒打薄情郎》,津津乐道地向在座的几位著名表演艺术家,称赞了一番我们那时候的表演。一达回来跟我说起这事,我很惊讶:这么多年了,总理还记得?
延安买来戏箱后,在演出传统戏的同时,我们也开始演出戏装的新编历史剧了。那时,我参加演出过两出。一是《梁红玉》,用的是国统区刊物上发表的欧阳予倩的剧本。我主演梁红玉,陶德康扮演韩世昌,张东川扮演金兀朮。二是《吴三桂》。这是由延安的戏剧工作者创作的第一部京剧新编历史剧,王一达和石畅编排。我扮演陈圆圆,王一达和石畅分别扮演吴三桂和多尔衮。如果说我们演的传统戏基本上是模仿前人的表演,那么,演新编历史剧,就是创作自己的角色了。在这一点上,和演现代戏一样。不同的是,穿传统戏装表演古代人物,形式与内容之间没有不协调的问题。尽管我对角色的创造说不上成功,但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