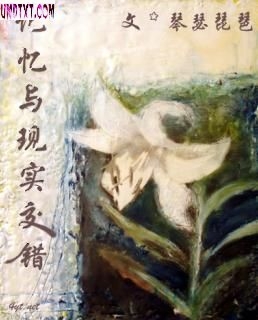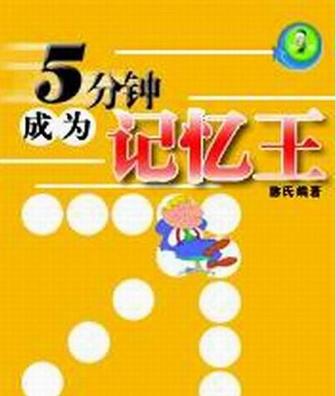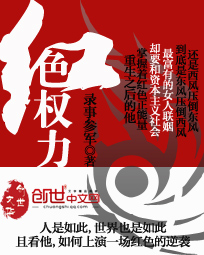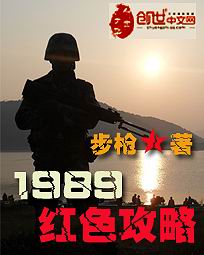红色记忆:纪事2007-第2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哈斯毕力格的儿子12岁了,小伙子还不清楚家族的使命,但父母一直让他在蒙语学校念书。“他将会是家族第40代传人。”哈斯毕力格很有信心。
哈斯身后,供桌上跳动的酥油灯火,闪烁着700余年的光芒,足以照亮未来。
风从草原走过
吹散了多少传说
留下的只有成吉思汗的故事
在达尔扈特人的诵经声里代代传扬
让昨天告诉明天
——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和幸存者名录采集纪实
黄加佳
2007年8月13日,收录了8242个遇难者资料的《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与收录了2592个幸存者资料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在南京出版。
抽象的数字被转化为一个个具体的名字。70年后,人们开始从宏阔的历史叙述中发现那些个体生命的存在。
从关注人的命运的角度去重新观照那一段历史,建立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历史叙述,是为了更深刻地记忆和反思那场悲剧。而研究历史,不是为了记录仇恨;牢记历史,是为了不让悲剧重演。
。 想看书来
那些逝去的生命
高大有男60岁厨师
遇难前家庭住址为中华门外宝塔根105号,遇难时间为1937年12月16日,遇难地点在自己家,遇难方式为被日军枪杀,加害日军部队番号为中岛部队。
周永财男被害时年龄为33岁
遇难时间为1937年12月16日,遇难地点为难民区。遇难情形:被日军指为中国军人抓走后杳无音信。证明人周洪氏,与被害人关系为母子。证明人住址为南京止马营140号。
黄腊红女8岁汉族南京人
遇难前家庭住址为中央门外五班村,遇难时间、遗体掩埋时间为1937年12月,遇难地点为中央门外五班村家中,遇难方式为被日军枪杀,遗体掩埋地点为迈皋桥回子山。
杨得意男73岁籍贯南京农民
被害时住所太平乡第八保第六甲。遇难时间1937年12月13日。遇难地点为太平乡第八保第六甲。
……
他们都是南京大屠杀30万遇难同胞中的一员。长期以来,他们的名字已经湮没在30万遇难者的抽象的群体概念中。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去追问他们究竟是谁。而在70年前,那个大屠杀来临的前夜,他们却是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人。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自己的父母子女,有自己幸或不幸的人生……
随着《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的编辑出版,一个更为鲜活的历史慢慢显露出来。
txt小说上传分享
抽象的与具体的(1)
“日本侵略者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这是高中历史教科书中对南京大屠杀的一段描述。多年以来,人们对那段历史的记忆,定格在这种抽象的描述中。所有人都知道,南京大屠杀中30万中国人被日寇杀害。他们是谁?他们是怎样遇害的?却很少有人追问。遇难者变成了一个数字。
数字化是研究历史必不可少的方式,但记住这段惨烈的历史,光有数字显然不够。“受害者不意味着数字,他们是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做了15年馆长的朱成山,感到在这种抽象的记忆中,人们与那段历史越来越远。
1997年,一本名为《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的书在美国问世,很多西方读者从这本书中第一次知道了南京大屠杀。而许多中国读者,则从作者独特的视角和叙述方式中,找回了对那段历史的情感记忆。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
曾给来南京采访的张纯如做了20多天翻译的杨夏鸣记得,张纯如与我们一直以来的视角非常不同。“她希望采访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并实地看一下集体屠杀的地点。”
在日军曾经屠杀了万人的燕子矶,张纯如将摄像机的镜头对准了山下破旧的房屋,然后拉到远处林立的烟囱,接着是江水、江中航行的船只和遥远、朦胧的长江对岸。杨夏鸣说:“她仿佛是想再现当年那些试图渡江的中国士兵那遥不可及的逃亡之路。”在采访中,张纯如不断向被访者追问那些生活的细节,甚至早上吃什么东西,平时穿什么鞋,那天的天气如何?杨夏鸣知道,她是想尽量感受当时南京人的生活细节和氛围。
正是这种细致入微的采访,使张纯如与那段历史和那些奔跑在逃亡路上的南京百姓产生了共鸣。因此,她的叙述才显得那样有质感。
其实,在张纯如的《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出版以前,我们国内已有很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学术著作出版。其中很多论述翔实,还获了奖。但这些文章的叙述语言太枯燥了,很少有普通读者会去读。
时隔10年,当杨夏鸣重新翻译张纯如的书时,对书里关于幸存者的叙述也曾有过疑惑。“书中记录的第一个幸存者唐顺山,经历太有戏剧性了,我曾怀疑张纯如叙述中有演绎的成分。”但当重新观看张纯如留在他那里的采访录像时,他发现书中的记录竟与幸存者的口述分毫不差。“张纯如毫无添枝加叶,仅仅用事实就打动了读者。”
而国内那些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通俗作品,显得过于情绪化和戏剧化,从而冲淡了史实本身给人的震撼。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抽象的与具体的(2)
史实的力量,是最能打动人的。
令朱成山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他在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参观。奥斯维辛集中营位于距波兰首都华沙300多公里的偏僻小镇上。1946年波兰刚刚复国,就以立法的形式,把它确立为国家博物馆,并进行原地原貌保存。
奥斯维辛集中营里最令人震撼的不是那些照片和讲解,而是那些壁垒森严的围墙,密布四周的电网,高耸的哨所看台,是那些曾经结束过110万人生命的绞刑架、毒气杀人浴室、焚尸炉……这些原貌保存的场景,使观者一进入其中,便感受到一种无形的气场。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展厅里成堆的遇难者穿过的鞋子,用过的皮包,以及那些死去犹太人的头发。这些实物比任何描述,给人心灵的冲击都要大得多。
而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除了原地保存的遇难同胞尸骨,更多的还停留在照片加说明的展陈方式上。纪念馆所在的江东门地区,就是当年日军集体屠杀南京百姓的一个“万人坑”遗址。可在1984年建馆的时候,建设者们并没有刻意寻找遇难者的尸骨,以至于1998年当他们在馆内整理草坪时才发现这些遗骨。纪念馆研究部主任梁强说:“当时想赶快把馆建成,也没有注意挖掘这么重要的历史证据。”
2004年,犹太人大屠杀遇难者姓名中央数据库建成,人们可以从中查到300万左右遇难者的姓名和个人资料。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哭墙”上仅镌刻着3000个遇难者的名字。这个巨大的反差刺激着朱成山的神经。
2007年是南京大屠杀70周年纪念,纪念馆要进行第3次扩建。新馆建成后,展厅面积将从原来的900平方米,扩大到6000平方米。这么大的展厅,展览什么?怎样才能帮助人们找回对那段历史的情感记忆?
朱成山想到了参观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时,那个装满遇难者档案盒子的展厅。“那个展厅里,档案盒从上到下装满了整面墙壁。每个可以搜集到的遇难者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档案盒。盒子上写着他的名字,里面装着属于他的资料,不但有年龄、职业、家庭,甚至还有生前的爱好。”
如果,能找到那些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名字,把他们编成《名录》,输入“数据库”,再制成档案盒,那将给人们一种全新的了解历史的方式。
txt小说上传分享
迟到50年的追问
2005年,《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的编辑工作开始了。
然而,时隔70年,想找到那些逝者的信息,谈何容易?资料的缺乏是编辑者们遇到的最大困难。
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和幸存者的资料,远比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的名字难查。研究南京大屠杀多年的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卫星说,“犹太人进入集中营很多都做了登记,但当时南京的流动人口很多。淞沪会战时,很多上海和安徽的难民认为南京是首都,会安全一些,都跑到了南京。而很多南京人又跑到了乡下。”
南京金陵中学的一位老师也证实了这种说法。他说:“那时候,管逃难叫‘跑反’。我们家原本在安徽乡下,鬼子来的时候听说南京城里安全,就跑到南京。到南京以后,又听说乡下安全,又跑到乡下去了。”
这种毫无规律的人口流动,加上连年战乱,户籍制度不完善,使得编辑者们不可能根据户籍查找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姓名。
几乎所有研究者在谈到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调查时,都惋惜地说,我们动手太晚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犹太人马上就开始对遇难者资料进行调查,而我们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真正开始。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民国史处于历史研究的禁区,而作为民国史一部分的南京大屠杀,也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在上世纪60年代,南京大学历史系的高兴祖老师曾组织学生进行过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和幸存者寻访,并且出了一个在校内流通的研究报告小集子。由于史料和历史条件的限制,现在看来,那次研究的学术价值并不高,它的意义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标志。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南京大屠杀,篡改教科书事件发生以后,南京学界才重新开始面对这段历史。
湮没在证人证言中的名字
《名录》的编辑作开始以后,编辑们首先从历次对幸存者的调查开始寻找线索。
对于幸存者最早的调查始于1945年。抗战刚刚结束,为了向东京法庭和南京法庭举证,也为对日索赔作准备,南京国民政府曾面向广大市民调查抗战人口和财产损失。当时很多工作人员下到各个街道,向南京市民下发调查表格。同时也有不少市民向政府呈文,述说自家的遭遇。
由于这次调查主要是向东京法庭和南京法庭举证,做得并不全面。当时的报告书称,“涉及名誉赧然不宣者有之,事过境迁人去楼空者有之,生死不明无从探悉者尤有之,故此五百余件均系经极大困难所访得。”
但这些证人证言中,还是留下了一大批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名字。
在一份1946年6月15日由市民袁福生向南京法庭提供的证言里,编辑们看到了高大有遇难的经过: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敌寇入城之际,余因经济窘困未及逃避,同屋高大有因不忍家具什件被劫,卒未离去。当日下午,即有日兵数人持枪敲击屋门,余恐波及生命,立即躲藏屋内蓄米箱内。同屋高大有则因年迈动作迟缓,前往开门,不意日寇进门怒容满面,向高大有喃喃责问,高因不懂日语,被数人捆绑椅上,以枪击毙。余蹲箱内见此情形,几乎昏绝。
而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593—27敌人罪行调查表之七,编辑者们也看到了关于高大有的记录。于是,这个叫高大有的遇难者被收录在名录中。
另一份由市民葛家永在1945年9月27日致南京市政府的呈文中,编辑看到了5名被日军杀害双亲的孤儿悲惨的经历。呈文这样写道:
具呈报人葛家永,现年十九岁,南京人,暂住润德里二号之一附户亲属处。缘因民国二十六年,南京沦陷,当时生父葛传经,年四十一岁,不幸被日敌暴兵杀死,生母张氏、外婆共计三人同归于尽。难民家前住长乐路小心桥三号,家内衣履、器具等等物件,被敌抢烧一空,该房屋成为荒地种菜,此损害重大,不堪凄惨,遗留下我兄弟妹小五口。难民当年十一岁,二弟家炎九岁(哑巴),三弟三岁,大妹家贞七岁,二妹家芳五岁,此五小口苦孩,全奈我姑父母抚养,救济生命存世者……
葛传经以及其妻葛张氏和其丈母,也被收录在《遇难者名录》中。
就这样,编辑们一点一滴地从这些60年前的资料中,积累着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名字。
1949年后的两次调查(1)
《名录》中更多的资料来源于新中国成立后做的两次调查。南京市先后在1984年、1997年做过两次大规模的大屠杀幸存者寻访活动。这两次寻访工作,可谓是抢救性的。但是,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这两次调查的方式,并不让人满意。
1984年3月,“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开展了一次为期5个月的幸存者调查。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孙宅巍还记得那次调查的范围很大,“是普查的形式。对南京10个城近郊区55岁以上的人都进行了调查。”参加调查的工作人员由南京市各区县机关、文化馆、街道的工作人员组成,也包括部分学校的师生。当时发现了1756名幸存者,形成的证言更是触目惊心。
幸存者唐广普描述了他从日军集体屠杀中死里逃生的经历。当时,15岁的唐广普是中央军的一名士兵。日军攻入到南京后,他与两万多被俘士兵和平民被日军赶到上元门大洼子江滩。日本兵用整匹整匹的布撕成布条,开始绑人,从早上4点钟一直绑到下午4点。然后,日本兵让他们一排排坐下。晚上###点,日本兵开始屠杀了。他回忆:“机枪一响,我就躺倒在地。20分钟后,机枪停了。我右肩头被打伤也没有知觉,死尸堆积在我身上,特别重。5分钟后,机枪又开始扫射。过了一阵子,日军上来用刺刀刺,用木棒打,最后用稻草撒在石榴树上,用汽油一浇就烧起来了。”这时,他从死人堆里挣扎着爬出来。而那次大屠杀,他只看到一名幸存者,姓诸。
调查中,虽然幸存者的基本信息都具备,但是从专业角度看,孙宅巍认为那些口述记录做得非常业余。“除了这些基本信息,还应该问到受难者当时的感受,后来的生活,以及灾难对其日后生活的影响等情况。但是,这次调查并没有涉及。”孙宅巍认为,这主要是缘于调查者水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