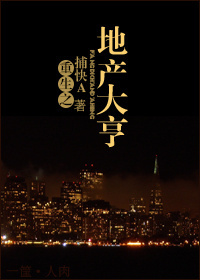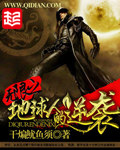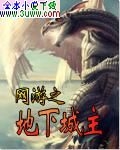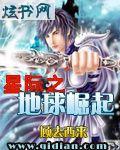一席之地-第2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走,他也许多站一会儿;他似乎听不见那施号发令的锣声。他更永远不看前后的距离停匀不停匀,左右的队列整齐不整齐,他走他的,低着头象作着个梦,又象思索着点高深的道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觉现在的自己已经变成了结尾处的祥子。我自诩曾经也像祥子一样,是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但是,我转脸发现我已经成为了一个废物,不折不扣的废物。
你们教我的东西让我站在这里时,无所适从。
这是骆驼祥子自身的原因。也更是骆驼祥子身处的北平的原因。
再见了,模拟电子技术和数字电子技术。再见了,责任和担当。再见了,让我变成了骆驼祥子的大学和大学里的自己。你们一定要记住我的模样,有朝一日,我回来的时候,你们要认出我。那时,我不一定能够认出你们,但是,请你们能够原谅,因为,我生病了。我是一个病人。
没有听到吗?我的家人,我的同学,我的老师,全都在窃窃私语。是的,他们没有谣传,他们说的是真的。他们的诊断切入骨髓一针见血。
他们说,我有严重的思想问题和心理问题。
4月1号的早晨,我接到了吴柏的电话。他说,哥,过来吧,不管怎样,我们是一辈子的兄弟手足。我握着手机,停了很久,我说,谢谢。
出发的时候,我带了几本书。我记得,那天是星期三,上午是通讯原理课,下午是单片机课。我还记得,那一天的太阳,愚人节的太阳,像梦中世界末日的景况一样,和煦万里,光照大地。
2、凤林村的病
凤林村是我读大学的这座城市的郊区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村庄。村庄中大多数的居民都是外来务工人员。本地居民只占到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多一点。说它位于城市的郊区,似乎有失公允。因为现在沿海大城市的郊区都好像长了脚。城市的快速发展让郊区变成了一个顾不得穿鞋只知道撒丫子往外跑的淘气娃。城市在扩张,郊区在移动。曾经的凤林村兔子不拉屎。现在的凤林村,南边毗邻着酒店、超市和居民楼。北边鳞次着玩具厂、电子厂和汽车配件厂。仿佛一夜之间,凤林村开始熙熙攘攘。也仿佛一夜之间,凤林村所有的房子都换了样。东屋,西屋,南屋,以前没有的全有了。不行的话层上再加一层,间里再隔一间,租出去,全租出去。曾经喂猪的地方,曾经拴狗的地方,统统租出去。开始的时候,纯粹是市场导向。有人要有个住的地方,有人有房子要租,你情我愿,一拍即合。后来,办公大楼里的人民公仆看到一时间来了那么多需要服侍的主子心慌得不得了。为了能拿出一个可行性的应对方案,搞得大大小小的会议开得葵花上的籽样密密麻麻。最后,公仆们一致决定,将几个像凤林村这样的村庄定点为外来务工人员聚居村,重点关注,重点监控,重点保护。要给外来人员办理暂住证。要收取他们的卫生费和管理费。要严格控制本地居民肆意改造自己房屋的嗜好,保持市容市貌。要加强对所有居民的宣传教育,坚决杜绝一切不良违法犯罪行为。具体的措施就是从本地居民中招揽一部分政府性质的保安人员,设立一个特殊的专门的派出所,施行村内自治管理。这样的话,既起到了对外来人员的监管,又解决了本地地痞流氓的就业问题,消除了社会的隐患,一举两得。
凤林这样一个村本来跟吴家村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它风火它的。咱萧条咱的。可经历了几年的人为熵变,盲流的盲目流动,再仔细一瞧,嘿,这个凤林村竟然和远处的非亲非故的吴家村建立起了非常稳固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双赢。这样的结果让人不禁联想起我们伟大的祖国与那些远在天边的不停地在温饱线上跳上跳下的黑人朋友们的国际友谊。吴家村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来到了凤林村。这是吴家村有史以来最为惊心动魄的一次迁徙。凤林村的诱惑已经远远超过了丘陵山的召唤。对于吴家村来说,这样的空间转移的意义绝不亚于商王朝的迁都。超过四分之一,二百多人,这么一个数字是多么令人激动啊!
大一暑期社会实践的时候,我来过一次凤林村。凤林村里住着吴柏和吴松,住着我以前的同学和朋友,还住着一群我不太熟悉的父老乡亲。但是,那次去,却不是冲着他们的。一个农民工出身的企业家在凤林村开办了一所打工子弟学校,为那些跟着父母一起背井离乡的儿童提供一个求学的机会。但是,学校开办了,运行起来却十分困难。农民工出身的那位企业家比农民工也阔绰不了多少,很多时候,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师资力量极度缺乏是学校濒临关门的最主要原因。没办法,提供食宿、一个月二百块钱的待遇让所有脑子正常的人望而却步。凤林村周围的工厂哪一家的月工资平均也不会低于八百块钱。况且,有点墨水的混在工厂里,如鱼得水不敢说,起码在更多的事情上应该更容易得心应手。这样的境况下,是不会有人过来代课的。没办法,吃饭第一,教育第二。没办法,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
大一暑假,我和我的同学在那里教了一个月的课。
而2009年4月1日以后,凤林打工子弟学校又成了我的落脚点。
开着一辆二手桑塔纳正要去给孩子们选课外书的冯校长冯小企业家郑重地点了点头,收留了我这个有严重抑郁症倾向的大二学生。谢谢伟大的仁慈的校长先生。谢谢包容的温情的凤林打工子弟学校。
从那一天起,我开始了几个月的代课生涯。从那一天起,我白天呼吸着凤林村的腾腾热气,到了晚上去记录一个叫吴桐的人在一个叫吴县的地方所经历的高中生活。从那一天起,我开始心存畏惧战战兢兢地观望那本应属于我正在属于我也即将属于我的命运——凤林村。
有一个好消息。由于社会上一些慈善基金的到账,我去代课的第三天,冯校长就兴高采烈地对着所有的教工宣布,工资暂时加一百,每月三百。进去第三天,工资就涨了一百,我乐滋滋地想,按照这个速度,我这个带病上课的代课老师真可谓之前途无量啊。但是,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吴柏的时候,他微微一笑,指了指那个特殊人员组成的派出所对过的一个霓虹闪烁的足浴城,煞有介事地说,哥,再涨一点就好了,再涨八十块钱,里面漂亮的小姐就可以张开嘴做一次漂亮的*了。
我看了看足浴城,心想,太贵了,对过派出所里的人也不一定消费得起啊。
我就这样在凤林村待了几个月。我走的时候已经快到2010的农历新年了。其实,认真想一下,这几个月里,我的生活跟在学校里也差不很多,都简单得很。除了上课,大部分时间,我都待在打工子弟学校分给我的一间单人宿舍里。只不过,吴柏、吴松以及他们的工友和朋友们会经常过来看我。我们偶尔也会一起去吃饭,一起压马路,一起聊过去今天和明天。当然,聊天的时候,一般都是他们在说,我在听。时间长了,我慢慢地发现,他们似乎和我一样,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思想问题和心理问题。
简而言之,待在凤林村里的人,也和凤林村一样,有点病。
因为2009年冬天的时候,吴柏出事了,我本来是不想回吴家村了。我打算在凤林过完年之后,就直接回大学校园上课了。我怕回吴家村以后,吴柏的事情的最新发展状况,我没办法第一时间了解到。但是,临近2010年春节的时候,家里的一个电话,让我不得不立马收拾好行囊,一刻都不耽误地回家找人去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一章
在隐隐约约的远方,有我们的源头,大鹏鸟和腥白月光。西方和南方的风上,一只只明亮的眼睛瞩望着我们。回忆和遗忘都是久远的。对着这块千百年来始终沉默的天空,我们不回答,只生活。这是老老实实的、悠长的生活。——海子
1966年的隆冬季节,天已经下过一场大雪。河沟里的冰面上越来越多的孩娃子开始抽打起木头制的陀螺。十几岁的孩娃子也不知道冻,一个个破棉袄敞着怀,黄鼻筒黏着嘴巴。他们呼啸着绕来绕去,不停地甩动着手里的皮鞭。有个人滑倒了,摔了个狗啃泥,鞭子扔出去老远,爬起来还没忘了冲着身后的伙伴嘿嘿地笑。有两个人的皮鞭铲到了一块,河面上就慢慢有了吵嚷声。吵闹声越来越大,盖过了其他人说话的声音,盖过了打口哨的声音,盖过了鞭子抽打陀螺时发出的“啪啪”的声音。于是,其他人都闭了嘴巴停了手里的动作,摇晃着脑袋寻找声音的来源。有眼睛尖的抢先跑过去劝架,吵嚷的人就被拉开,骂骂咧咧地重新把自己的陀螺拧转。既而,河面上又是一阵阵“啪啪”的回响。
北方的冬季,空气里仿佛藏着无数把刀子,冰面上闪动的人群,是刀子刻下的伤疤。看哪,那些伤疤还冒着热气呢。
孩娃子们不知疲倦的抽打快要把太阳赶进山里了。这个时候,吴老三回来了。吴老三驾着驴车驮着一捆席回来了。吴老三是吴家村的席业主席。席,你听说过吗?噢,你可能不知道,那我给你讲讲。我们这的席指的是高粱席。高粱这种作物浑身都是宝。那个年代里,还不时兴种玉米,地里最主要的粮食作物除了小麦就是高粱了。高粱有红高粱和白高粱之分。高粱穗人和畜生都能食用。高粱秸秆的外叶可以当柴火烧。高粱秸秆长得其实跟竹子差不多,它们的颜色当然不同,我所说的差不多是指它们身上都长着一节节分明的骨眼。高粱秸秆劈下的外皮叫篾子。高粱秸秆的最上面一节,我们的老土话唤作头厅杆子。把高粱摔下来以后,头厅杆子就可以拿去捆绑笤帚和刷帚了。而除去头厅杆子的高粱秸秆基本上有两样用处。一是打箔。箔呢,箔一般又有两样用处。一是铺床。我们那冬天的确是天寒地冻的,但历来都没有像东北人那样烧火炕的习惯。我们在木头炕上先是铺上箔,然后上面放上一领白席或红席。白席或红席上面是被褥。被褥里装着厚厚的棉沓沓的夏天里刚收上来的新麦秸秆。再上面就可以铺被单了。所以,冬天里再冷,我们也是不怕的。高粱秸秆和小麦秸秆都压在身子下了。高粱秸秆和小麦秸秆通过我们的摩擦为我们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温暖和希望,延续着丰收和梦想,传递着过去的岁月和来年的日子。人是生于土又归于土的,高粱秸秆和小麦秸秆也是生于土又归于土的,人和秸秆通着脉呢。你想想吧,那些庄家秸秆吸收了阳光和雨露,吸收了大地的灵气和人间的精华,吸收了蓬蓬勃勃的生命欲望,它们在屋檐上的冰渣子比人的牙都还硬的天气里,摩擦着你的脚,摩擦着你的屁股,摩擦着你的脊背,你会是什么滋味呢?箔再一个功能就是储存粮食了。它在我们的屋子里圈一个空间,我们夏秋里收的农作物就可以被呼呼啦啦地囤进去。这时的箔像院墙,像篱笆,像一个盛饭的瓷碗,像一个盛水的玻璃杯。法律牛吧,道德牛吧,老祖宗派下来的三纲五常的戒律牛吧,说到底,它们的作用跟这时的箔一样一样的。接下来要说的,就是高粱秸秆最重要的用武之地了。对,你应该猜到了,编高粱席。高粱席是吴家村人的营生,也是吴家村人的骄傲。吴家村人的生老病死,吴家村的婚丧嫁娶,吴家村人的吃喝拉撒睡,你往细里看,都跟高粱席打断骨头连着筋。老辈人愣是将除了当柴火烧再无什用处的高粱秸秆变成了最有用的宝贝,这份曲径通幽的聪慧,这份于山重水复之中创造柳暗花明的睿智,实在是让人钦佩不以。你说,文化是个啥,文化不就是藏在人肚子里的人性的衍生品嘛。在吴家村,编高粱席就是一种文化。高粱席严丝合缝地填满了人的生活,再发展吧,吴家村人的所行所为所思所考也跑不出一领高粱席覆盖的乾与坤,它比文化还文化。
按颜色,席分红席和白席。按种类,席又分独席、枕头席、凉席、穿房席、满天星席等。席的用途很多,比如晾晒东西,比如打席包,比如前面提到的铺床,不过这些都是实用功能,高粱席还在红白事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红事用红席,白事用白席。要是一对新人圆房的时候,床上没铺一领红席,那就等于往后的日子里少了一把红火,别指望着老天爷保佑这个家人丁兴旺了。要是谁家灵堂的正门上不挂一领白席,那就意味着这家主人跟阴阳两界的人都过不去,跟死了的人过不去,也跟前来悼念的亲戚朋友以及牌位桌两旁跪棚的后辈们过不去。别管死了的人是去了天堂还是下了地狱,别管活着的前来吊唁的人是多么想知道死去的人是见了阎王还是跟了天神,中间隔着一领白席呢。老祖宗都说了,生还没有侍弄好,就不要管死的事情了,换个方向说,你既然死了,就老老实实死吧,家里还剩多少油盐酱醋已经跟你没关系了。这横在门房上的高粱白席,就是吴家村里生和死的通关关卡。将死之人,扑打扑打身上的灰尘,丢下编了一半的席,换身干净的衣服,过去。要活的人,领了那边允许投胎转世的签证,轻车熟路地回来,继续编不知道哪个人丢下的半摊子席。这高粱席还真是宝贝。哪天你要是从这里过了,你就知道了。你想啊,要是上了天堂还能炫耀炫耀,但要是一不小心掉进了十几层的地狱,没有它,正好让亲戚邻居们看见,那还不得把人害羞地活过来啊。
吴老三驾着驴车驮着席回来一点都不奇怪。那头大叫驴走在河面的石拱桥时,呜噢呜噢地吼起来也不奇怪。奇怪的是,吴老三不光把没卖出去的席驮了回来,还驮回来两个半大小伙子。这会儿,排车上的两个青年正目光炯炯地看着抽陀螺的人群,河面上那帮子黑炭也直直地往石拱桥上张望。
也不知道哪块炭梆子张了嘴,冲着驴车使劲喊:
三爷爷,车上的人是谁?
小孩子家问那么多干啥。
吴老三跳下车,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