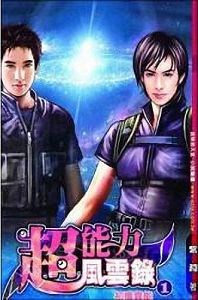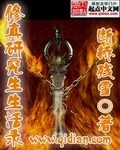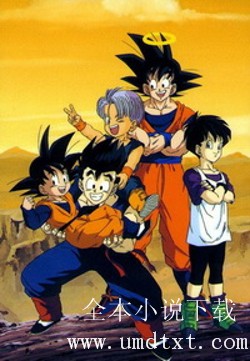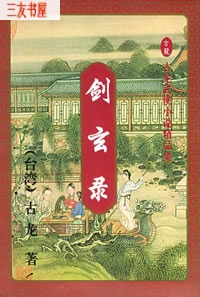黄昏录-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放了,却又重新陷入了束缚当中;体现在作品中,会有一种共性的情调,我看到有的期刊上称之为“破碎感”,为了避免抄袭,我叫它是一个群体的“无措”。
从典型作品,曹禺先生的《胆剑篇》入手,去分析这种“无措”的体现与挽回。
关键字:曹禺 十七年文学 卧薪尝胆
正文:
《胆剑篇》是曹禺创作的第一部历史剧,也是一部“奉命创作”的《卧薪尝胆》;同样,它是当年以此为题材的七十一部相同题材的历史剧中唯一流传到现在作品,流传到了当今,流传到了我手机电子书小小的宋体字里面,它的存在意义已经不仅是一部用来演出话剧那么简单了,它——《胆剑篇》,不仅是一部教材,也是一本错题本。
第一遍看完后,这部话剧却让我联想到了一篇与之时代、题材、文体完全不同的作品,那是司马相如的《长门赋》。
为什么呢?
牵强一点说,都是奉命而写的作品,都是出自大家之手却不能完全反映出其真实水平的作品。大家毕竟是大家,你依旧会看出其流畅的手法、饱满的情感,你会感到气势宏大,但你也会从这两部作品中感到一种相似的、“僵”掉的感觉,这是由各自时代决定的巧合。可以说,汉赋自从兴起就注定了它被后世诟病的命运;同样,作为“十七年文学”时代的作品,曹禺先生与他同时代的人也不免陷入了那个年代不可避免的桎梏里。
建国后,兴起了无数对新时代充满热忱的新人作者,但是对于像曹禺先生这样的一代,之前成名,但是又并未足够饱经沧桑的“中年作者”来说,他们感到了自己所追求的理想与实际现实之间的落差;他们似乎解放了,却又重新陷入了束缚当中;体现在作品中,会有一种共性的情调,我看到有的期刊上称之为“破碎感”,为了避免抄袭,我叫它是一个群体的“无措”。
从典型作品,曹禺先生的《胆剑篇》入手,去分析这种“无措”的体现与挽回。
(一)吴钩与越王剑
受限于社会背景,当时作品都会带有浓重的阶级论倾向,也就是说,会故意丑化奴隶主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而作为这个故事的两国国君,他们也被列入了被“黑”的名单里。
夫差不必说,自然是刚愎自用而且暴力愚钝的暴君形象。他一直对于伯嚭的巧言辞令言听计从,并因为如此,对于伍子胥的各种忠言充耳不闻。剧中对于他的描述是:“吴王夫差,即位不久,喜功贪杀,骄狂自是,自以为有富国强兵的本领,立下独霸中原的大志。他狡而贪,如他祖父阖闾说的,‘愚而不仁’。但他却自认有权术,有机谋,而且容不得比他高明的臣下,听不进耳的忠言。”可以说是教科书一样的暴君形象,直接按在商纣王等任意一个臭名昭著的君王身上都不会觉得别扭。
无疑,为了加强夫差这一性格特点,曹禺先生不得已地将其塑造为一个脸谱化的人物,这也是正常,毕竟他并非主角,我就不给他正名了,因为无论是历史人物还是剧里的人物我都不喜欢他。
至于勾践,他虽非英雄,却也是春秋最后的霸主,他凭借自己的军事才能杀了吴国阖闾、夫差两代大王,凭借越国弹丸之地最终吞并强大的吴国。但是与正史相比,曹禺先生明显将他故意写得懦弱与平庸。勾践似乎是被范蠡、文种、苦成,以及越国千万子民推着走的,就像勾践的台词:“二十年来,寡人别无长进,听取忠言,寡人学会了。”
无论是勾践还是夫差,他们历史中实际的性格与历史作用,与剧中所表现的性格脱节了——这是第一个“无措”。
而之所以会造成这种结果,还是因为写作这篇作品时的社会思想与曹禺本身的性格发生了冲突。第一,既要写出一部恢宏的历史剧,却还要突出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这在近代或者农民起义的时代还好,但是春秋时期,那是农民几乎算不得农民的年代(本人的史观同意人民群众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量变作用,但是一战而成的剧烈历史变革还是需要一个超出群众的英雄),战争的主导者还是奴隶主阶级;第二,诸侯间争霸本就是不义之战,要让赢的一方赢得有理有据,赢得正义,赢得光彩,即使写得出来也是极为勉强的效果;第三,这是战争题材的历史剧,曹禺先生是很擅长用心理描写和细节去体现人物性格的,他不像郭沫若那样永远燃烧,他的作品基调总是沉郁带着伤痛的,用这种感觉去写恢宏的历史剧显然是不合适的,更何况是那个需要史诗的年代里。
(二)越王与庶民
继续说勾践。
他在剧中是个重要角色,他的人物形象也是伍子胥以外最为饱满的,曹禺先生在他的身上丝毫不吝笔墨。比如他在吴王马厩的月下以及苦成崖上的大段独白,他看到国中欣欣向荣春耕时的壮志豪情等,篇幅所限无法一一详说。这部话剧,几乎是越王勾践逐渐成熟的历史:从一开始要发怒要石中拔剑,被臣子们拦住,到被囚时放生控诉自己的屈辱,再到回到越国后被臣民骂“没骨气”时先是愤怒而后反省,到了最后,吴王再次无礼挑衅时,他已经很能控制自己的喜怒,直到他攥碎了那枚玉圭,那是忍无可忍之时。
他一直在忍耐,忍住拔剑的冲动,忍住利用西施上马从吴王宫逃走的想法,忍住训斥直言的臣民的暴怒,忍住拒绝吴国强取豪夺的狠话,他只有一次没有忍,那便是最后一次,他劈碎占卜用的龟甲,说到“打得好”,他可是终于要有骨气了!
就好像拉封单寓言里说大山临盆,天为之崩,地为之裂,最后生出来一直耗子,就是这种感觉。
但是看到了最后你会发现,战争的过程很简略,先是齐晋二国违背了与吴国的盟约,率先出击——他们背弃盟约的原因都没有交代清楚——然后是因为一名战士首先忍不住反抗了,然后才顺水推舟的打败了吴国的军队,最后吴王被压到了越王勾践这里,而勾践本身甚至都没有参与到战争中去,然后这场战争就赢了——这是第二个“无措”。
这是虎头蛇尾吗?不是。淡去统治者的作用是为了突出另一群人物。
一开始会有疑惑,作为一部历史剧,吴越之争,兵家战事,为何有这么多原创平民。防风氏一家、鸟雍、无霸的孪生儿子、黑肩、苦成,他们一开始虽然出场,对话很多,但是却感觉可有可无,往后看,他们开始变得重要,到了最后一幕开始的时候,他们开始了唱,是大段的合唱,是他们壮阔的战歌。在勾践还想着藏起战船来,先把夫差糊弄过去,让他先赴黄池会的时候,那些战士们已经在苦成崖上磨好剑了(我觉得这好像是故意写的,体现出勾践反动妥协的剥削阶级本质)。战争胜利了,这是群众的力量。
苦成在剧中是人民的代表,虚构的角色,另一个浓墨重彩的角色:冒死将烧焦麦穗给勾践的是他,拔出“镇越神剑”的是他,骂勾践没骨气的是他,给勾践苦胆的人同样也是他。在剧中,勾践逐渐成熟的过程里,他的作用似乎比范蠡和文种还要重要,人生导师一般的人。即使在他死后,还依旧活在越国人所有人的心里,“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他死去的悬崖被无数人凭吊,成为越王钦点的英雄埋骨圣地(后来鸟雍也被葬在那里)。
但苦成也是一个失败了的角色,首先他的定位十分模糊:人设中他与越王是同宗的人,这样的出身显示他是贵族;同时,他似乎又是个劳苦大众,他的儿子们是战士,也是农民,是旱灾时吃不上粮食的人,是两国交战中被掠夺欺压的平民;从他的言行来看,若是隐士,他太过积极入世,若是热情的爱国者,他为何在越国战败后才站出来出谋献策?可以说,这个人物一身的破绽。
其次,他是太过于脸谱化的人物,像是样板戏里面那些伟大的革命家,是太过理想化了的角色,笔墨虽多却看不到其本髓,他的人格熠熠生辉高屋建瓴但我们无法为之感动,因为这是个不可能的人,你越加修饰他就越虚假——这是第三个“无措”。
我将两个角色放到一起,因为他们是绝对的对立两方,真实与虚构,最上层的大王与最底层的农奴,愚者与智者,摇摆与决心。说得胡闹一点,感觉就像是在故事的开始时,勾践在禹庙中迟迟不出来,是因为曹禺先生趁这段工夫,将勾践的性格单拎出来,随便注入一个普通人的躯壳里。
(三)人与自然
勾践去吴国之前,伍子胥烧了越国的粮食;勾践离开吴国,越国大旱,然后百姓们在太辛爹的带领下开始求雨,苦成、文种、勾践、全国人,都开始求雨,高喊出“非自耕者不食,君子自强不息”(历史上越国确实曾向吴国买米,但目的是为了使吴国国力空虚;到了剧中,变成了勾践为了百姓活命,用珍宝换取粮食,还被苦成和文种轮番骂了一通)。这是特别打动我的一段,而它打动我的地方不是因为他们的气节,而是因为最后没有下雨。
读到那声雷鸣传来的时候,我还以为会有一场暴雨,然后众人大受鼓舞,斩木为兵,堆石为船,百万黎民过江去,三千越甲吞了吴。但是,没有,他们站在龟裂的国土上,绝望的看着那片云彩飘了又走。
再翻篇,就是越人沐着春雨耕织了,再之后,是各种绝望与希望的交替,屈辱与荣耀的交替,苦成死了十五年,这十五年里他“成了神了。你保佑越国风滴雨顺,你保佑越国年年丰收……家家是谷满仓,牛成群,孩子一堆一堆的。他们长大了,入了伍了。连你殉难那天生下的孙儿,子犁、子剑也都入了伍了,拿起你舍命保下来的戈矛刀剑了”——这是第四个“无措”。
这是信仰的矛盾,求雨不成,是唯物主义的写作结果;人佑越国,这是客观唯心加上个人崇拜。如果苦成还活着,这好说,算是他的人格感召力,也算是客观反应了此剧本创作环境;但是苦成死了,这句话再说出来,就是迷信了。
下面我想说说与本文主题之外的议论。
*是相信人定胜天的,在三年灾害之前,哪有什么人定胜天,不过是你是打算保养还是透支这片土地。“何用尺刀,壁上雷鸣,泰山之下,夫人哭声。”事实上,如果仔细去看勾践的那些强国强军做法,你会发现这无疑都是透支国力的点子:减赋税,省刑罚,开沟洫,选贤能,轻徭役,叫百姓先富足起来……庶民家奴,生了男孩,大王就赐给一壶酒,一只狗…… 生了女孩,就赐给一壶酒,一头猪(正史里面是两壶酒,管他呢,谁知道是多大的壶)。
首先说,这些赏赐(正史里面更多,包括人战死了,他的家人都是有好处的)需要国家的资金作为支持,而同时轻徭薄赋,这会使得国库逐渐空虚下去,还不算以前向吴国的“进贡”,因此,勾践的此政只适用于短时间的迅速增强国力,不能长久地维持,因为久了,国家就穷了,国王就穷了。
有个典型的例子:战国末年的长平之战,秦始皇为了筹措粮草,而不得已将一郡的全部人加封爵位——这意味着,整整一个郡的人以后都不用交税了,而且终身可以拿到国家给他们的粮食——派遣十五岁以上男丁去战场运粮。这样的例子在春秋战国时期很多,一个国家会突然强大起来,然后又衰下去,因为它们强大的政策都无疑是釜底抽薪的办法,越国是当时做得最狠的一个,因为起步晚,所以后来居上。
因此战胜吴国之后,越王确实称霸了,但这个国家已经透支,勾践是春秋的最后一个霸主,当越国终于发觉了这政策的副作用时,当所有相似的国家都被这种刺激政策拖入泥潭的时候,正好是春秋时代结束之际,中原大地重新洗牌,开始以另一种模式再次争霸。
(《胆剑篇》其实有一个错误,春秋战国时期人的男性成年的二十岁,而十七岁开始能够入伍,只有在紧急时候——比如上面说的秦赵长平之战后期——才会发动十四到十六岁的半大孩子参与军事,因此剧中第五幕十五年后,那些“他们长大了,入了伍了”的孩子,包括子犁子剑那对孪生兄弟,其实还没有到入伍的年龄。)
(四)诗人与曹禺
在这个剧里面有个格格不入的人,那是黑肩,黑肩出场的时候在哀叹自己的命运,一边吹着竹管,这样的基调甚至比勾践囚在吴王宫里还要悲凉。《胆剑篇》中(我能够看出来的)化用了两篇《诗经》,一篇《鸱鸮》、一篇《无衣》,都是由黑肩歌唱或者领唱的。
我认为他在其中的角色作用不仅是从懦夫成长为英勇的战士的脸谱形象,也不是为了衬托苦成和鸟雍的忠心和硬气,更重要的,他是个细腻的诗人,他代表了这个全民皆兵、忙着自强不息的疯狂而粗犷的越国里面,格格不入的清醒与无所适从。这种感觉就像是看到了,在那个蒸蒸日上的新中国里面,无措的曹禺先生。
参考书目:
【1】面对“新的迷信”束缚的挣扎与反抗——《胆剑篇》新论 ; ;温潘亚 ;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8…08…25
【2】尊重与摆脱的调和——历史剧《胆剑篇》再解读 ; ;闫立飞 ; ;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12…03…15
八声甘州
落三千里破火神州,蹒跚曳蚍蝼
陷翻波旧水,吴艨击桨,不济河舟
正就迁酬年事,算未定归游
又夜寒交昼,困倦难收
阅遍难堪往事,反记荒唐者,恰好孱雠
错西山隐径,再凑众重谋
夜骑猜,参商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