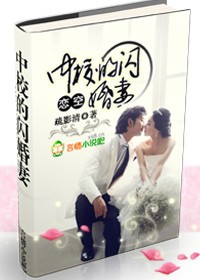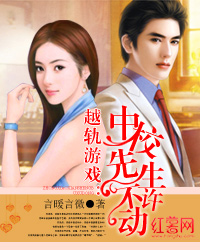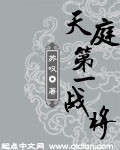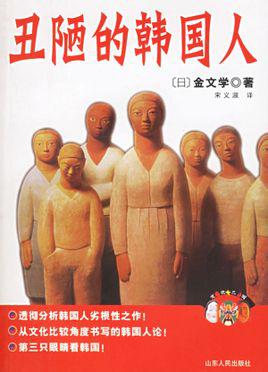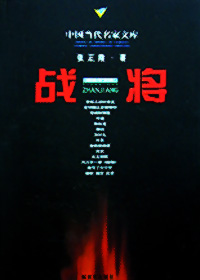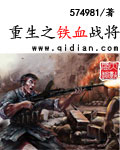战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传奇将领纪实-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谭政抵达汉口后,来到陈赓所在的特务营。在入伍时,他和陈赓商定说:“大哥,我不再叫那个封建主义的谭世铭了!”
“好!”陈赓大笔一挥,为他填上“谭政”二字。从此,他就改名为“谭政”了,随后,在特务营2连担任上士文书。
可是,谭政参加革命不久,革命形势就急剧变化,蒋介石叛变了革命,汪精卫也叛变了革命,共产党人惨遭屠杀,陈赓也被撤了营长之职,谭政也因共产党嫌疑分子失去了人身自由。因为严峻的形势,谭政克制了自己的感情,没和家中通信。一天,陈赓悄悄和他约定时间、地点逃跑。当夜四更时分,两人在“自己人”站岗时溜出营门,过江转而去武昌,寻找地下党。不久,陈赓去了南昌,谭政留在共产党员卢德铭的武昌警卫团任9连文书。
随后,警卫团进驻修水县城,在这里谭政遇到专门来修水与警卫团联络的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的党代表……罗荣桓,两人一见如故。在卢德铭、罗荣桓的率领下,警卫团参加毛泽东发动的湘鄂赣秋收起义,就这样,谭政随罗荣桓等人奔向井冈山,汇聚到了毛泽东的麾下。
1928年初,红军又一次攻占了遂川城,知识分子出身的谭政被组织上选派为前委书记毛泽东的秘书,成为了毛泽东的首任秘书,从此他和伟大的中国革命更加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从此,他也和家里完全断绝了联系。
早在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后,一天,谭润区在镇上喝茶,听到长沙大杀共产党员的消息后吓出一身冷汗:“可怕呀!太可怕了!”他回到家里,唠个没完,最后,拍着大腿说:
“千言万语,只后悔当初没有坚决阻拦,只落得现在挂念万千!”
由于对儿子的牵挂,久而久之,他渐渐将责任推到儿媳陈秋葵身上:“世铭要不是娶了这个媳妇,就不会去当兵,就没现在儿子无影无踪、不知生死的情况。”公公、婆婆的抱怨,对丈夫的思念和牵挂使得陈秋葵的思想压力很大,渐渐,她本来就有病的身体变得越差了。不久,她的亲生父亲陈绍纯也因为陈赓参加革命,而被反动当局两次以“教子不严”、“赤匪家属”的罪名被捕入狱。种种打击而来,陈秋葵终于病倒了。
15和妹夫同被授予大将(3)
这一病,她就再也没起床过,半年后,终因忧思过度,幽幽离世。
陈赓是1933年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后才和谭政再次见面的。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一个带兵打仗,一个在军中做政治工作,一武一文,虽然在不同的部队里,时分时聚,但大舅子的情谊一直保持着。他们共同成为了毛泽东手下倚重的军事将领,为缔造新中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这次两人同时被授予大将军衔,陈赓是大仗小战数不清,而谭政几乎没独立指挥打过一次大仗,他完全是凭着自己对军队政治工作的贡献而获得的,因此,有人称他为“政治大将”。授衔后,陈赓乐呵呵地说:
“谭政,你这支笔胜过枪啊!”
谭政说:“我只是扛枪的秀才呀!没你当年暗地使劲把我往东山高小‘煽’,我还不是写着那又长又臭的八股文,谁看得懂啊!那样的笔别说是当枪,就是当根竹竿,都没人要呀!”
。。
16心脏停跳三次,两次过关(1)
由于战争年代的伤痛和长期积劳成疾,从1957年开始,陈赓的身体渐渐变差。
这一年2月,他到南京、无锡、镇江、苏州等地视察防务。3月,从上海出发去沿海岛屿勘察。由于过度疲劳,他曾摔倒在浴室里。这时他已严重失眠,靠服药才能入睡,经常感到头晕目眩。4月回北京,紧接着又是参加各种会议。6月底,离开北京,冒着溽暑,前往广东、福建等前沿勘察。9月,出访苏联。10月,参加海陆空大演习。他从上海回来时脸色蜡黄,不住地用手摸着胸部,对傅涯说:”我可能坚持不了啦!”但他还是支撑着,照常上班。
12月19日,吃完早饭,身为副总参谋长的陈赓穿好了军服,正准备去总参谋部上班。突然有人登门,妻子傅涯去上班了,客人稍坐一会就离开了,家里只剩下陈赓、两岁的小儿子涯子和做家务的阿姨。客人一走,涯子就蹬蹬蹬地从客厅跑出来,在厨房找到阿姨说:“爸爸哭了。”
阿姨忙着收拾碗筷,以为孩子说玩话,就说:“爸爸怎么哭了?”
涯子又从后院跑到前院,找到司机老赵说:“爸爸哭了,爸爸哭了。”老赵忙到客厅一看,陈赓已经倒在沙发上了。
原来客人走后,陈赓胸部突然出现剧烈的心绞痛,呼吸困难,疼痛一阵比一阵剧烈,脸上迅速失去血色,满头汗水直淌,他随即在沙发上躺下,昏阙过去了。正在地板上玩耍的涯子发现了,懂事的他立即叫人。
老赵立即把陈赓抱到里屋床上,副官立即打电话叫医生。可是当北京医院的医疗小组赶来时,陈赓已经处于休克状态,手脚冰凉,连脉搏、血压都测不到了,诊断结果是心肌梗塞,立即进行抢救,可一直到晚上10点多钟,他还没有苏醒过来。
结果,聂荣臻、粟裕、张爱萍、刘亚楼、彭德怀、陈锡联等都闻讯先后赶来了,11点钟的时候,他终于苏醒过来了,第一句话就喊道:
“对×××不能让步!”
原来在前一天会议上发生过一场争论,陈赓对一位同志提出过批评。他这一喊,众人高兴起来了,陈锡联安慰他说:“你命都不保了,你别想那么多啦!”
结果,他此次发病在医院卧床3个月后才能走动。
1959年,陈赓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还兼国防科委副主任。一次,有个国防科研项目要在京郊20公里处试车,他要亲自去观看。结果,这天一早,傅涯同时接到两个电话,一个是军委办公厅打来的,一个是中央保健室打来的,两个电话都是要她劝阻陈赓不要去,傅涯放下电话,劝陈赓:“你身体不好,千万别去。”陈赓哪听,大喊一声:“开车——”蹬上汽车就走了,急得傅涯又给那个单位打电话,请他们准备些急救药品。
中午,陈赓回来了,一进门就生气地大声嚷道:
“傅涯,你汇报吧,就说我活着回来了!”
原来,他对妻子早晨劝他还生着气呢。
5月,陈赓心肌梗塞症第二次发作,但是他还是闯了过来。
此后,他被迫退居第二线。
1960年年底,陈赓的心脏已接近停跳的边缘。组织上安排陈赓和傅涯到上海疗养,但是陈赓自己不去,也不让傅涯跟去,后来中组部部长安子文给傅涯安排了一件去上海的调研工作,陈赓才同意。1961年2月,陈赓到达上海,第二天他便催着傅涯去上班。
这时,陈赓明显地衰老了,头出现秃顶,脸皮松弛。其实,他才刚满58岁,是多年的病痛令他如此衰老。但是,包括傅涯都没意识到他危在旦夕,陈赓也根本不承认病有多么严重,动不动就说:”过去打那么多仗都没有死,现在好好的就死啦?”
因为心脏病,医生不让他吃肥肉,他就当着众人面,冲着傅涯大喊大叫:“傅涯你最坏了,不让我吃大肥肉!”
到了上海,傅涯依着他,让他吃肉,陈赓却把盘子朝旁边一推:“主席、总理都不吃肉啦,我们在这里为什么还要吃肉?”
16心脏停跳三次,两次过关(2)
他犯病之后,战友来看他,他冲着人家问:“你们又开会?什么内容?为什么不告诉我?”
到了上海,他一直嘀咕:“在广州,他们开会,不告诉我;到了上海,连看的人也没有了。”
傅涯跟他解释:“许多人都来过了,被医生挡驾了,怕影响你休息。”
他马上对傅涯说:“那他们一定骂我官当大了,架子大了,不行,你明天登门道歉!”
陈赓的举动有些反常。
在上海,他开始练大字,又教女儿练字。练累了,他就叫女儿上楼去玩,叫秘书念文件给他听。秘书看他身体不好,多是挑主要的念。一天,秘书念了一份文件:“中央军委要求人民解放军所有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都要将自己参加革命战争的整个战斗经历,写一篇作战经验总结。”
陈赓微笑起来,又皱起眉头。他拿过那份文件翻了最后一页,用手指戳了一下:“这份文件我在北京就应该看到,怎么到上海才接到!”
“他们可能怕首长身体……”
“我还没死!他们是成心的!”
他激动地一把摘下眼镜,然后,吃力地拄着手杖,站了起来,望着墙上一副中国地图,忽然说道:
“我这条瘸腿走遍大半个中国,打了30多年的仗,现在不总结,更待何时?你给我找一份作战地图,我列个纲目,我口授,你来写!”
晚上,傅涯赶回来了,陈赓把秘书写的开头给她看,自己躺在沙发上叹气:“我觉得我的本意没有充分表达。”
傅涯附和道:“这么重要的总结,恐怕秘书很难体会你的思想。等你身体好些,自己亲自写吧。”
听到这话,他颇有些兴奋,从沙发上爬起来,坐回办公桌:“我这就动手!”
“哎呀,你现在怎么能写?”傅涯急了,后悔刚才不该说那些话。
“我现在不写,什么时候写呀?”
结果,他抄起稿纸就奋笔疾书,饶有兴趣地排列着前后章节,并且开始了动笔。随后,一连几天,他都沉浸在写作之中。
3月上海的天气多变,气温偏低,这使得他常常感到不适,这加速了他的心肌梗塞的第3次发作。3月15日,傅涯从外面回来,陈赓突然做在沙发上,半开玩笑地说:“欢迎,欢迎。”
傅涯见他兴致很高,忙问:“好些么?”
“托你的福。”陈赓一开了个玩笑,然后说:
“傅涯,今天是我的生日,你给我擀点面条吃吧。”
从不记得自己生日的陈赓破例提起了自己的生日。当夜睡觉时,夜已深了,陈赓突然说:“傅涯,你怎么不看看我?”
第二天黎明,天色阴暗,朔风吹得门窗发出怪叫声。6点多钟,陈赓被剧烈的胸痛惊醒,他的心肌梗塞第3次发作了。傅涯赶快给医院打电话。
不巧,这天是星期天,医院大夫没能及时赶来。陈赓已经不行了,他软弱无力地转动着身子,喘息着问道:“今天是不是应该打肝素啦?”
大夫还没有来,陈赓在病床上挣扎着,傅涯紧紧握住他的手,渐渐,他的手越来越冰凉了,瞳孔逐渐扩散。
大夫终于赶来了,打强心针,按摩,作人工呼吸,穿刺……全都无效。
1961年3月16日8时45分,陈赓大将没有再起来。
1父子相依为命(1)
在大别山、桐柏山交会的湖北孝感小悟山下,有个叫刘家嘴的地方。1915年3月3日,刘震就是出生在这里一个穷人之家,刘震原名刘幼安,是家中的独生子。全家只有一斗半(7分)田,刘父刘德显是个老实人,起早贪黑,也不够糊口。由于过度劳累,刘母在刘震5岁时就离世。母亲去世后,家境更加艰难,父子俩相依为命。刘震开始拣粪、拾柴、放牛,还干家务事。父亲对小小年纪的他要求很严,规定他每早得拣一筐粪,有几次他拣粪不够一筐数,不敢回家,只好坐在野地里直哭。
在7岁时,一天晚上父亲把他叫到身边说:
“幼安!你娘在世时就说过,我们家只有你一个崽,家里不好也得送去读几年书,要不一个大字不识,将来人家会看不起的,还会受人欺。”
此时乡里还没有公学。他上了私塾,读的是四书五经之类的东西,每天“之乎者也”,弄不懂也记不住,只能死记硬背,枯燥无味。父亲管教很严,晚上一有空就督促他读书习字。在父亲的严格督促下,他渐渐对读书有了兴趣。但好景不长。3年后,父亲的哮喘病发作,而且越来越严重,一天对他担心地说:
“我这个病无钱医治,非拖死不可,我死了不要紧,没把你抚养成人,我死了也闭不上眼。”
父亲边说边流泪。刘震“哇”的一声痛哭起来,不知如何是好,只是一个劲地对父亲说:“不会死!病会好的!我不读书了,帮你种田。”
父子俩紧紧地抱在一起,沉浸在哭泣中。10岁的他也由此辍学了。
第2年,父亲的病有些好转,刘震就开始跟着他学种田。因为父亲的身体还不大好,他又年幼,干重的农活父子俩都有困难。只得把租种的三斗田退了,只种自家的一斗半田。这样粮食就更少了。为了渡过青黄不接的难关,从这年冬天开始,他又跟父亲上山砍柴,一同挑到松林岗、花园集镇上去卖。
父亲体弱,肩负着沉重的柴担,驼着背,喘着粗气,走路一步一步的,很艰难。即使这样,他还是心疼年幼的儿子,生怕他压坏了幼小的身躯,每次只让儿子担50斤。有时,刘震一个人担柴去卖。他就挑上六七十斤,想多卖点钱回来,但人小力不足,在路上压哭了好几次。
这一年年底,父亲要打算让儿子去学木匠手艺。刘震听人说当徒弟不仅挣不到分文,还要挨打受骂,对父亲说:“我不想去学木匠。”
父亲劝他说:
“伢仔!我是为你着想。你也晓得,靠我们家一斗半田种的粮食不够吃,租地主的田要缴高地租。做生意你还小,我们也没本钱。你不去学手艺怎么办?常言说‘百艺好藏身,荒年饿不死手艺人’,有了身手艺,将来也好有个谋生的路子啊!”
刘震还是不愿去学木匠,便说:“到小河镇去学个店员也好嘛!”
父亲说:“我没这种关系去求人的。你仔细想一想,还有什么出路可走的啊?”
刘震想了一会。确实没有别的出路,在父亲苦口婆心地劝说下,只好答应学木匠试试看,从此开始了学徒生活。可在这年头学手艺还不如说是当下人。师傅整天叫他拣粪、种田、劈柴、担水、做饭,还要帮师娘照看孩子、洗尿布,真是无所不干。至于木匠活,师傅最多只教点粗活“手艺”,如劈木柴、拉大锯等,真正的手艺从不传授。结果,学了两年,他只是学些劈木柴的粗活儿。后来在红四方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