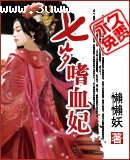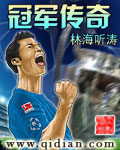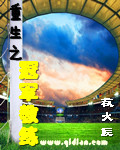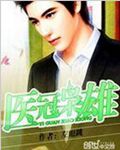嗜血的皇冠-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四年之前,流民初起,规模都不算大,几十人或者上百人,便是一支流民队伍。倘若此时予以安抚,事态很容易平息下去。然而,所谓屁股决定脑袋,由于帝国官僚们的官僚习气,耽误了最佳的应对时机。官僚们为了政绩,存着侥幸心理,一开始根本不报,以为可以蒙混过关。事态扩大之后,虽然不敢不报,但又多有隐瞒,实百言十,实千言百。就这样一层层欺骗上去,县欺其郡,郡欺朝廷,朝廷大臣们一看报告,并不严重嘛,这般小事,无须惊动皇帝,于是,王莽便被蒙在了鼓里。
等到终于惊动王莽,事态的严重已经可想而知。不得不承认,王莽对老百姓的爱,绝非嘴上讲讲,他心中确实装着穷苦大众,因此在接到流民报告之后,第一时间便作出批复:一律赦免,允许他们各返故乡。
和王莽雄心勃勃的改革一样,王莽的批复同样未能落到实处。流民们返回故乡之后,依然不能解决吃饭问题,加上贡税负担沉重,辛苦一年到头,将所有收成全部用来缴税,还得倒欠政府,兼以法禁繁苛,动不动就可能被判犯罪,抄家入狱,这样一合计下来,还不如重新当流民,吃霸王餐,做自由人。更为可恨的,则是官府的所作所为:流民集中之时,力量强大,官府奈何不得。一旦解散,化整为零,官吏们则趁机报复,对分散的流民追剿堵杀,以此充作政绩,邀功请赏。
于是,流民们散而复聚,不可断绝。王莽见赦免毫无效果,不禁勃然大怒,当朝痛骂道:“剪韭剪韭断杨柳!流民盗贼,宁有种乎?”
曾经的王莽,其见识远不止此。作为一名优秀的政治家,理应和优秀的文学作品一样,来自生活,高于生活。然而现在的王莽,已经没有了生活,他所赖以依靠的,只剩下他的感觉。
然而,有感觉就会有错觉。王莽依然主宰着帝国,但他已经不再了解他的帝国。王莽依然深爱着他的百姓,但他已经不再了解他的百姓。他独处于宏伟的未央宫中,拍着脑袋,想着当然,人间之疾苦,民生之多艰,对于他来说是如此之遥远。他根本无法体会流民们的悲惨处境,他只是觉得,你们这些流民,擅离家乡,四处掠食,不知道触犯了帝国的多少条法律,而我却赦免你们无罪,给你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我是如此宽宏大量、仁慈端庄,然而你们却把我的一片好心当成驴肝肺,放着好好的良民不当,非要去四处流浪,难道你们是天生受虐狂?
王莽当朝怒骂流民,等于是给流民定了性,官吏们纷纷表态附和,陛下您德高三皇,仁过五帝,天下人有目共睹,有心共知。些许流民,非但不感激陛下的恩德,反而自甘堕落,实在是因为他们天生就是做盗贼的材料。陛下无须忧虑,萤虫岂能撼日月之光,这些流民盗贼,不久就会自生自灭。王莽于是大悦,对这些官吏加官进爵。其余官吏一看这架势,当然见样学样,也都只报喜不报忧。
然而,四年过去了,流民们非但没有自生自灭,规模反而越来越大,人也越聚越多,其席卷区域,包括了青州、徐州、荆州、并州、兖州、冀州、扬州,整个关东地区,都已是盗贼蜂起、流民遍地,王莽这才如梦方醒,知道受了手下那群官吏们的忽悠,这些流民原本只是国家之小疾,经过官吏们有意的误诊,硬是给活生生地耽搁成了国家之重症。
我也曾劝过王莽君,重症尚非绝症,天下事溃烂至此,你多少也应和其他皇帝那样,先使出减膳、祷天、下罪己诏等常用套路来,以示心系百姓、与民同忧。表面文章总归是要做的,你不是最擅长做表面文章吗?王莽听完之后,背过身去,以袖掩面,号啕恸哭。
【No。5 伤心事】
仿佛是多年的压抑,在此刻一总爆发,王莽痛哭流涕,直至耗尽全身力气,如一堆稀泥瘫倒在地。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哭得如此伤心,如此委屈,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会让人意识到,尽管王莽是帝国至高无上的皇帝,统治着当时近七千万的人口,但他仍然只是一个普通的老人,再华丽的衣冠,再巍峨的宫殿,都无法掩饰这一现实,他已经六十八岁,即将迈入古稀之年,身体佝偻,白发苍苍,一身的老人味。
王莽这一哭,虽然突然,想来却又在情理之中,人到晚年,心境本来就寂寥悲苦,更何况家门连遭不幸,眼看着亲生骨肉一个个先自己而去,人越来越老,伴越来越少,心中的凄凉悲伤,可知可想,然而他却偏偏又是皇帝,他能向谁倾诉?而谁又敢给他安慰?他只能在没人的地方,允许自己短暂崩溃、痛哭一场,哭完之后,又必须擦干眼泪,继续坚强。
然而,我依然低估了王莽的情商,王莽这一哭,并非为家事而哭,而竟是为国家而哭。他睁着昏黄的双眼,嘴中不住念叨着,百姓,流民,百姓,流民,念叨了一会之后,忽然又高声咒骂起来,那意思大致是说,你们这些百姓,老子改革的时候,怎么没见你们这么积极?现在稍微一挨饿,就合起伙来跟老子作对,你们都他妈的是些什么东西?
很明显,在王莽的判断里,老百姓们实在不是个东西。他虽然恨那些误国的官吏,但他更恨这些悖逆的百姓。他就是想不通,他为了这些百姓,可谓是操尽了心,勤勉政事,加班加点,常御灯火至明,犹不能胜。有这些时间,我本可以饮美酒,赏美景,睡美人,想多快活就能多快活,而我竟拒绝了这些快活,傻傻地选择了受苦,我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你们百姓?在我之前的历朝历代,你们过的都是些什么日子?最早的西周春秋,连打仗都不让你们老百姓去,觉得你们这些贱民,只能耕种畜牧,根本不配拥有为国而战的荣誉,后来到了战国,他们见让你们送死是好的,这才慢慢将你们送上战场。长久以来,你们都在被侮辱被损害,富者田连阡陌,骄奢淫逸,而你们却贫无立锥之地,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一想到你们的境遇,我几乎每次都要叹息流涕。如今我当了皇帝,有了改变这种不公正的权力,我什么都替你们想到了,解放奴婢,分给你们田地,又免费借给你们钱粮,古往今来,哪个皇帝能做到这些?而我做到了,并且是在你们没有开口要求的情况下就主动给了你们这些,你们可曾想过我为此所承受的压力?你们没有,你们也不关心,你们甚至连自己也不关心。那些权贵地主就懂得关心自己,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纷纷起来反对我,阻止我,而你们呢?我以为你们会站出来为我欢呼,给我继续前行的鼓舞,然而你们没有,你们屁也没有一个,只是可耻地沉默着。我应允了你们一个光明的天堂,你们不要,反而甘心活在黑暗的地狱,你们究竟是不知好歹,还是奴性愚昧?
王莽单方面咒骂着百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然而,他高居在庙堂之上,又怎能听到百姓们真正的心声?老百姓虽然人数众多,却是绝对的弱势群体,如狼似虎的官吏们,拥有随意欺负他们的权力,俚语曰:州县符,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王莽哪怕有浩瀚如江海的恩泽,等到了老百姓这里,最多也就剩下一滴两滴,其余的则流进了一层层官吏们的荷包里,王莽又没有顺风耳、千里眼这样的特异功能,不可能监督到每个人,逐一进行纠正。因此,王莽的诏书虽然是无比的美意,但老百姓的境况并无任何改善,该被侮辱的照样被侮辱,该被损害的照样被损害,甚至比以前更加悲惨。
在王莽的想法里,既然我皇帝都维护你们老百姓的利益,如果有官吏胆敢从中作梗,有我替你们撑腰,你们还怕什么,你们大可以反抗嘛,你们为什么不反抗?殊不知,就算王莽到时候真的肯为老百姓撑腰,老百姓们依然不会选择反抗,一则他们本来就以善于忍受苦难而闻名于世,二则又是人性的必然结果。
博弈论里有一种“自愿者困境”,即在一个群体之中,率先采取行动的人将会丧失一切,而让其他人得益,但是,如果群体中的所有人都维持不动的话,那么最后大家都会面临灭顶之灾。而具体到老百姓反抗官府这事上,则“自愿者困境”可以改称为“出头鸟困境”,即老百姓们不堪官府欺压,都希望官府完蛋,但是要让官府完蛋,就必须有人起来反抗,而反抗官府的代价则是死亡,于是,每个人都希望别人去当出头鸟,为了大家的利益去送死,自己则搭顺风车捡便宜。最终结果则是谁都不愿用自己的性命为他人做嫁衣,大家都等着别人起来反抗,最后就变成没有人反抗。孔子所言的“不患贫而患不均”,至此则有了新的意义,老百姓们既然都很平均地过着悲惨的生活,同时也很平均地受着官府的侮辱,于是很容易便会沦为麻木的看客,非但不抱怨自己的悲惨,甚至还学会了欣赏别人的悲惨,并从中获取巨大的安慰。
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一路上虽然偶尔也有好事,譬如女儿国什么的,但大部分时间里,总还是碰到妖怪前来欺负他们。此时的师徒四人,其实也面临着“出头鸟困境”,打妖怪总是有危险的,最好是让别人去搞定,自己则不出工也不出力(尤其考虑到妖怪的主要目标通常都是唐僧,三个徒弟如果都选择观望容忍,结果最多也就是白挨一顿揍,保命应该问题不大)。让唐僧高念“阿弥陀佛”的是,每次妖怪一来,孙悟空都会义不容辞地主动跳出来,从而解决了这一“出头鸟困境”。孙悟空之所以甘做出头鸟,抛开他的本领大不论,更重要的是其余三人都是人(猪八戒曾经也是,而孙悟空则是猴,他没那么复杂和阴暗的人性。
王莽想不通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老百姓们一饿肚子,就要合起伙来跟他作对?王莽这一问,虽然远比说“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来得清醒,来得高明,但他毕竟从未挨过饿,他根本不明白饥饿带给人的恐怖。
这世上原本什么人都有,生旦净末丑,猪马鸡羊狗,千人千面,不一而足。然而尽管人性变化莫测,但所有的人性,都有一个最小公约数也是唯一的公约数,那便是对食物的需求。饱腹之后,自然可以人人有一本流水的账,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从而陷入到出头鸟困境,然而一旦饥饿降临,像做除法一般剔除掉所有多余的人性,于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要吃饭,我要活下去。
被官府欺压,尽管遭罪受气,至少还可以暂时苟活,久而久之,也就习惯成了自然。但是肚子这一饿,饿得连称颂我皇圣明的力气都不再有,再多饿上几天,性命也将没有,此时的老百姓已经别无选择,只能成群结队、离家出走。然而,依然要替这些善良的老百姓们辩诬,他们虽然离家出走,却并不敢和王莽作对,他们的策略类似于甘地,非暴力、不合作,他们只是想找到属于自己的食物,仅此而已,别无他意。
孙中山先生在民權初步》序言中曾经慨叹,“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而老百姓这一盘散沙,如何才能聚沙成塔,乃至于化为威力更大的沙尘暴?这里单讲民智尚未开启的古代。如我们所知,此次王莽末年流民的兴起,主要是由于持久的干旱和蝗灾,而蝗虫本为独居动物,生来胆小,但是一旦其后腿受到触碰,蝗虫就会改变原来独来独往的习惯,变得喜欢群居,群居多了,进而泛滥成灾(资料来自网络,未必正确)。百姓身上也存在着类似蝗虫后腿的部位,而这一部位便是胃,只有统治者掏空了百姓的胃,突破了这一容忍底线,一盘散沙的百姓才会奋起团结,齐心协力(拿蝗虫和老百姓相比,只为议论,绝无恶意,相反,蝗虫和老百姓堪称对立的两极,蝗虫是不劳而获,老百姓却是劳而不获)。换而言之,历史上所谓的盛世乱世,无非也就是老百姓们能吃饱和能饿死的区别而已。
王莽天真地希望老百姓们能够为了他们自己的权利抗争,可是老百姓们到底都有哪些权利,王莽自己也说不清,两千年来的儒家也没说清。孟子曰: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听上去冠冕堂皇,然而却经不起较真,受累问孟夫子一句,民为重,到底有多重?计量单位是什么,用什么秤,怎么称,谁来称?想来孟夫子大抵也只能报以怒斥:小子无状!这重嘛,乃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
类似的漂亮话,史上多有,儒家经典上说,皇帝诏书上说,士大夫奏章上也说,但这些漂亮话通常说完算数,不能量化,更不能执行,唯一的作用,就是抚慰一下说话人那尚且残存的良心。于是乎,仁义道德多烂然显著于高文大册之间,而小民终疾苦蹙然于穷檐败壁之下。于是乎,民为重,沉于地,千人踩,万人踏。君为轻,高在天,变成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对于这些漂亮话,老百姓一开始或许还相信,但慢慢就死了心,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将欲望压抑到了最低,压抑到了只剩下生存欲。尚书·康诰》曰:“若保赤子,唯民其康乂。”在这里,周公将百姓们比喻为婴儿,想想也有道理,婴儿只要吃饱喝足,就会乖乖睡觉,不来和大人们闹了,更不会提多余的要求,说什么我要发财,我要泡妞,我要开名车,我要饮花酒。然而,老百姓们毕竟不是婴儿,而且就算是婴儿,婴儿肚子饿了,也免不了要大哭大闹,叫大人们不得安生!
【No。6 反贼贼多】
王莽自称帝以来,有大膨胀,以自己为磅礴而挥洒的存在,每自捉其发,提置于万丈高空,冷眼向洋,张口吃风。今年原本是他做皇帝的第十二个年头,也是新朝的第一个本命年,谁知道却风声雨声,声声无情,家事国事,事事揪心,王莽于是觉出了孤独和悲壮,觉出了空旷和瘙痒,在他悲观的眼里,上天抛弃了他,百姓背叛了他,而这更让他心中平添了一股殉道者的凄凉。
王莽是自信的,他知道自己的分量,他也坚信真理只掌握在他一个人手上。五百年乃有圣人出,上一个圣人是孔子,五百余年过去了,如今的圣人则轮到了他王莽。谁都可以失败,但他王莽绝对不能失败,一旦他失败,不仅是他个人的损失,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