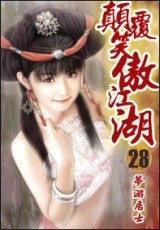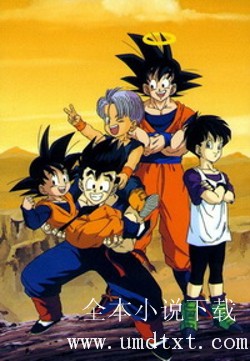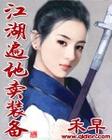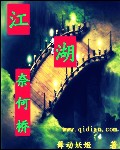食在江湖-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然而,这一天我走在街的花坛旁,我忽然发现,这干渴得如同水泥灰的泥土,居然萌出几点新绿,且自信地开出几朵小花,黄灿灿的小花。它们在春天的阳光照临下,竟是透着那么一份惊喜,它们的根就扎在这块毫无湿润的土地上。它们,是以怎样的毅力在这样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呵?我索性停下步来,俯身凝视着一朵小花,它向我微笑着,因它的缘故,我发现阳光要美妙得多。这样一朵小花,它有两片小小的叶子,像两只举起欢呼的小手,有一根小茎,极绿,在春风吹拂里颤栗不止,它整个的形像微小而精致,令人不忍触碰。它便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生命,一朵开放在春天里的小小花朵,它猛然地让我感悟到生命力的强大。在如此干燥的土地上,扎根,吸收到哪怕一丁点儿的养份,极顽强地生长出来,还绽开小小花朵,捧起即便是这样微小的颜色,微小的喜悦,但它终是这春天里的花朵的一种呵!它的呈现,妩媚了我心头的枯燥的北国的春天。
一朵小花,它竟拂去我心头的冷寂和积尘,它把这一捧小小的美丽托送给我,它让我在它的面前思之不已。我们的生命,究竟有没有一朵小花强大?有它的从容而饱含激情?有没有它那么一点点亮色?我还呼吸到小花儿的淡淡的一缕清香,它在阳光里暗放。终于是看得久了,我用心灵轻轻地抚摸它,我的心刹时也芬芳,即便北国这样的土壤,它亦是要养育一种花朵呵,所谓的荒凉,原来竟是心灵所生,真正的土地,也总是会有花朵的,会有这样小小的花朵。我就用这朵小花拂去我孤旅的疲惫,且要把它移植到我的文字里,让我的文字也暗香浮动。
读修游龄先生之乐
游修龄先生的文章读来颇有意味,便是见到一篇拜读一篇,很有趣味,相比较之北大的长老们,身为浙江农业大学教授的游先生名气是要逊了,到是学识可能高出一筹。游修龄先生近时专事指谬,早先读他一篇文章介绍,一个地方发掘出来一枚花生化石,便写出了论文,轰动一时,此地花生种植史有一万年,游先生的意见是不可能,不足旁证。后再测定,方知是现代陶瓷花生,出一个大笑话。
今读游先生另一篇文章,《随心所欲的茶文化“考古”和“论证”》,说的是杭州出版社新出版一本《茶魂之驿站》,序言中说:“杭州有着极久远的茶文化史。代代传承,源远流长,据一些茶学研究者认定,早在八千年前,跨湖桥人就有饮茶的习惯。”论文中,以一粒跨桥遗址发掘的炭化种子和一个陶釜碎片为证,说种子就是茶种,陶片就是茶壶,这未经鉴定的事物已经为证了,游先生说这么做学问是不对的,游先生又指出:西湖在距今约万年前还是一个海湾,
经历着不断的潮沼化和陆化,现代西湖形成的年龄,约在距今 1860……1850
年,即东汉年间(公元25~220年)(周峰主编《南北朝前古杭州》,233…237
页,1997,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的前身是东汉时的钱塘县。那时的钱塘县,在现今西湖之西、北至岳坟、西去灵隐一带,三面为山,一面滨湖,湖外尽是沙滩,不过是个山中的小县。杭州脱离山中小县的地位,始于隋开皇九年(589年),改钱塘郡为杭州,移治余杭,后20
年,到隋炀帝开通江南运河,以杭州为大运河的起点,地位才逐步显要起来。
这便不用说八千年前跨湖桥人就有饮茶的习惯了,八千年前那里是海呀。游先生再指出《茶》文更多荒谬处,不论。游先生亦对《中国古代动物学史》(郭
郛,'英'李约瑟,成庆泰著)中的“在圃渔”质疑,即“圃”不可以简单作池塘解,圃仍保留甫的古义,指繁茂的泽薮,即沼泽浅水之地,将“在圃渔”认定为殷商有池塘养鱼不对,不过,游先生不否殷商时代即已人工养鱼,因为他也没有证据证明那时候没有人工养鱼,只是强调“在圃渔”不足以支持殷商即已人工养鱼的论点。
似乎没有什么能够难倒游先生,很神奇,游修龄先生出生于1920年5月9日,浙江省温州市人,1943年7月毕业于前国立英士大学农学院。游修龄先生有“愤青”级的激情,亦不论谁人,有谬必指,则又有大师级的水平,尤其古汉语之造诣深厚,举凡在论文中玩文字之法者,皆被其揭穿。农学界的博士如果今有日子不好过的感觉,那可能就是有游修龄在。上次去杭州,就打听有人与浙江农业大学熟否,惜之,好像杭州人不大知道游修龄,这可能大家都不熟农学有关。
。。
李白与酒和茶(1)
李白善饮,这不用怀疑,千年以降,饮者留名,唯有李白。相比较可以上得台面的人物,曹操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至于武松十八大碗,那就算不上风流人物了,只能称得上好汉。但是好汉,纵观古今中外历史,都属配角角色。李白不然,在说到李白这个人物的时候,往往大唐天子也不过给他做了配角。至今可查阅的李白的诗,有1500首,据郭沫若考证其中写到酒者,占16%,显然是诗酒不离的了。然而,唐朝诗人能饮,亦不独李白,他的诗友杜甫有诗1400首,写到酒者占20%,说起来杜甫也爱喝两口,酒量绝不会弱,只是李白的酒名在先,将杜甫这样一个伟大的酒圣给活活掩盖了。杜甫酒名被李白掩盖了不说,且还使劲替李白大扬酒名,杜甫在《饮中八仙》写道:“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李白能酒,杜甫岂不能之?是不是历史评价系统太过偏差,独钟李白?估计这里面奥妙在于,李白的诗须由酒来催生:诗,冒着酒气;人,在酒间的醉态中写作,简称为醉写。杜甫可能酒量比李白还大,但他不醉写,或不常醉写,他的大多数诗是明白时候写作,属于醒写,所以杜甫就失去了诗酒互为烘托机会,写诗是写诗,喝酒是喝酒,这样导致世间人都不知道杜甫还能喝酒,多少对杜甫不公道。话再说回来,李白虽然做过翰林院待召,从其一生的写作生涯考察,他是一个自由撰稿人,杜甫不是,他有官职,常有公务在身,能喝也要保密,因此尚不能完全算历史对杜甫不公道。
显然是这样,如杜甫所言,李白斗酒诗百篇,这个斗字,只说它是斗争之斗,只要李白一斗酒,他的诗情就如三峡之水滔滔流涌,那一个斗字,确切判断是一个动词,不是量词,坊间将其作量词解,拿酒来使劲地灌文人墨客,不过是玩了一个修辞上的技法,历史上也没有拿斗来做酒量具的,十八碗、十八坛、十八缸……这么论者偶有所见。李白斗酒诗百篇,此百篇则是形容语词。否则,以李白的1500首诗折酒量,一斗一百篇计,其一生不过是喝了150斗酒而已。设若真的以斗量酒,一生中能喝150斗酒的人确大有人在,与酒仙之称谓应该相差甚远,想那武松不过翻一个景阳冈而已,就喝了十八大碗。像武松这样一个好汉豪杰,一生中又该翻越过多少座“景阳冈”?
李白是斗酒,而不是拿斗装酒喝,也不是喝一斗两斗酒那样计量,这个问题应该可以不再纠缠,而斗酒之传统,至今也保持非常完好,可区别的是斗法斗技之不同也。但是,李白到底喝的什么酒?千百年来,仍是一个谜,白酒肯定不是的,李白的名也有一个白,此白非彼白。坊间盛传,李白喝的酒不过是低度米酒,能喝却不能以为他真的酒量大,让李白来喝56度二锅头试试,看他还能否斗酒诗百篇?确乎如此,有一年,我去了神农架的房县,这地方旧称房川,也叫卢陵州,就是武则天把她的亲儿子李显流放来的地方,这地方现在还沿袭喝一种皇酒。皇酒,卢陵王从长安带来的宫廷酒,还包括360种酒规。
斗酒,须有酒规,360种酒规,现在神农架一带仍然流传,平常席间,总会使用其中几种,比如转杯,对面笑,跳一跳,赶麻雀等,这些斗酒的玩法,在神农架呆上十天半月,大约是可以略知一二。比较遗憾的是皇酒一直深藏在神农架深老林间,没有流布神州大地的亿万酒肆,让今天的芸芸众生一品大唐帝国的酿造风味。
我在神农架被灌醉的次数不好统计了,总之不会少于十次。皇酒之色,呈浅茶色,入口微甜,渐渐弥散酒香,较之绍酒,同是米酒的皇酒,就没有绍酒后缀的酸涩味,皇酒入口绵甜,淡淡的酒香漫溢,再喝、再喝依然。然而,它的后劲不可小视,或者当场就让人飘起来。伟大的皇酒就有如此之妙,喝得人飘起来,还可以继续喝,那妙处必须亲自去喝,以神农架的仙境之水加稻米酿造,生产环境与唐朝也会相差不远。
饮罢皇酒,真的就相信李白喝的那种米酒,与现实中的种种酒都有不同,唐朝的酒没有失传,只在小众当中流行而已。神农架的世世代代山民,饮大唐皇酒,讲大唐酒规,他们居于山中,常向来客讲卢陵王,讲薛刚,边讲边敬客人以皇酒。话说回来,皇酒度数不高,豪饮必醉的规律却逃不掉,往往是每豪饮的结果都醉,主要是它太好入口了,尤口感之甘、绵、香、清,清是此酒尚未浑浊,如神农架之山水。
世上有斗酒,斗茶主要反映在宋代,然而茶在大唐时代就盛行了,不过,尚处于取其药用价值阶段,煮茶还须加上诸多佐料,然只要盛行,李白遇到喝茶的机会应为不少,但通观了许多茶书,历史上那么多的文人墨客,只有李白不喝茶。李白不喝茶,不好取证是为什么,个人爱好么,那个唐朝的陆羽,不是也不喝酒么?
今年偶翻茶经,忽然见到李白叙茶,这事情险些颠覆了我对李白的印象,到底世上的酒仙也饮茶。据那份茶经介绍,李白还给人茶叶著文《李太白集•;赠族侄僧中孚玉泉仙人掌茶序》:余闻荆州玉泉寺近青溪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窟多玉泉交流。中有白蝙蝠,大如鸦。按《仙经》:“蝙蝠,一名仙鼠。千岁之后,体如白雪。栖则倒悬,盖饮乳水而生长也。”其水边处处有茗草罗生,枝叶如碧玉。惟玉泉真公常采而饮之,年八十余岁,颜色如桃花,而此茗清香滑熟异于他茗,所以能还童振枯,扶人寿也。余游金陵,见宗僧中孚示余数十片,卷然重桑,其状如掌,号为“仙人掌”茶。盖新出乎玉泉之山,旷古未觏。因持之见贻,兼赠诗,要余答之,遂有此作。俾后之高僧大隐,知“仙人掌”茶发于中孚禅子及青莲居士李白也。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李白与酒和茶(2)
一种生于玉泉寺边上的仙人掌茶,原来李白也没见过,著文则因中孚给了他数十片茶叶样品,我开始怀疑是否出自李白之笔,但一想到“桃花流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就能理解李白毕竟不是神仙。
李白不属茶道中人,给一种茶叶写这么一段广告文字,不算离奇。但是说什么旷古没有遇见过,珍罕茶品,那不是李白风格,给世界贡献一些情趣罢了。可惜的是,唐人编的李白集未能流传下来,北宋编有《李太白文集》30卷,刻于苏州,即“苏本”,后人据苏本翻刻了蜀本,蜀本为现存最早的李白集。康熙年间缪曰芑据蜀本翻刻,称缪本。后面是为李白集作注者,南宋杨齐贤有《李翰林集》25卷,今人瞿蜕园、朱金城的《李白集校注》是迄今为止李白集注释中最详备的。
李白与茶,大约就这么一个段子,终究是一个酒仙,茶就让郑板桥们去喝罢,郑板桥一喝茶,端的喝出个“难得糊涂”,这是意想不到的。
燕坐华榭(1)
一直喜欢磨山。南来北往的奔走,很多年没有来磨山了,黄慎如说,去磨山吃鱼?我说去,他说磨山有臭鳜鱼,非常值得一品。我想,在那样的风景里,喝杯白开水也是很有情趣的吧?我记得跟程绍国在雁荡山大龙湫旁的茶亭里,一个人喝一杯雁荡云雾,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秀丽的风光,优雅的心情,时隔两年仍然记忆犹新。
车沿着长堤驶向磨山,一边是林荫大道,路旁枝繁叶茂,清凉且绿意葱葱,一边是东湖的大水,水光漾动,烟波浩淼,武昌东湖的面积为杭州西湖的六倍,尤东湖的水鸟多,每每看到东湖堤旁护堤木桩上孤立的水鸟,不禁哑然失笑,不能想象一个没有水鸟的湖,它是一个什么湖。黄慎如开着他的别克车,他说每走这一段路,心里都有一种感觉。我以为,这样的路骑摩托走比较好,最好是坐马车,且要慢悠悠地走,夏天时,南京的张久先生开着宝莱也这么拉着我往明孝陵转了一圈,但是走了一趟总比没有走好得多。
还是在地质队的时候来过几次磨山,叫做春游吧,过五四青年节,那时候,我找裁缝用灰涤卡布做了一件五四青年装,刻意要做大一些,穿着松垮垮的,要那一种感觉。后来,我把它也带到了北京,现在穿不得了,事实上,每个人都回不到历史中。
磨山有很好的梅花,堪称中国梅苑之最,但是在五四青年节看到的花,都是桃花。花朵差不多,然时间不一样,梅瘦桃肥,我觉得一个人保持良好的赏花心情是一种造化,我有几年时间都设想拍出一本植物花集,自己配文字,然都没有实现,我以为最好从野生植物开始,园林植物的花,怎么看来都有一样媚态。比如看梅花,真正好的梅花,还是小时候在赣南老家看的,学校有两株梅树,平时葱葱郁郁,入冬落尽了叶子,我上小学那年,下了雪,雪后的早晨大地上泛着白光,我去学校转悠,忽然看到梅花开了满树,铁丝般的枝条上,猛烈地爆开了许多娇嫩的花朵,它们迎着寒风怒放。可以想见,我后来读到课本中那首诗“笑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它在丛中笑”,我脑海里就出现那满树梅花。但是,我却觉得梅花不一定有老师讲的城府那么深,它不过是喜欢雪罢了,跟小孩子一样,对雪又怕冷又喜欢,人每次看到大地上铺着白茫茫的雪,就忍不住想脱掉鞋子,打赤脚在上面走一走。又爱又怕,雪天风中的梅花,惊喜地开放且冻得哆嗦,梅花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