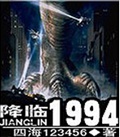大江大海1949-第1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亲爱的,我百思不解的是,这么大规模的战争暴力,为什么长春围城不像南京大屠杀一样有无数发表的学术报告、广为流传的口述历史、一年一度的媒体报导、大大小小纪念碑的竖立、庞大宏伟的纪念馆的落成,以及各方政治领袖的不断献花、小学生列队的敬礼、镁光灯下的市民默哀或纪念钟声的年年敲响?
为什么长春这个城市不像列宁格勒一样,成为国际知名的历史城市,不断地被写成小说、不断地被改编为剧本、被好莱坞拍成电影、被独立导演拍成纪录片,在各国的公共频道上播映,以至于纽约、莫斯科、墨尔本的小学生都知道长春的地名和历史?三十万人以战争之名被活活饿死,为什么长春在外,不像列宁格勒那么有名,在内,不像南京一样受到重视?
于是我开始做身边的“民意调查”,发现,这个活活饿死了三十万到六十万人的长春围城史,我的台湾朋友们多半没听说过,我的大陆朋友们摇摇头,说不太清楚。然后,我以为,外人不知道,长春人总知道吧;或者,在长春,不管多么不显眼,总有个纪念碑吧?
可是到了长春,只看到“解放”的纪念碑,只看到苏联红军的飞机、坦克车纪念碑。
我这才知道,喔,长春人自己都不知道这段历史了。
这,又是为了什么?
帮我开车的司机小王,一个三十多岁的长春人,像听天方夜谭似地鼓起眼睛听我说起围城,礼貌而谨慎地问:“真有这回事吗?”然后掩不住地惊讶,“我在这儿生、这儿长,怎么从来就没听说过?”
但是他突然想起来,“我有个大伯,以前是解放军,好像听他说过当年在东北打国民党。不过他谈往事的时候,我们小孩子都马上跑开了,没人要听。说不定他知道一点?”
“那你马上跟大伯通电话吧,”我说,“当年包围长春的东北解放军,很多人其实就是东北的子弟,问问你大伯他有没有参与包围长春?”
在晚餐桌上,小王果真拨了电话,而且一拨就通了。
电话筒里大伯声音很大,大到我坐在一旁也能听得清楚。他果真是东北联军的一名士兵,他果真参与了围城。
“你问他守在哪个卡子上?”
小王问,“大伯你守在哪个卡子上?”
年轻的于祺元,在长春。
“洪熙街,”大伯用东北口音说,“就是现在的红旗街,那儿人死得最多。”
大伯显然没想到突然有人对他的过去有了兴趣,兴奋起来,在电话里滔滔不绝,一讲就是四十分钟,司机小王一手挟菜,一手把听筒贴在耳朵上。
一百多公里的封锁线,每五十米就有一个卫士拿枪守着,不让难民出关卡。被国军放出城的大批难民啊,卡在国军守城线和解放军的围城线之间的腰带地段上,进退不得。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野地里,一望过去好几千具。
骨瘦如柴、气若游丝的难民,有的抱着婴儿,爬到卫士面前跪下,哀求放行。“看那样子我也哭了,”电话里头的大伯说,“可是我不能抗命放他们走。有一天我奉命到二道河去找些木板,看到一个空房子,从窗子往里头探探,一看不得了,一家老小大概有十个人,全死了,躺在床上的、趴在地上的、坐在墙跟的,软绵绵扑在门坎上的,老老小小,一家人全饿死在那里。看得我眼泪直流。”
林彪在五月中旬就成立了围城指挥所,五月三十日,决定了封锁长春的部署:
(一)堵塞一切大小通道,主阵地上构筑工事,主力部队切实控制城外机场。
(二)以远射程火力,控制城内自由马路及新皇宫机场。
(三)严禁粮食、燃料进敌区。
(四)严禁城内百姓出城。
(五)控制适当预备队,沟通各站联络网,以便及时击退和消灭出击我分散围困部队之敌……
(七)……要使长春成为死城。
解放军激励士气的口号是:“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蒋匪军困死在城里。”十万个解放军围于城外,十万个国军守于城内,近百万的长春市民困在家中。不愿意坐以待毙的人,就往外走,可是外面的封锁在线,除了炮火器械和密集的兵力之外,是深挖的壕沟、绵密的铁丝网、危险的高压电网。
伊通河贯穿长春市区,草木葱茏,游鱼如梭,是一代又一代长春人心目中最温柔的母亲河,现在每座桥上守着国民党的兵,可出不可入。下了桥,在两军对峙的中间,形成一条三、四公里宽的中空地带,中空地带上尸体一望无际。
到了炎热的七月,城内街上已经有弃尸。眼睛发出血红的凶光、瘦骨嶙峋的成群野狗围过来撕烂了尸体,然后这些野狗再被饥饿的人吃掉。
于祺元是《长春地方志》的编撰委员,围城的时候只有十六岁,每天走路穿过地质宫的一片野地到学校去。野地上长了很高的杂草。夏天了,他开始闻到气味。忍不住跟着气味走进草堆里,拨开一看,很多尸体,正在腐烂中。有一天,也是在这片市中心的野地里,远远看见有什么东西在地上动。走近了,他所看见的,令他此生难忘。
那是被丢弃的赤裸裸的婴儿,因为饥饿,婴儿的直肠从肛门拖拉在体外,一大块;还没死,婴儿像虫一样在地上微弱地蠕动,已经不会哭了。
“什么母爱呀,”他说,“人到了极限的时候,是没这种东西的。眼泪都没有了。”
国军先是空运粮食,共军打下了机场之后,飞机不能降落,于是开始空投,用降落伞绑着成袋的大米,可是降落伞给风一吹,就吹到共军那边去了。
“后来,国军就开始不用伞了,因为解放军用高射炮射他们,飞机就从很高的地方,直接把东西丢下来,还丢过一整条杀好的猪!可是丢下来的东西,砸烂房子,也砸死人。”
“你也捡过东西吗?”我问他。
“有啊,捡过一大袋豆子。赶快拖回家,”他说,“那时,守长春的国军部队与部队之间,都会为了抢空投下来的粮食真枪真火对拚起来呢。后来规定说,空投物资要先上缴,然后分配,于是就有部队,知道要空投了,先把柴都烧好了、大锅水都煮开了,空投一下来,立即下锅煮饭。等到人家来检查了,他两手一摊,说,看吧,米都成饭了,要怎样啊?”
于祺元出生那年,满州国建国,父亲做了溥仪的大臣,少年时期过着不知愁苦的生活,围城的悲惨,在他记忆中因而特别难以磨灭。
“围城开始时,大家都还有些存粮,但是谁也没想到要存那么久啊,没想到要半年,所以原来的存粮很快就吃光了。城里的人,杀了猫狗老鼠之后,杀马来吃。马吃光了,把柏油路的沥青给刨掉,设法种地,八月种下去,也来不及等收成啊。吃树皮、吃草,我是吃过酒……的,造酒用的……,一块一块就像砖似的。酒……也没了,就吃酒糟,干酱似的,红红的。”
“酒糟怎么吃?”
“你把酒糟拿来,用水反复冲洗,把黏乎乎那些东西都冲洗掉,就剩一点干物质,到太阳底晒,晒干了以后,就像荞麦皮似的,然后把它磨碎了,加点水,就这么吃。”
有一片黄昏的阳光照射进来,使房间突然笼罩在一种暖色里,于老先生不管说什么,都有一个平静的语调,好像,这世界,真的看得多了。
我问他,“那么——人,吃人吗?”
他说,那还用说吗?
他记得,一个房子里,人都死光了,最后一个上吊自尽。当时也听见过人说,老婆婆,把死了的丈夫的腿割下一块来煮。
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林彪等人给毛泽东发了一个长春的现场报告:
……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与(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
……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的。饥民们对我会表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
十月十七日,长春城内守军六十军的两万六千人缴械。
十月十九日,在抗战中赢得“天下第一军”美名的新三十八师、新七军及其它部队,总共三万九千名国军官兵,成为俘虏;所有的美式装备和美援物资,全部转给解放军。
守城的国军,是滇军六十军,曾经在台儿庄浴血抗日、奋不顾身;是第七军,曾经在印缅的枪林弹雨中与英美盟军并肩作战蜚声国际,全都在长春围城中覆灭。
东北战役的五十二天之中,四十七万国军在东北“全歼”。
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出对共军前线官兵的贺电:
……热烈庆祝你们解放沈阳,全歼守敌……在三年的奋战中歼灭敌人一百余万,终于解放了东北九省的全部地区……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与关内人民和各地人民解放军亲密合作,并肩前进,为完全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驱逐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解放全中国而战!
在这场战役“伟大胜利”的叙述中,长春围城的惨烈死难,完全不被提及。“胜利”走进新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代代传授,被称为“兵不血刃”的光荣解放。
32,死也甘心情愿地等你
十月十九日城破以后,解放军在凌乱中找到一袋又一袋国军官兵在围城期间写好了、贴了邮票,但是没法寄出的信。里头有很多很多诀别书,很多很多做最后纪念的照片。
林彪围城指挥部决定了“使长春成为死城”的所有部署规划,是在五月三十日,我读到的这封信,写在两天后。“耕”,写给在家乡等候他的深情女子:
芳:
……生活是这样地压迫着人们,穷人将树叶吃光了,街头上的乞丐日益增多……我因为国难时艰,人的生死是不能预算的,但在我个人是抱着必死的信念,所以环境驱使着我,我不得不将我剩下的几张照片寄给你,给你做为一个永远的纪念……我很感谢你对我用心的真诚,你说死也甘心情愿地等着我,这话将我的平日不灵的心竟感动了,我太惭愧,甚至感动得为你而流泪……我不敢随便的将你抛弃,我的心永远的印上了你对我的赤诚的烙印痕,至死也不会忘记你……
我已感到的是我还能够为社会国家服务,一直让我咽下最后一口气方罢。这是我最后的希望……我的人生观里绝对没有苛刻的要求,是淡泊的,是平静而正直的。脱下了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民,尽我做国民的义务。
耕手启
六月一日九时第五十二号
这应该是“耕”在战场上写的第五十二封信了。端庄的文体,使我猜想,“耕”会不会是一九四四年底毅然放下了学业、加入“十万青年十万军”去抗日的年轻人之一呢?
那个“芳”,终其一生都没有收到这封信。
离开于老先生的家,我又回到人民广场;那顶着苏联战机的纪念塔,在中午的时分显得特别高大,因为阳光直射,使你抬头也看不见塔的顶尖。我手上抓着几份旧报纸,报导的都是同一件新闻。二零零六年六月四日的报导——围城五十多年之后的事了:
新文化报(本报讯)
“每一锹下去,都会挖出泛黄的尸骨。挖了四天,怎么也有几千具!”二日清晨,很多市民围在长春市绿园区青龙路附近一处正在挖掘下水管道工地,亲眼目睹大量尸骨被挖出……
成百成千的白骨,在长春热闹的马路和新建的高楼下面。人们围起来观看,老人跟老人窃窃私语,说,是的是的,一九四八年围城的时候……
那个年轻的“耕”——他的尸骨,是否也埋在这满城新楼的下水道下面呢?
解放军在十一月一日下午攻入沈阳。“大批大批徒手的国军,像一群绵羊似的,被赶入车站前剿匪总部军法处大厦内集中”。马路上到处是断了手脚、头上缠着肮脏渗血的绷带、皮肉绽开的伤口灌脓生蛆的国军伤兵。
二十八岁的少校政治教官郭衣洞,后来的柏杨,也在沈阳,正准备开办《大东日报》。他看着大批的解放军兴高采烈地进城,穿着灰色棉军服,有的还是很年轻的女性,挤在卡车里,打开胸前的钮扣给怀里的婴儿喂奶。
头几天,解放军对“蒋匪”采宽大政策,准许国军士兵“还乡生产”。于是柏杨穿上国军的军服,逃出沈阳。在山海关附近,看见一个国军,清澈的眼睛大大的,是新六军的少尉军官,断了一条腿,鲜血不断地往下流,双肩架在拐杖上,走一步,跌一步,跌了再挣扎撑起来走。是一个湖南人,对年轻的柏杨说,“我爬也要爬回家,家里还有我妈妈和妻子”。
他,会不会是“耕”呢?
33,卖给八路军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解放军的士兵踩着大步进入沈阳。三年前苏军当众奸杀妇人的沈阳火车站前,几乎是同一个地点,现在地上有一个草席盖着的尸体,尸体旁地面上草草写着一片白色粉笔字:
我是军校十七期毕业生,祖籍湖南,姓王,这次战役,我没有看见一个高级将领殉职,我相信杜聿明一直在东北,局面不会搞得如此糟。陈诚在沈阳,也不会弃城逃走。所以现在我要自杀,给沈阳市民看,给共产党看,国军中仍有忠烈之士。
国军中,当然有“忠烈之士”。譬如说,抗日战争中几乎没有一场重大战役没有打过的“王牌将军”张灵甫,一九四七年被围困在山东临沂的孟良崮——是的,台北有临沂街,它跟济南路交叉。整编七十四师深陷于荒凉的石头山洞中,粮食断绝,滴水不存。美式的火炮钢管发烫,需水冷却,才能发射,士兵试图以自己的尿水来浇,但是严重脱水,人已经无尿。伤亡殆尽,在最后的时刻里,张灵甫给妻子写下诀别书,然后举枪自尽。
十余万之匪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趋恶化,弹尽援绝,水粮俱无。我与仁杰决战至最后,以一弹饮诀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