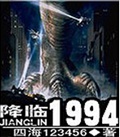大江大海1949-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大概是在四点多钟太阳还没下来,这时就看着有两个老太太——因为我们住的那个村庄对面是有梯田的,干的梯田——我看这两个老太太不能走路了,从梯田那边用屁股往下滑,碰在那个堑子,碰了以后往下滑。我一看就知道是我母亲,我就大喊说,“我娘来了,我要去。”
那个门口站卫兵的马上用枪一挡,我说那个是我母亲,我说我得跑过去接她。他说不成。我说,那是我母亲,她不能走路,她眼睛看不见啊……
龙:管管——你不要哭……
管:……我母亲就一路跌、一路爬、一路哭到了眼前。我对母亲说,我跟他们讲好了,就是给他们挑东西、挑行李,挑完行李就回家,你放心好了。我很快就回家。
我就拚命骗我母亲。
我母亲就给我一个小手帕,我一抓那个小手帕,就知道里面包了一个大头,就一块大头。这一块大头对我们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父亲那时候穷得只有两块大头。那一块大头给了我以后,家里就只剩一块大头。
我就把这个手帕推给我母亲,说,“你拿去,不成,这个不成。”她当然是哭哭啼啼,一直要我拿钱,说,“你拿钱可以买。”我心里清清楚楚,这一路都是阿兵哥,阿兵哥会把你的钱拿走,而且你不可能回家了嘛,对不对。但是你给这个老太太这样讲,她根本不听。她还是把手帕——
龙:管管,你不要哭……
管:我一直在骗我妈,说我给他们挑了东西就回家——
龙:管管你不要哭……
管:……马上就要出发了,我想我完蛋了。
龙:有多少人跟你一起被抓?
管:应该有一个排,二十多、三十个左右,统统都是被抓来的。两三点钟吧,就说叫我们起来刷牙走了。我心里怕死了,可能要去打仗了。我被抓的单位是八二炮连,每一人挑四发炮弹。
龙:一个炮弹有多重?
管:一个炮弹,我算算有七斤十二两。行军的时候,他们是两个阿兵哥中间夹着一个被抓来的挑夫,他们讲“你跑我就开枪”,其实后来我们知道,他们根本不会开枪,因为撤退是悄悄地撤退,不准许出声的。我们完全可以逃走,可是那时候谁也不敢冒险哪。
龙:管管那时你是一个人肩挑两边炮弹呢,还是前后两个人挑中间的炮弹?
管:不是,我一个人挑四发,一边各绑两发。
龙:然后呢?
管:然后就走,天亮的时候,从郊区走到了青岛。我当时穿双鞋,是回力鞋,跟我现在这球鞋差不多。要过一条桥的时候,挑着炮弹,突然滑倒了。
龙:慢点啊,管管,你家里怎么买得起回力鞋给你?
管:我打工,譬如美军第六舰队在青岛的时候,我就到军营附近卖花生,还卖一些假骨董,譬如说女生那个三寸金莲的鞋啊,还有卖日本旗,到总部里面去找日本旗来卖。
龙:挑着四发炮?
管:我挑了四发炮弹,然后就在海泊桥过桥时“砰”摔了一跤。我那时候以为炮弹会爆炸啊,吓死我了。这时长官过来,啪啪给我两个耳光。后来我才知道这炮弹不会爆炸,但我吓死了,你看压力有多大。就这样到了青岛码头。就这样……到了台湾。
17,栖风渡一别
粤汉铁路是条有历史的老铁路了,一八九八年动工,一九三六年才全线完成,也就是说,在戊戌政变的时候开工,到抗战快要爆发的时候完工,花了三十八年,总长一零九六公里。
从武昌南下广州,在湖南接近广东交界的地方,粤汉铁路上有个很小的车站,叫栖风渡。中央研究院院士、历史学家张玉法,记得这个小站。
十四岁的张玉法和八千多个中学生,全部来自山东各个中学,组成联合中学,跟着校长和老师们,离开山东的家乡,已经走了一千多公里的路。搭火车时,车厢里塞满了人,车顶上趴满了人,孩子们用绳子把自己的身体想方设法固定在车顶上,还是不免在车的震动中被摔下来。火车每经过山洞,大家都紧张地趴下,出了山洞,就少了几个人。慌乱的时候,从车顶掉下来摔死的人,尸体夹在车门口,争相上车的人,就会把尸体当作踏板上下。
八千多个青少年,背着行囊。所谓行囊,就是一只小板凳,上面迭条薄被、一两件衣服,整个用绳子绑起来,夹两支筷子。到了没有战争的地方,停下来,放下板凳,就上课。通常在寺庙或是祠堂里驻点,夜里睡在寺庙的地上,铺点稻草;白天,每个人带着一个方块土板,坐在庙埕的空地或土墙上,把老师围在中心,就开始听讲。用石灰,或甚至石块,都可以在土板上写字。
我听着听着不免发呆:这是什么样的文明啊,会使你在如此极度的艰难困顿中却弦歌不辍?
饿了,有时候到田里挖芋头吃,带着土都吃;没得吃的时候,三三两两就组成一个小队伍,给彼此壮胆,到村子里的人家去讨食。有点害羞,但是村人开门看到是逃难来的少年,即使是家徒四壁的老爷爷,也会拿出一碗粥来,用怜惜的眼光看着饥饿的孩子们。
湖南人对外省人最好,张玉法说,因为湖南人几乎家家都有自己的儿子在外面当兵——可能是国军,也可能是解放军,所以他们常常一边给饭,一边自言自语说,唉,希望我的儿子在外面,也有人会给他饭吃。
一九四九年端午节,大军海上撤退,管管在青岛被抓夫的当天,八千多个山东少年到了栖风渡。长沙也快要开战了,他们只好继续往南,计划到广州。到了广州然后呢?没有人知道。
栖风渡是个很小的站,看起来还有点荒凉,可是南来北往的火车,在这里交错。少年们坐在地上等车,一等就是大半天,小小年纪,就要决定人生的未来。搭南下的车,离家乡的父母就更遥不可及了,而且广州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一个举目无亲的地方。搭北上的车,马上就回到父母身旁,但是一路上都是炮火燃烧的战场,一定会被抓去当兵,直接送到前线,不管是国军还是解放军。战死或被俘,总归到不了父母的面前。
很多少年少女,就在那荒凉的车站里,蹲下来痛哭失声。
玉法的二哥,十七岁,把弟弟拉到一旁,说,我们两个不要都南下,同一命运,万一两个人都完了的话,父母亲就“没指望了”,所以把命运分两边投注;我北上,你南下。
二哥决定北上到长沙报考,到处都是孙立人招考青年军的布告。
北上的火车先到,缓缓驶进了栖风渡;张玉法看着亲爱的哥哥上车,凝视着他的背影,心里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孤独。
五十年以后,自己的头发都白了,玉法才知道,二哥这一伙学生,没抵达长沙;他们才到衡阳,就被国军李弥的第八军抓走了。跟着第八军到了云南,跟龙云的部队打仗,二哥被龙云俘虏,变成龙云的兵,跟解放军打仗,又变成解放军的俘虏,最后加入了解放军。但是解放军很快地调查发现他是地主的儿子,马上遣送回家,从此当了一辈子农民。
在栖风渡南下北上交错的铁轨旁,深思熟虑的二哥刻意地把兄弟两人的命运错开,十四岁的小弟张玉法,确实因此有了截然不同的命运,但是,那纯是偶然。
八所山东中学的八千个学生,从一九四八年济南战役、徐蚌会战时就开始翻山越岭、风雨苦行,一九四九年到达广州时,大概只剩下五千多人。广州,也已经风声鹤唳,有钱也买不到一张船票了。为了让五千个学生能够离开广州到安全的台湾,校长们和军方达成协议:学生准予上船,送到澎湖,但是十七岁以上的学生,必须接受“军训”。
七月四日,几千个学生聚集在广州码头上,再度有一批少年,上了船又走下来,走了下来又回头上船;于是危难中命运再度分开“投注”:如果姊姊上了船,那么妹妹就留在码头上。
巨舰缓缓转身时,那倚在甲板上的和那立在码头上的,两边隔空对望,心如刀割。军舰驶向茫茫大海,码头上的人转身,却不知要走向哪里。
上了船的少年,不过一个礼拜之后,就面临了人生第一次惨烈的撞击。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三日,澎湖。
年龄稍长但也不满二十岁的学生,以耳语通知所有的同学,“他们”要强迫我们当兵,我们今天要“走出司令部”。同学们很有默契地开始收拾行囊,背着背包走出来,却发现,四面都是机关枪,对准了他们。
所有的男生,不管你几岁,都在机关枪的包围下集中到操场中心。司令官李振清站在司令台上,全体鸦雀无声,孩子们没见过这种阵仗。张玉法说,这时,有一个勇敢的同学,在队伍中大声说,“报告司令官我们有话说!”然后就往司令台走去,李振清对一旁的卫兵使了个眼色,卫兵一步上前,举起刺刀对着这个学生刺下,学生的血喷出来,当场倒在地上。
张玉法个子矮,站在前排,看得清清楚楚刺刀如何刺进同学的身体。看见流血,中学生吓得哭出了声。
不管你满不满十七岁,只要够一个高度,全部当兵去。士兵拿着一根竹竿,站到学生队伍里,手一伸,竹竿放下,就是高矮分界线。张玉法才十四岁,也不懂得躲,还是一个堂哥在那关键时刻,用力把他推到后面去,这懵懵懂懂的张玉法才没变成少年兵。
个子实在太小、不能当兵的少年和女生,在一九五三年春天被送到台湾南部的员林,组成了“员林实验中学”。喜欢读书深思的张玉法,后来成为民国史的专家,一九九二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为这五千个孩子到处奔波、抗议、陈情的,是一路苦难相携的山东师长们。他们极力地申辩,当初这五千个孩子的父母把孩子托付给他们,他们所承诺的是给孩子们教育的机会,不是送孩子们去当兵。作为教育者,他们不能对不起家乡的父老。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台湾,《新生报》。
七月十三日操场上的血,滴进了黄沙。五个月以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星期一,上班上课的日子,所有的人一打开报纸,就看见醒目的大标题:
台湾岂容奸党潜匿,七匪谍昨伏法!
你们逃不掉的,昨续枪决匪谍七名。
以烟台中学校长张敏之为头,为山东流亡少年们奔走疾呼的七位师长,全部被当作匪谍枪决。
去年此时,徐州的战场上,五十五万国军在“错误”的指挥下被包围、被歼灭、被牺牲。所谓“错误”的指挥,后来才知道,关键的原因之一就是,共产党的间谍系统深深渗透国军最高、最机密的作战决策,蒋介石痛定思痛之后,决定最后一个堡垒台湾的治理,防谍是第一优先。
很多残酷,来自不安。
为了能够平平顺顺长大、安安静静读书而万里辗转的五千个师生,哪里知道,他们闯进了一个如何不安、如何残酷的历史铁闸门里呢?
18,永州之野产异蛇
一九四八年五月,河南也是一片烟硝。中原野战军刘邓兵团在五月二十日发动宛东战役,国军空军出动战斗机,在南阳城外从空中俯冲扫射,滚滚黑烟遮住了天空。
第二天,南阳的中学生们回到学校时,发现学校已经变成一片地狱景象:从校门到走廊、教室、礼堂,挤满了“头破血流的伤员,脑浆外露、断腿缺胳臂、肚破肠流、颜面残缺、遍体鳞伤、无不哀嚎痛哭”。南阳城外,国共双方伤亡一万多人,曝尸田野之上。五月天热,尸体很快腐烂,烂在田里,夏季的麦子无法收割。
这时诗人痖弦才十七岁,是南阳的中学生。
十一月,南阳的十六所中学五千多个师生,整装待发,他们将步行千里,撤到还没有开战的湖南。
开拔的那一天,十一月四日,场面壮观:五千个青少年,像大规模的远足一样,每人背着一个小包,准备出发。成千的父母兄弟,从各个角落赶过来找自己的孩子,想在最后一刻,见上一面。还有很多人,明明早就把银元缝进了孩子的裤腰,明明已经在三天内和姑姑嫂嫂合力赶工,用针线纳好了一双布鞋塞进孩子的行囊里,这时仍旧赶过来,为的是再塞给他两个滚热的烧饼。
一九四八年冬天的中国,灌木丛的小枝细叶,已经被白霜裹肥,很多池塘沼泽开始结冰,冷一点的地方,大雪覆盖了整个平原和森林。可是霜地、冰川、雪原上,风卷云滚的大江大海上,是人类的大移动:
葫芦岛的码头,停泊着四十四艘运输舰,十四万国军官兵正在登舰,撤出东北。
八千多个山东的中学生,正在不同的火车站里等车、上车,在奔驰的火车里赶向南方,在很多大大小小的码头上焦急地等船。
当南阳这五千多个中学的孩子在雪地里跋涉、涉冰水过河的时候,徐州战场上,几十万国军在雪地里被包围,弹尽援绝,连战马的骨头都重新挖出来吃。
一九四八年冬天,进攻的部队在急行军、在追赶、在抄包、在冲锋;撤退的部队在急行军、在绕路、在对抗、在奔跑。大战场上,几十万人对几十万人;小战场上,几万人对几万人。战场的外围,城市到城市之间的路上,拥挤的车队和汹涌的难民,壅塞于道。
河南这五千多个学生,每走到一个有车站的点,就会失去一部分学生。
南下北上。一上车就是一辈子。
一个叫马淑玲的女生,穿过了整个湖北省,到了湖南的津市,却下定决心不走了,她要回家。脱离大队时,留下一直带在身上的《古文观止》,给赵连发做纪念。
跋涉到了衡阳,十六所中学联合起来,和衡阳的学校合并成立“豫衡联中”,继续读书继续走。
一九四九年三月八日,终于在湖南西南的零陵安顿下来。零陵,就是古时的永州。
柳宗元被流放永州是公元八零五年秋天;一九四九年秋天,自河南历尽艰辛流亡到这里的四、五千个孩子,一部分,就被安顿在柳子庙里头。柳子庙是北宋仁宗在一零五六年,为了纪念柳宗元而建的。
和山东的孩子们一样,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