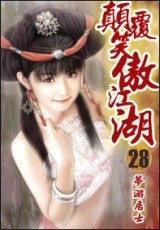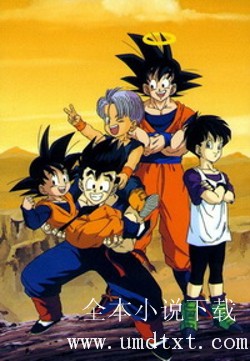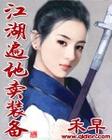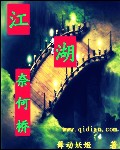江湖江湖 (1)-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爷爷躺在塔底下了,永远看不见了,师父走了,再也不会来传授武功了。这些天来,庄守严已去世,但他的遗体仍在,张寻和真怜仍感觉他在身边,仍然以他为中心过日子。可从今天起,他们要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了。张寻与真怜住在新盖的小木屋里朝夕相处,张寻本觉得不妥,可不住这儿又没地方去,让真怜一个人在这儿也不放心。好在藏民皆生性纯朴自然,并不会往孤男寡女、授受不亲这方面去想。
想到师父临终前的托付,张寻总想照顾好真怜,揽下全部的活,不让她累着。可真怜却抢着干家务,里里外外做得象模象样,真想不到这么纤弱的女孩会这么能干,每次张寻觉得过意不去,想帮着做点,真怜就会说:“你安心练武吧,这些活就应该是女孩干的。”
张寻每次听到这样的话,心里总会升起一般温暖,暗想即便有个亲妹妹,也未必会有真怜妹妹这般好的。渐渐地,张寻适应了这种生活,又见真怜干得挺愉快,也就放手让她去了,自己精心习武。
庄守严塔葬后,张寻每日都想开始练父亲传下的两样绝技,可他一直未从失去师父的悲伤中缓过劲来,心浮气躁,不适于新习深邃高深的武功。直至一月之后,他觉得自己心凝气定,才打开了父亲的《亢仓子服气诀》。张寻生长在尊父重教的孔子故里,耳濡目染,自幼喜爱读书。不仅遍读儒家经典,还喜欢翻阅道家的书籍。他知道亢仓子是春秋时道家始祖老子的弟子,深得老子真传,特别是行气的功夫很深,乃一代武林宗师。但因年代太过久远,事迹大多已经不传。却不知他还有武功秘诀留传下来,而且竟传到父亲手里。张寻仔细研读,见一开始是一首“服气总诀”,曰:“凡修炼之道,息心勿乱,精神勿行。若人行、住、生、卧、常、恃如是。其心自静,自然成就。不修此理,枉费齐河功,终无成法。但日日如此,俱但心成。若动静双忘,道不求自德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在行气养生中,首先要能心情平静,思想专一。不语、不念、不恼、不忧,保持血气畅通,做到一切厉害关系都不要放在心上。其次要能经常练习,始终保持心情快乐,这样就会水到渠成,练成功夫。第三要能在调息、调身的同时,注重调心。若不明白这一点,最终还是练不成功夫的。道理似乎很浅易,但要理解这浅易道理之中的深奥含意,却非达到较高的修为不可。张寻因为刚练通“黄龙仙传四十九式”气功,故对此已有所悟,心中一动,赶紧闭上眼睛细细琢磨。他一心想着寻找父亲,绝不可能将之抹去,那岂不和“服气诀”的要求背道而驰了?他苦苦思索,不知自己该怎么办,蓦然间,仿佛有一道闪电在他心中划过,照亮了他的灵性。他猛地睁开眼,明白了“服气诀”的这段话有一个前提,便是在“修炼”之时。若平日一律要求没有喜、怒、哀、乐,反倒不近情理,违背自然了。他只需要在进入气功状态时,做到心情平静,物我两忘,抛开一切利害关系,并经常练习,就会练成功夫。想通这一点张寻感到自己在武学修为上又精进了一层。再往下看时有十个练功图像,图旁分别有“潜龙在渊势”、“呼啸森林势”、“择星换斗势”、“倒拽九牛尾势”、“三盘落地势”、“青龙探爪势”、“卧虎扑食势”、“打躬势”、“掉尾势”……图下则是练功心法。这十势,每练成一势,身体的相应部位就会真气充盈,待十势全部练成,全身真气就会贯通。张寻已练成“黄龙仙传四十九式”,经络畅通,真气初生。现在又顿悟了服气总诀,练成这十个图形已是水到渠成,六六三十六天后,十势招法全部练完,他的功夫一下大增三成。此后随着练习时日增加,功力会越来越深。而张寻体内“黄龙仙传四十九式”与“亢仓子服气诀”两种气功练成的真气如水乳交融相辅相成,功力增长之速,更是远胜于常人。一法通,百法通。张寻此时对武学已有极深的造诣,接下去再练“七十二手梅花剑”,亦是迎刃而解。没有多久,就把一套绝世剑法练成了。
时光如过隙白驹,一眨眼间,又到了春天。而张寻在这剑岩之旁,已经住了整整一年。一日,张寻练完功,坐在岩石上望着由人踩出来的通往剑岩的小路,想起一年前,自己就是踩这条小路来的。现在武艺虽已初成,但受师父重托,得照顾真怜,也不知道自己何日才能踩这条小路出沟,去寻找父亲。不知不觉间,已是愁锁双眉。
真怜准备好晚饭,叫他去吃,喊了一声,张寻竟未听见。真怜这才注意到他表情有异,
便关切地问道:“张寻哥哥,怎么了?”
张寻摇摇头,没有答话,思绪仍然飞得很远。
真怜有些惊讶,疑惑地看着张寻,忽然间,她明白了张寻所思,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她平息了一下情绪,说道:“张寻哥哥,我知道你在想你父亲,想出去找他,对吗?”
张寻沉默片刻,真怜又怯怯地问道:“你是不是等不及了,现在就想走?”
张寻似乎有些茫然,仍机械地点点头,还是没有言语。真怜见了,差点要哭了出来,幽幽地说道:“你虽然想走,却又不放心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对不对?”
张寻呆了片刻,终于点头道:“是的。”
随即两人都不再言语,各怀心事。空气凝固起来,渐渐似乎要令人咬嘴唇才能让气氛舒缓一点似的。
最后。还是真怜打破了沉默,说道:“张寻哥哥,如果你要想找你父亲,就去好了。其实不用为我担心的,我都长大了,自己会照顾自己的。再说这里的藏民都那么好,他们也会照顾我的。”
张寻听了这话,略有所动。半年来,他唯一担忧的就是真怜。真怜是庄守严的亲孙女,按规矩,必须在墓旁守满三年孝,而他只是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弟子,并不受此规矩的约束,张寻只是想起了在曲阜读过的儒家信义:“事师者心衰三年,其哀如父母而无服,情之重而义有不得书者也。”他想,师父待我恩重如山,这“三衰”当以自己的生命为期限,又何止这区区三载?同时,他又每日都在想出去寻父,因为寻父这一宿命已深入他的骨髓,无时无刻不在折磨他了。但是,他又怎能任意远走,而抛开师父临终时要自己照顾好真怜的重托?当年,师父为了对父亲的一诺之言,找了他十年,等了他十年,化了整整二十年的光阴,自己既已经作出承诺,自然不能食言。而且真怜这般柔弱可爱,即便没有师父的遗命,他也不会扔下她一个人不管的。现在真怜自己提出让他走,道理也说得通,那到底该怎么办呢?踌躇之下,一时难以定夺。真怜见他为难,安慰道:“泽仁布秋大伯不是几次说剑岩离树正寨太远,不方便,让我们搬去他那住吗?你因为他房子也不宽敞,不利于练功,几次都谢绝了。你如果走的话,我就可以住到他那去,求个照顾,周围又有许多藏族女孩可以一起玩,不是挺好吗?”
张寻觉得这话挺有道理,知道在泽仁布秋家里,真怜一定会过得很好的。此念一生,出去寻父的愿望就像蔓延开来的山林烈火,立刻烧遍了他的全身。他发觉自己再也无法等待了,决定明天就出谷,先去找七星派掌门卓正明,问他是否找到了去宝石谷的地图,以便可以去寻找父亲。他对真怜深感内疚,不禁说道:“真怜妹妹,两年半年后,待你守孝期满,不管有没有找到父亲,我都来接你。”其实张寻自己也不知道,该把真怜接往何方。
真怜想到即将分离,极为伤感,但脸上好似没事一般,佯装笑容,说道:“好,我们一言为定,你可不要赖啊!你赖的话就是大熊猫,天天喝水醉倒。”说着,她轻轻一笑,泪水却已滚落下来。
第二日上午,真怜送张寻出沟。由于张寻的汉族衣衫在半年前皆被烧毁,幸存的穿在身上的一套也早已破烂不堪。昨晚真怜熬了一夜,替他缝了两套衣衫,今日一套穿在张寻身上,虽不甚妥贴,但一针一线,尽显情意。
张寻一路行来,想起一年前,也是同样的季节,同样的山道,当时他从这条山道进来是为了寻父,今日他从这条山道出去也是为了寻父。可心境却大不一样了。来时无牵无挂,去时却要体会离别的滋味。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张寻突然想起了江淹《别赋》中的这个千古名句。真怜也和一年前初见时大不一样了,当时她一身洁白,学着小鸟飞翔的姿势,在树林里和各种动物交流联欢。而现在他穿藏衣,颜色偏于灰暗,人也似乎有着重重心事,一路上沉默不语。
中午,他们来到了树正寨,在泽仁布秋家里吃了饭。泽仁布秋和他老伴听说真怜要住过来,开心得不得了。可知道张寻要走后,又深深惋惜,连连为他祈祷祝福,希望他早日找到父亲,完成心愿。
吃过中饭,泽仁布秋和老伴也要送张寻,被他谢绝了。行不多久,张寻和真怜在快接近沟口处见到一条往右延伸的小道,真怜突然对张寻说:“张寻哥哥,沿这条小路走大约两里地,有一个喇嘛寺庙,我想去许个愿,好吗?听说那许的愿都是很灵验的。”
张寻也想和真怜再多呆一会儿,就陪她向左拐上了小路,行了两里路,果然见一寺庙倚山临崖而建。寺前立着十数面五色经幡,在风中猎猎作响,让人油然地感到一股苍凉雄壮之气。
这座寺庙不大,为土木结构,大门上有块匾额,写有藏文,显是寺名了。张寻和真怜跨入大殿,发现此刻寺内极为宁静,只有一个喇嘛,盘腿坐在垫子上,默默地摇着转经筒。大殿内有些阴暗,檐沿饰有三个金顶,四个金钟,正前方塑着象征生死轮回的金轮,金轮两侧为一对神羊,旁边还有一面暗红的大鼓,佛像前有一盏酥油灯,火苗忽明忽暗地跳跃着,更增添了大殿内的神秘气氛。
真怜走上前去,恭恭敬敬她说道:“且诺杰。”意思是“你好”,她在九寨沟住了十余年,已学会讲一些藏语,便将自己想许愿的要求告诉了喇嘛。这个喇嘛沉默寡言,但面容和善,知道真怜的来意后,替她做许愿的准备,然后让真怜跪在佛像前面许愿。真怜认真地磕了三个头,双手合什,口中念念有词,脸上极为虞诚,张寻见状,也跪了下去,默默地陪着真怜。
就在真怜许愿的时候,张寻发现有一个木架上挂有几根白绸,还有一些布带,不知作何用场,便多看了几眼。真怜顺着他的目光望去,脸露欢喜之色。她与喇嘛对讲了几句,喇嘛站起身,走到木架边取下一根布带回来,替张寻系在头上。张寻虽觉奇怪,但大殿内气氛肃穆,却未便多问。
出了喇嘛寺,张寻不禁奇道:“这红布带是干什么的?”
真怜有些兴奋,滔滔不绝地说道:“这叫‘朗格’,大活佛对他念经,施过咒语,谁戴上它,谁就会受到佛的保佑。‘朗格’一般给那些最虞诚的教徒。可那个喇嘛说除了爷爷和我之外,你是他见过的第三个汉人,而且刚才你已向佛跪拜过了。所以就答应给你一根,并亲自给你戴上。”
张寻问道:“他就是大活佛吗?”
“不是。大活佛到印度取经去了。别的喇嘛也出去云游去了,现在寺里只剩下他一个。”
“那么和‘朗格’挂在一起的那几根白绸又有什么用呢?”
“那叫‘哈达’,是献给尊贵客人表示敬意的,我们可受不起。”
说话间,不知不觉两人离开了九寨沟。此时已近黄昏,仙鸟开始归巢,夕阳把树木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张寻与真怜在这样的背景之中,久久不愿道别。
终于真怜开口说道:“张寻哥哥,我一定等你……等我守满孝后,你到哪里,我就随你到哪里……”
她的意思是说,爷爷已将我托付给你,我的心早已就是你的了。到时候即便你到天涯海角,我也会陪伴着你的。而张寻并未理解真怜话中的深情,只是说道:“真怜妹妹你放心。两年半后,不管怎样,我都会回来接你。”
第四章 得剑
张寻一路往南,经都江堰而至巴蜀首府成都,其间途经“天下第一幽”的青城山,也未去游玩。一上路,他寻找父亲的意愿便压倒了一切。
成都乃蜀中名城,物产丰饶,百姓富庶,小吃尤为有名。张寻却无心驻足品尝,任“夫妻肺片”、“担担面”、“郭汤圆”、“赖珍珠”和“龙抄手”这些诱人的招牌在拥挤的街道边悬挂着,只宿了一夜,便匆匆往重庆赶去。他想由重庆坐船沿长江而下,至岳阳找七星派掌门卓正明,询问前往“宝石谷”的路径。
不一日,张寻来到川南小城大足,看看天色不早,便找了一家客栈准备在此歇息一晚,那家客栈只剩一间两人房还有空铺。他在伙计的带引下进了房间,屋内有一书生正轻摇折扇,看着摊开在桌上的一本书。他不停地晃着脑袋,口中还念念有辞,见张寻进来,即刻站起身,对张寻拱一拱手,道:“同经大足孤苦客,相逢何必曾相识。小弟姓董名昌,乃大邑人氏,出门在外为的是求取功名。不知老兄缘何到此?”
没待张寻回答,他又抢着道:“看老兄的模样,不像是生意人,难道竟和小弟一样,是进京赶考去的?”
张寻知大邑乃成都附近的一个小县,读书风气不盛,并未出过有大学问的人。他见这个书生一脸真挚,说话又是这般坦白,便也忙双手一拱,礼貌地答道:“在下姓张名寻,自小在山东曲阜长大,出门在外,是为了寻找父亲。”
董昌听张寻是出来寻父的,不仅夸张地大为感慨,赞他孝心可嘉,诚心可励。还从老菜子斑衣戏彩一直谈到营田孝子郭巨,甚至还讲到了花木兰替父从军,说张寻可与花木兰相提并论,都可以与二十四孝媲美。
张寻开始听得颇为有趣,可董昌越谈越有劲,也越谈越莫名莫妙。
张寻渐渐不耐,又见他滔滔不绝,似乎永无休止的样子,便找个借口说要去吃晚饭,退出了房间。
谁知张寻刚在饭厅里坐定,董昌又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