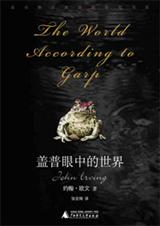计算中的上帝 作者:[加] 罗伯特·j·索耶-第1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个很大的范围。
我一直是个好学生,一个好学的人——苏珊也是。但那天的事发生得太快、太乱、太纷杂,我们无法体味、无法相信。科尔却独立于我们的感情之外——类似解说她已经作过上千次了,她已经变得职业化了,变得冷漠了。
但对于我们,对于所有那些曾坐在苏珊和我正坐着的塑料背椅子上的人,对于那些挣扎着去接受,去理解的人来说,整个过程是令人恐惧的。我的心在狂跳,头疼得似乎要裂开。科尔不断递给我的温水也不能缓解我的口干舌燥。我的双手——曾经小心冀翼地将恐龙胚胎的骨头从破碎的蛋中剔出的双手,把羽毛化石和石灰石外壳分离出来的双手,我赖以谋生的双手——像阵风中的树叶般颤抖不已。
“肺癌,”这位癌症专家以平静的语调说着,仿佛在谈论最新款的SUV车或是录像机的某些功能,“是最致命的一种癌症,因为它通常不能在早期发现,当它被发现时,它一般已经扩散到了颈部和腹部的淋巴结,肺与胸部之间的胸腔隔膜、肝脏、肾上腺以及骨髓。”
我希望她能说得抽象点,理论化一点。只做些笼统的评论。
但不,不是。她不断地说。她说得很清楚。而且这些都跟我有关,有关我的将来。
是的,肺癌经常大范围扩散。
我的就是这样。我问了个问题,一个死也要间的问题,却又是一个害怕听到答案的问题,一个极其重要的,一个从那一刻起决定我的世界中所有一切的问题。还有多少时间?还有多少时间?
科尔,终究是个人而不是一台机器,她此刻也不敢面对我的眼睛。确诊后的平均存活时间,她说,在无任何治疗的情况下是九个月。化疗可能会延长我的生命,但我得的那种是肺腺癌——一个新词,跟我姓名的音节一样多,却比我的名字托马斯·戴维·杰瑞克更能决定我的命运。即使在经过治疗之后,八个肺腺癌患者中只有一个能够在确诊后活过五年,大多数人很快就走了——这就是她用的词,走了,就好像我们溜出去在街角的小店买个面包。
它像一颗炸弹,粉碎了我和苏珊的一切。
在那个秋日发条已上好。
倒计时已经开始。
我还有大约一年时间。
第十一章
每天傍晚,博物馆对公众关门之后,霍勒斯和我就会下到下层大厅。作为我允许他研究化石的回报,他继续演示长蛇星座第二—Ⅲ上不同时期的生态圈,我把它们都拍了下来。
可能是由于我自己的生命很快要到尽头,我渴望尽量多见到些不同的东西。袱勒斯曾经说起过六个被其居民抛弃的星球,我想看看它们,见识一下这些星球上最现代的人造物品——它们的居民消失前的最后一件作品。
他给我看的东西令人惊异。
第一个是Epsilon Indi Prime。在它的南方大陆上有一个巨大的围在高墙中的广场。墙是由巨大的花岗岩垒成的。每块岩石加工粗糙,边长大约为8米。被围起来的场地直径大约有500米,里头铺着碎石:巨大的锯齿状的混凝土碎块。要是有人爬过高墙,他肯定会被眼前大片的荒凉震惊。没有什么动物或是机械装置能够轻易地横穿它,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在那里生根发芽。
接下来是Tau Ceti Ⅱ。在一片荒地的中央,消失已久的当地居民安置了一个巨大的黑石圆盘。盘的直径达2,000米。从它的边缘来判断,大概有5米厚。黑色的表面吸收着当地太阳的热,使得它灼热异常。如果你在上面走动,鞋底会融化,脚底板也会起泡。
Mu Cassiopeae A Prime的表面看不到它以前居住者的痕迹。所有东西都被二千四百万年的风化埋葬了。但霍勒斯给我看了一个马莱卡斯上的传感器扫描生成的计算机模型,它显示了沉积物下的世界:一个巨大的平原,平原上满眼是高耸、扭曲的尖顶。在那下面是一个拱顶建筑,永世掩埋,远离人们的视线。那个星球曾经有一个非常大的月亮,它相对于它围绕的行星的比例要比月亮与地球的比例小得多。但现在月亮已经变成了一圈壮观的陨石带。霍勒斯说他们已经确定了陨石带的年龄,大约为二千四百万年。换句话说,它是在当地居民消失时出现的。
我让他展示了这个行星的其他部分,看到了海中的群岛——岛屿像项链上的珍珠般串在一起。我还发现,它最大的大陆的东海岸线和第二大大陆的西海岸线几乎可以完全拼合。有证据表明此星球的大陆板块曾经漂移过。
“他们把他们的月亮炸了。”我说,为自己的观察力感到得意,“想彻底断绝搅动行星内核的潮汐力,他们想结束大陆板块的漂移。”
“为什么?”霍勒斯说,听上去对我的假说很感兴趣。“为了防止他们的拱顶建筑沉入地壳深处。”我说。大陆漂移使得地壳的岩石循环再生,老的岩石被压入地幔,海底裂缝则不断冒出岩浆形成新的岩石。
“但我们曾经认为拱顶建筑是用于埋藏核废料的。”霍勒斯说,“沉入地壳深处应该是消除核废料的最佳途径。”
我点了点头。他向我展示的在各个星球上的纪念碑似的建筑的确和我想像中地球上的核废料处理设施差不多:人造的建筑蕴含着不祥的预感,没有人会想在那儿挖掘。
“你们发现了什么和核废料有关的碑铭之类的东西吗?”我说。地球上的埋藏点都有标示性的说明文字及图案,表明这儿有危险材料,将来的居民便能知道地下埋着什么。图案包括了从病态的或是表情厌恶的脸——表明这个地区是有毒性的——一直到原子的模型图,告诉后来人埋藏了什么。
“没有。”霍勒斯说,“没有那一类东西,连年代最近的设施中都没有。”
“好吧,我想他们以为这些地点几百万年内都不会被打扰——时间这么久,当将来的智慧生物发现它们时,这些智慧生物和埋藏废料的智慧生物很有可能不属于同一物种。向同种物种传递危险信号是一回事——我们人类用闭眼、聋拉嘴角及伸出舌头表示有毒物质——但跨越不同物种之间的交流可能完全是另一回事,尤其是当你对后续物种没有任何概念时。”
“你的想法不全面。”霍勒斯说,“大多数放射性废料的半衰期小于十万年。等出现新的物种时,那儿可能早已没什么危险了。”
我皱了皱眉。“尽管如此,它们看上去还是很像核废料收藏地。还有,那些行星上的原居民离开时,他们可能认为应当在走之前处理好自己的垃圾。”
霍勒斯听上去不太相信。“但为什么Cassiopeae上的居民要防止建筑物沉入地壳呢?我刚才说过,那是消灭核废料的最好办法——甚至比把核废料送入太空还要好。如果负责运送废料的飞船爆炸了,核污染可能会扩散到半个星球,但如果核废料被送入地幔,那就一劳永逸了。我们最终也采纳了这种对付核废料的办法。”
“嗯,看来,可能他们在那些阴森森暗含警告性的地表下掩埋的是其他东西。”我说。“十分危险的东西。他们要确信它永远都不会被发现,因此它就不可能出来危害他们。可能Cassiopeae上的居民担心一旦拱顶建筑沉入地壳,关住它的建筑物的墙就会被融化,他们想囚禁的东西——确切说可能是想要囚禁的怪兽——就会逃出来。而这些居民,甚至在埋藏了他们感到恐惧的东西之后,还是离开了家园,希望离他们埋藏的东西越远越好。”
“我想这个星期天去教堂。”苏珊说。那是去年十月,我们见过科尔医生后不久。
我们在起居室里,我坐在沙发上,她在椅子里。我点了点头。“你不是经常去吗?”
“我知道,但——发生了这么多事之后……”
“我没事的。”我说。
“你确定吗?”
我又点了点头。“你每个星期天都去教堂。用不着改变。科尔医生说我们应该尽量保持正常的生活。”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度过时间。不过可以找出许多事。我得给在温哥华的弟弟比尔打电话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但温哥华比多伦多晚了三个小时,而且比尔工作到很晚才回家。如果我在他那儿的傍晚时分打电话给他,我很有可能会碰到他唠叨的新老婆。我可不想那样。比尔和他上次婚姻生的孩子是我惟一的亲属、我们的父母几年前就过世了。
苏珊陷入沉思。她抿着嘴,棕色的双眼和我的短暂相遇,随后又看着地面。“你——你可以和我一起去,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大声地呼了口气。这个问题一直是我们之间不太愉快的地方。苏珊一辈子都定期去教堂。和我结婚时她就知道我是不会那么做的。星期天的上午我上网浏览、看“唐纳尔森和库奇罗伯茨的这个星期”。刚开始约会时我就明确表明我不喜欢去教堂。太伪善了,我说,对于那些真正的信徒来说是个侮辱。
但是,她现在清楚地感觉到我们的世界已经变了。可能她以为我想祈祷,以为我想在我们的创造者面前找到安宁。
“可能吧。”我说,但我知道,我们俩都清楚这不会发生的。
要么不下雨,要么大雨倾盆;事情要么不来,要么总是集中在一块儿出现。
对付癌症花费了我大量时间。现在霍勒斯的拜访又占据了剩下时间的大部分。我还有其他职责。我为博物馆组织了布尔吉斯页岩化石特别展。虽然几个月前它就开幕了,但我还是承担了很多与之相关的管理工作。
史密森学会的查尔斯·瓦科特在1909年于不列颠哥伦比亚旁的洛基山布尔吉斯小道中发现了布尔吉斯页岩化石。他在那儿一直挖掘到1917年。后来,从1975年开始并一直延续了二十年.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德斯蒙德·柯林斯开展了一系列成果巨大的新挖掘,发现了另外的化石埋藏地和新的物种。198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布尔吉斯列为第八十六个世界文化遗产,与埃及金字塔和美国大峡谷同属一类。
布尔吉斯页岩化石的年代可追溯到大约5亿2千万年前的寒武纪中期。页岩实际上是劳伦系岩石层上滑落的泥石流,它将海床上的一切生物都埋在底下。页岩质地极细,连生物体上柔软的部分也保存得完好无缺。无数形式各异的生物被页岩记录下来。一些古生物学家,包括我们的老琼斯在内,认为它们中的一些和现代生物毫无关系。它们就这样突然产生,生存一阵子,最后又消失了,好像自然界在尝试各种不同的形态,看看哪种最适合发展。
为什么这个“寒武纪大爆炸”会发生呢?当时地球上的生命已经存在了三十五亿年,但是,在这整个期间,生命形式都非常简单。是什么导致了突然出现这么多形态各异的复杂生命?
加拿大理工学院的戴维逊和卡麦隆以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彼德逊有一种看法,寒武纪大爆炸之前的生命形式为什么简单,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在寒武纪之前,受精卵的复制次数是非常有限的。十次之后似乎就已经到达上限。而十次复制只能产生1,024个细胞,因而也就只能支持非常简单的生命。
但是到了寒武纪早期,一种新细胞的发展打破了十次复制的障碍。这种新细胞在现代的某些生物体上依然存在。这些细胞可以复制很多次,并且可以决定各种新生物的形态分布,也就是说,可以决定躯体的形态。(这种情况发生时,地球的年龄已经有四十亿年了,但是同样的突破——超越复制十次的极限——显然在弗林纳人的行星只有二十亿岁时就发生了。在这个突破点之后,那里也突然爆发出生命形式的多样性。)
地球上的布尔吉斯页岩中有我们的直系祖先皮凯亚虫的化石。皮凯亚虫是第一种有脊索的动物,脊椎就是在脊索的基础上进化而来。但是,那里的几乎所有化石仍然属于无脊椎动物,因此,布尔吉斯页岩特别展似乎应该由博物馆的高级无脊椎古生物研究员凯利布·琼斯来组织。
但是琼斯再过几个月就要退休了——至少还没人当着我的面说,博物馆马上就要损失两个高级古生物研究员,几乎在同一时间——而且,我与史密森学会的人有些私交。在加拿大通过保护文物的法律之前,瓦科特挖掘的布尔吉斯页岩就存放在那儿。我还协助组织了与特别展同时进行的大众科普讲座。大部分讲座由我们的员工(也包括琼斯)负责,但是我们也从哈佛邀请了《奇妙的生命》一书的作者斯蒂文·杰·古德前来做一次讲座,古德的这本书详细地向人介绍了布尔吉斯页岩。此次展览为博物馆赚取了大把钞票。像这样的展览总是会成为媒体的热门话题,因而吸引了大量的观众。
在刚开始筹备特别展时我就挺兴奋的,等到它被批准,而且史密森同意共同参展之后我就更兴奋了。
但是现在——
得了癌症以后——
它成了我的累赘。
我还有一件事未了。我所剩无几的时间还得花在这上面。
最难的就是告诉里奇。
你要知道,如果我像我父亲一样,满足于学士学位和朝九晚五的生活,事情就不会变成这样。有可能在二十岁刚出头我就当上了爸爸。如果真是这样,到了我现在这个年纪时,我第一个孩子已经二十多岁了,也可能已经有了他自己的孩子。
但我不是我父亲。
我在1968年拿到了学士学位,当时我22岁。
1970年,硕士学位,24岁。
然后是博上学位,28岁。
然后在伯克利做博士后。
然后换到另一个大学,卡尔加里大学,34岁。
然后开始研究工作,不知为什么还没有遇到合适的人。
然后没日没夜在博物馆工作。
然后,在我觉察到以前,我己经40岁了,仍是单身,没有孩子。
我是1966年在多伦多大学的哈特堂首次见到了苏珊·科瓦斯基。我们都是戏剧俱乐部的成员。我不是演员,但我对剧院照明特别感兴趣,我猜我爱上博物馆学,这也是原因之一。苏珊演过一些角色,但现在想来,她缺乏演戏的天分。我一直对她挺着迷的,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