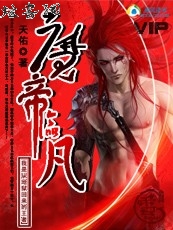网人 作者:黄孝阳-第2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那时并不明白妈妈指的“这样”到底是什么,也许大人之所以是大人,之所以可以对一个孩子呼喝打骂,是因为他们能够通过“这样”或“那样”诸如此类的词汇来交流、沟通,在心照不宣的时候获得支配的权力。他开始觉得委屈,认为他们藏起了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但随着时间随着屋外老去的树皮一段一段剥落后,他渐渐习惯了这种委屈,且不再觉得委屈。谁不会有秘密呢?自己已经不会当着任何人的面咬手指头,但自己是越来越喜欢咬手指头了,并常常把手指头咬得鲜血淋漓,它们确实很好吃,总能咂出各种各样的味道。
她听了他的话咭咭地笑,嘟起嘴,让嘴巴像花瓣一样翘起,然后把食指缓缓伸进去,抽出来,再伸进去,再慢慢抽出来,嘴里咂咂有声,是不是这样?她露出一脸不怀好意的媚笑。她的手势让他坐不住了。妈的,他在心中嘀咕道。裤裆处渐渐顶起一处帐篷。他缩回脚,佝偻着身子,用手指头轻弹着酒瓶口。
爸爸死的那天也是这样轻弹着碗沿。爸爸那天没有揍他,摸着他的脑袋说,几岁了?他说,十四岁。爸爸哦了一声就不再言语,目光定定地看着远方的云。云在天边一朵一束,有的像花朵,有的像岩石,不过,很快便被阳光一一搓薄,还淌出一大滩鲜血的汁液,把大半个天幕染得通红。他觉得这红有点儿狰狞,就闭上眼睛。等到他再睁开眼时,爸爸已经不见了。他的泪水一下子涌出来,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多。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哭,只是放声大哭,手中揣着爸爸放在他手里的大海碗。他的家在铁路边上。铁路很长。他小时候喜欢做的游戏有不少,多半与铁路有关。他喜欢踩着黑色的枕木往前走,走啊走啊,走得前面传来汽笛声,脚下的大地都陷入一阵阵不可抑止的颤粟中时,这才不慌不忙地跳在旁边,任那白色的水蒸气将自己紧紧包裹。他还喜欢从裤兜里掏出一个铜钱放在铁轨上,等列车驶过,如果运气足够好,铜钱的边缘会变得无比锋利。他的手里经常攥着这么一枚铜钱,铜钱有时会把掌心割出血,但他一声也不哼。这枚铜钱带给他的荣誉远远要大于所带给他的疼痛,何况忍受疼痛往往会在孩子圈里带来更大的荣誉。他没事时就拿这枚铜钱朝各种各样的木板上扔,啵地一声,很像是一个甜蜜的吻,铜钱便牢牢嵌入木板肌纹里。可惜后来,铜钱忽然不见了。
他不无懊恼地想着。对了,就是那天,那天火车轰隆隆从爸爸的身体上辗过,发出尖锐的嚎叫,爸爸没有像铜钱一样变锋利,反而一下子就支离破碎。他松开手,碗摔在地上,铜钱也从裤兜里滚出,慢慢滚到爸爸那堆血肉里,夹在几根白骨里,不再动了。后来,妈妈就来了,跑得真快,比风还要快,远远的,从腥红色的地平红上跃出,一开始只是一个小白点,白点越来越大,像生出了翅膀,妈妈眨眼间就已到了。他以为妈妈又会掐他的胳膊,悄悄缩了下脖子,可妈妈却看都没看他一眼。她惊疑不定地收住脚,目光掠过四周闹哄哄的人群。人群顿时肃静下来,有人抬头,有人低头。妈妈的脸上有几滩淤痕。他愣愣地看着妈妈向爸爸走去。妈妈的眼角眉梢急速扭曲着,嘴边泌出血迹,脸成了一张纸,纸上的文字与图案一下子惨白一下子鲜红一下子青紫。妈妈就像书上说的会变脸的妖魔鬼怪。过了一会儿,妈妈嗷一声叫,一头往铁轨上撞去。妈妈肯定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脑袋立刻就破了,露出一个大洞咕嘟咕嘟往外冒着血。他记得爸爸喝酒时也是这样咕嘟咕嘟的,便想走过去看个究竟。可人群迅速骚动了,并将他结结实实地拦在外面,没有给他留下一丝希望。
他说到这里时又把手指头伸入了嘴里。他说,他有时只是想咀嚼点东西,但并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放入嘴里。手指头显然是属于自己的,而且显然不会把牙齿崩坏。他都有些语无伦次了。他抬起头看着她。她的目光有些茫然。他说,或许有些事情不是你想象的一样吧?不过,我还是不明白,也许归根到底,它还是你说的那样。比如母爱什么的,因为它也许不是插入,仅仅只是吮吸。她点点头,脚在沙发上踢了踢。沙发上留下一个月牙状的鞋印。这屋内月牙状的东西还有几个,墙壁上的两盏灯,茶几上那片被人啃过一口的西瓜以及两个人忽明忽暗的脸庞。她忽然生气了,说,你烦不烦?他说,烦就不说了。她沉默了一会,说,不吭声,更烦人。他说,那想怎么样?她说,见你就烦。他说,那我走了。她说,不准走。她的眼泪掉了下来。
她说,她也一直想不明白。等到她想问个究竟时,她的小姨已经不见了。她赶紧把嘴里半生不熟的豆子吐在手心,从裤兜里掏出一方手帕小心包好。这些豆子嚼起来很费劲,腮帮子常会因此变得又酸又涨,但她非常爱吃。她跑到井台边,扒着井沿,往里看,水面上有一个被涟漪揉碎的影子。她喊了几声小姨。小姨没有回答她。声音很快便被青砖砌成的井壁吸得没有一点剩余。她忽然看见井沿边的青砖上有一丛褐黄色的小花。她揉揉眼睛,那确实是一束花,花瓣椭圆,近叶柄处微尖,形状与一个孩子扮鬼脸时吐出的舌尖差不多。花瓣很精致地排列着,像一只绿色的手上轻轻拿着的一面面明黄色的芭蕉扇,样子很好看,她一下子好奇起来,勾下腰,摘下花,凑到鼻尖,嗅了嗅,花一点也不香。她嗅到被井水浸透的空气正若有若无地泛出一股酸涩说不大清楚的气息。她颦起眉尖,花瓣从指尖漏下,翻了几个跟斗,落在水面上,不再动弹。她想起小姨,又小声喊了几下,然后便瞅着水面直发愣。不知为什么,撒在水面上的花瓣一下子便泌出微香,也许因为井底光线比较幽暗,又或是有了水的滋润。她眨眨眼,井底水面上的那个影子却似乎对她招起了手。她吓了一跳,手指下意识抠紧井沿处几个窟窿,心慌得厉害,怦怦直响。她以为自己要掉井里了,眼前蓦然跃出一团嗡嗡作响的金色的星星。
他想了想,说,人在高处总有往下跳的欲望,特别是当人趴在井沿边。因为井就像是女人的阴道,我们从那里来,当然也想回到那里去。子宫是最温暖的地方。这是生命的烙印。所以,你当时有那种感觉,一点也不奇怪……她冷不丁笑起来,随手点燃一根烟,看着他,眸子里的光线先是明暗不定,然后渐渐迸裂,忽然,凝结住,无形却有质。这让他有些心虚。他绞动一下双手,骨节处暴出一阵脆响。他不是心理医生,对自己说的话并无多少底气。他咳嗽一声,没再说下去,手指伸出,在茶褐色的玻璃上轻轻叩击,似乎若有所思,样子显得特深思熟虑,不过却心知肚明,自己的心神已全为她转述她小姨死前对她说的那句话吸引住了。她说,她的小姨跳井前,从她身边走过,她闻到小姨身上的香气,没看见小姨脚下的影子,而事实上那天的阳光真的很大,大得整个院子没有一丁点声响。小姨好像摸了一下她的头,又好像没有。小姨说,她以后嫁的男人会比她的头发还多。她说着话,把烟灰弹在玻璃上一叠翻开的沾满酒渍的塔罗牌上,嘟起嘴,轻轻吹口气。这些烟灰便无影无踪了,像长了飞毛腿。她叹口气,小姨为什么要这么说她呢?她说完眼泪便不见了,咯吱咯吱地笑。她问他,她是不是很漂亮。他说是。
她的确是一个天生尤物,她的存在让男人想犯罪。譬如现在,他就很想亲亲她的嘴。只要不是瞎子,那一定可以看出她的唇上并没有涂抹任何口红,但她的唇不仅艳,软,而且香,轮廓分明,不要说男人,大罗神仙怕也会心猿意马。可惜他有贼心没贼胆。他没有吻她的权力,她没有被吻的义务,虽然他是男人,她是女人。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同时出现在某个空间里,按常识来说,两者应该发生一点故事。遗憾的是,到现在为止,这个故事仍只在他肚子里发酵,并不能倒进酒杯倾入嘴里,品咂其中美味。或许他们都会很乐意享受吻与被吻的滋味。但想尝美女的吻似乎也得先拿出等量的硬通货来换。这个道理很多书上都说过,有的书上还特别用了大号的黑体字,所以他还是记得比较清楚。说句良心话,像她这样的美女若只属于一个男人,确实有点暴殓天物。她的小姨还真有先见之明。不过,她那时应该才几岁大吧,一个大人对一个孩子说那样的话,两个人之间还多少有点血缘关系,这个诅咒未免太有点恶毒了?如果说只是恶毒,那为何不把还是孩子的她掐死扔井里去?那样不仅恶毒、还省事、还干净利落。这里面到底藏了些什么?他也笑,脑袋里已是稀里糊涂。他伸出舌头,耐心地舔着手指头上的手指甲,手指甲其实也有很多种味道,当人万事如意时,味道甜得很,当人屋漏偏逢阴雨时,味道就苦得很。当然,这些知识都是属于他一个人的秘密,纵然将它们公之于众,别人也多半没法从中尝出人生五味。大家各有各的活法。
那天晚上很快就过去了。她坚持要他搬到她哪里去住。那是一个藏在城市角落里一个很老的四合院。大宅门上黑色的漆几乎剥落光了,门前的石狮子,丢了一只,另外一只却被砸成两半。到处落满灰尘,门是旧的,砖是旧的,不过,她与他倒是衣着光鲜的。门响了一阵,退往两旁,他跟在她身后跨过月牙状的门槛。进门照壁处的那株玉兰树上挂着一面巨大的蜘蛛网,直径居然有一米见方。他从玉兰树下走后时听见她叹息了一声。她说,这蜘蛛网上原来有一只大蜘蛛,力气很大,甚至能抓住刚开始学飞的小鸟,后来不知怎么搞的,就不见了,或许是被大鸟啄去了吧。他心里想着,没吭声,继续往前走。前面有一口井,井台很阔,井口却小,不会比她的臀围大上多少。他走到近处随意往里面瞥了一眼,顿时头晕目眩。井极深,且呈倒葫芦状,里面最大处的直径约有两米。他倒吸了一口凉气,这若有人不小心掉下去,那可是糟糕之大极。这口井应该有很多年的历史。掀开在井口旁边的铁盖锈迹斑斑,井檐也沾染着锈水。一些半枯半黄的落叶不时从空中飘来,在井台上打着旋。他站在长满苔藓的小青砖上发起了呆。他想,最早建这口井的人恐怕并不是为了打水喝吧。
他回头看了她一眼。她扭过头去看天边。她说,这里不久要被夷为平地,要建好高好高的楼,原来在院子里住的人都搬走了,可她却不晓得自己能搬到哪里去。她说,有一天,她的妈妈忽然扔下她与爸爸还有小姨,与一个长得很丑很丑的男人走了,那个男人是小姨请来的医生。爸爸生气了,奸污了小姨,小姨夫杀了爸爸。警察来找小姨夫,怎么都找不着。一个面目和蔼的中年警官朝她蹲下身,说她也不知道小姨夫藏在哪里。她就指了一下阁楼。阁楼还没一尺高,很难想象一个大活人能够藏在里面。她说,小姨夫就在哪里趴着呢,我怎么会不知道?警察从阁楼里找出了暗道,小姨夫被枪毙后,小姨跳了井,死之前,她对她说了那句话。那天,小姨洗了头发,非常漂亮。她当时八岁,她被送进了孤儿院,十年后,她离开孤儿院,又回到了这所房子。她笑了。她对他说,你怕吗?她指指井口说,每当她走到这里时总能听见小姨说的那句话。她边笑边用手指头刮着鼻子。阳光让她的鼻子变得透明。她的样子真好看。
他也笑了。他说不怕,我都是死过一回的人,又怎么会怕这些事呢?他告诉她,他结过婚,离过婚。结婚是因为爱上了一个女人,离婚是因为这个女人只爱他的钱,并为此帮他买了巨额人身保险,然后雇人在他那辆桑塔纳的刹车片上动手脚。她太贪了,不应该买保险,而且事先竟然不对自己打半声招呼,否则他还真会以为是刹车片失灵。他从悬崖上翻了下去,不过命大福大没有死成,当保险公司来调查,并出具相关证据时,他这才弄明白,并为自己当初竟然会看上这么一个女子而羞愧。杀人,那也是一个技巧活,怎可以为贪欲蒙蔽住眼睛?活做得这么不地道,就是杀成功了,那也无趣得紧。譬如把人分筋错骨大动手术,双手拧成麻花别在脑后,双腿一条向前一条朝后,然后把人放出去,让他在山道上走,他自然会四仰八叉掉到山涧里去。这样的杀人法子显然有趣多了。他说,他虽然恨她,最后却没有报案,而是给了一大笔钱请她离开,并因此变成了一个穷光蛋,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以后若有哪个女人肯嫁给他,绝对不会是贪图他的钱财了。他又说,他还请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喝过几回酒,讲明一切责任皆在自己,刹车片上的切痕也是自己不小心割出来的,所以他不仅不要人身赔偿,而且也不要车险赔偿。他说,当时她感动得一塌糊涂,说大恩大德只待来世结草衔环来报,可他前些日子看见她时,她眼里的凶光可真让人毫毛倒竖。
她就笑,说,编故事吧?他说,爱信不信。她说,她也会编。她指了指身边的井说,如果她说这里面不仅有她的小姨,还有她妈、还有那个好丑好丑的男人,会有人相信吗?他说,不知道。她不作声,皱起鼻子,说,她跟过的男人,已经比小姨的头发还多。他点点头,打量着四周,阳光像雨点刷刷地落下,庭院里升腾起一阵热气。他瞥见假山石处有几片影子在晃来悠去。他眨眨眼,影子不见了,几根藤萝洇出一股阴森森的绿意。他打了个寒颤,扭过头对她笑道,把井填了,然后忘掉它。咱们一起来做这个游戏,好不好?她嘴角往上一挑,脸上浮出若有若无的笑意,咱们?他说,是啊,咱们。委屈大美女了。她就笑。
她与他填了这口井。她非常能干,甜甜地叫着大哥喝水,愣让运送沙石的司机主动把价钱打到五折。她仍不满意,继续浅笑倩兮地侃价,价钱最后就变成了三折。她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快活极了,每一次司机开着翻斗车轰隆隆把沙石倾入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