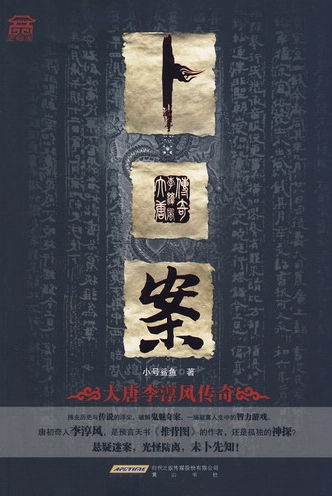弓区大谜案-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突然一阵激动含混的咕哝传过人群,一个模糊的无人知道是什么的低语。有什么事发生了。有什么人来了。很快人群周边的一角骚动起来,那儿传来一阵骤发的欢呼,沿街一直传递过来。人群分开了——一辆马车从中疾驶而过。
“格罗德曼! 格罗德曼!”那些认出了马车里乘客的人叫道,“格罗德曼! 万岁!”
格罗德曼表面上镇静而面色苍白,但他的眼睛里闪着光;他勉励地挥着手随着马车疾驰向门前,就像小舟切过水面一样切开扰动的人群。格罗德曼跳出来,门口的警官尊敬地给他让路。他紧急地敲门,门小心地被打开;一个男孩冲上去送了一份电报;格罗德曼闯了进去,报上了姓名,并坚持要为了一个事关生死的问题见内政大臣。
在门附近的人听到了他的话而开始欢呼,人群中显示出好的预兆,空气中跳动着连续的欢快的声音。当门重重地关上的时候,欢呼声在格罗德曼的耳边回响。记者们费力地挤到前面。一群激动的工人们围住了停住的马车;他们把马牵开。一群狂热者争夺着让他们拉车的荣誉。而人群等待着格罗德曼。
第十二章
格罗德曼被领进了勤奋的大臣的书房。这勇敢的骚乱的领导,可能是一个无法被拒绝的人。当他进去的时候,内政大臣的脸似乎宽心地亮了起来。在主人的示意下,带来最后的电报的文书助理又把它带回他工作的外面的房间里。不用说,没有多少给大臣的通信能到他眼皮底下。
“我想你有一个正当的理由来打扰我,格罗德曼先生?”内政大臣几乎是高兴地说,“当然是关于莫特莱克?”
“是的;我有最好的理由。”
“请坐。讲下去。”
“请恕我冒昧,但你有没有关注过证据的科学呢?”
“你是什么意思?”内政大臣疑惑地问,又加上一个沮丧的微笑,“最近我不得不去。当然,我从没有像我的一些前任一样,当过刑事律师。但我不会把它称为一门科学;我把它看作一个常识问题。”
“请原谅,先生。这是所有科学中最微妙而困难的。实际上,它是科学中的科学。由培根和缪勒建立的整个归纳逻辑学,不就是一个对证据的价值进行评价的尝试,那些被称为是由创世主留下的痕迹?创世主——我最崇敬地说——一路上留下了无数的障眼法,但真正的科学家在探察自然的秘密的时候,不会被表象所迷惑。粗俗的大众只抓住表面明显的事实,但是有洞察力的人知道表面的东西可能是虚假的。”
“很有趣,格罗德曼先生,但真的——”
“请听我说,先生。证据的科学是如此微妙而且要求最为敏锐和熟练的对事实的观察,还有最为广泛的对人类心理的理解,自然要交给专家,而这些专家一点也没有‘事物并不像他们看上去那样’或者所有东西都和表象不同这样的观念,对那些大多数把全年投身于商店柜台或是办公桌的专家来说,他们都得以详细地了解所有事物的无尽区别和复杂性还有人性。当12个这样的专家被放在陪审席上,就叫做一个陪审团。当一个这样的专家被独自放在证人席上,他被叫做证人。对证据的复述——对事实的观察——被交给了那些经历了一生却从未真正睁开眼的人;对证据的评价——判断这些事实——被交给了那些只会熟练地称糖的人。除了他们完全无法完成任何一个功能——去观察或者去判断——他们的观察和判断都受到了各种各样无关偏见的损害。
“你在攻击陪审制度。”
“不一定。我准备科学地接受它,因为,一般来说,那里只有两种选择,可能性略微倾向于他们作出正确的决定。而且,在像我这样的专家拥有证据的情况下,陪审团就可以通过训练有素的眼睛观察了。”
内政大臣不耐烦地跺着脚。
“我不能听信抽象的理论,”他说,“你有什么新的实在的证据吗?”
“先生,一切都依赖于我们去找到问题的根本。平均百分之多少的证据你认为是彻底的、完全的、简单的、未加修饰的事实,‘真相,全部的真相,除了真相别无其它’?”
“50%?”大臣有点开玩笑地说。
“不到5%。我不是在说记忆的错误,或者观察能力的天生缺陷——尽管在一些事隔几年后的重要审判中,普通证人对于日期和事件的可疑的精确回忆,是现代法律学上的珍奇事件中最令人震惊的。我试着向你挑战,先生,让你告诉我你在上个星期一晚餐吃了什么,或者你在上个星期二下午5点确切地说了或干了什么。任何不是过着机械的刻板生活的人都不能作出这种事;除非,当然,那些事实是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但通过这种方式。切实观察的最大障碍就是在任何所见的事物中先入观念的影响。你是否曾注意到,先生,由此,我们从不看见任何人超过一次?我们第一次遇到一个人我们可能看到他真实的样子;第二次我们的所见就被对第一次的记忆而修饰和渲染了。我们的朋友看起来和陌生人一样吗?我们的房间。我们的家具,我们的烟斗在我们眼里和在第一次见到它们的外人眼里是一样的吗?尽管对其他所有人都很明显,一个母亲能看到她孩子的丑陋,或者一个坠入爱河的人看到他另一半的缺点吗?我们能像别人看我们一样看自己吗?不行;习惯,先入观念改变了一切。头脑是一个对所有的被称为外来事实的加工厂。眼睛有时候看到它想看到的,更多的时候是看到它所预期看到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先生?”
内政大臣点了点头,他不再那么不耐烦,而是开始感兴趣了。外面的喧嚣微弱地传到他们耳朵里。
“给你一个明确的例子。温普先生说当我在12月4号撞开康斯坦特先生的房间门的时候,看到门闩的锁环在梢边从门楣上被扯开后,我立刻得出了我撞坏了门闩的结论。现在我承认当时就是这样,只是在这种事中你不像是去‘推断’,结论下得太快以致于你‘看见’或者似乎是看见了。另一方面,当你看见一个回旋的火把所造成的火圈时,你不相信它是持续存在的。这和看戏法表演是一样的。不管谚语怎么说,看见并不代表相信;但相信通常导致看见。不切题地说一句,关于这件门的小事温普和他在其他事情上一样毫无希望和无可救药地错了。门确实好好地上锁了。但我还是得承认如果它是被提前破坏的话,我也会看成是我撞门时破坏了门闩。自12月4号以来,我从没想到这个可能性,直到温普凭着误用的机智提出了它。如果对于一个训练有素的观察者,而且是已经注意到这人类思维根深蒂固的倾向的人都是这样,对于毫无经验的观察者又会是怎么样啊?”
“直截了当些,直截了当些。”内政大臣说,他伸出一只手似乎它想去按桌上的铃。
“比如,”格罗德曼不为所动的继续说,“比如说——达顿普太太。那个可敬的人无法通过不断猛烈地敲门叫醒她要求被叫起来的房客;她变得惊恐,她冲过来寻求我的帮助;我撞开了门——你认为那位好太太预期会看到什么?”
“我想,是康斯坦特先生被谋杀了。”内政大臣疑惑地咕哝道。
“正是如此。所以她看到了这个。你认为当门被我用强大的力道砸开时,亚瑟·康斯坦特的情况怎么样?”
“什么,他不是死了吗?”内政大臣吸了一口气,他的心激烈地跳动。
“死了?那样一个年轻健康的人!当门被撞开的时候,亚瑟·康斯坦特只是在睡觉。当然,那是一个很深,很深的觉,不然很早以来的撞击声就该吵醒他了。但是达顿普太太幻想着她的房客冰冷而僵直的时候,那可怜的年轻人正躺在床上睡一个舒适温暖的觉。”
“你的意思是你发现亚瑟·康斯坦特当时还活着?”
“就像你昨晚一样。”
大臣沉默了,困惑地努力去理解状况。在外面人群开始再一次欢呼。可能只是为了打发时间。
“那他是什么时候被谋杀的?”
“接下来立刻。”
“被谁?”
“请原谅我这么说,这不是一个聪明的问题。科学和常识在这点上是一致的。试着用穷尽法。那不是达顿普太太就是我。”
“你的意思是说达顿普太太——!”
“可怜的亲爱的达顿普太太,凭这你可不配当内政大臣!会认为是那个善良的太太!”
“是你!”
“冷静下来,我亲爱的内政大臣。没有什么可慌的,那只是一个单独的试验,我希望它能保持那样。”——外面的噪音越来越大:“为格罗德曼欢呼三声!加油, 加油, 加油,万岁,”——微弱地传入他们的耳中。
但是面色苍白深受震撼的大臣摁了铃。内政大臣的家庭秘书出现了。他吃惊地看着大人焦虑的脸。
“谢谢你叫来了你的文书助理,” 格罗德曼说,“我打算请你让他替我干些事。我想他会速记。”
大臣点了点头,一句话也说不出。
“很好。我希望这份声明能作为我的书,《我抓住的罪犯》第25版的附录的基本框架——就像某种银婚纪念。丹泽尔·堪特考特先生,根据我今天立下的遗嘱,将被任命为我的文学执行人,承担起把根据我的书中其它章节的样式将它润色修饰的工作。我有足够的信心他会公正地从文学的角度评价我,正如你,先生毫无疑问会从法律角度上一样。我相信他能够成功的赶上其它章节,达到完美。”
“邓普莱顿,”内政大臣小声说,“这个人可能疯了。要解决弓区大谜案的努力可能使他的脑子糊涂了。尽管如此,”他大声补充道,“你最好还是把他的声明速记下来。”
“谢谢你,先生,” 格罗德曼衷心地说,“准备好了,邓普莱顿先生?开始吧。我在离开苏格兰场侦探部门之前的职业生涯为人所熟知。我是不是讲得太快了,邓普莱顿先生?有一点?好,我会放慢一点;但如果我忘了减速的话请提醒我。当我退休了,我发现我是一个单身汉。但想结婚已经太晚了。我手上的时间太多了。为我的书《我抓住的罪犯》作准备让我几个月有事可做。当它被出版了,我便没事可干,只能思考。我有足够多的钱,而且进行了很安全的投资;没有什么事需要思考的。未来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后悔为什么没有在工作中死去。同所有无所事事的老人一样,我活在过去中。我一遍遍回顾我早前的功绩;我重读我的书。当我不断地反复思索,远离实际追踪的刺激感,而从一个更真实的角度看待事实,结果我越来越清楚的发现罪犯比流氓更为愚蠢。
“每一起我所追查的犯罪,不管是多么巧妙地犯下的,从更透彻的角度上来看都是一次软弱的失败。痕迹和线索被留在各种地方——破烂的边缘,粗糙的角落,整个工作都很笨拙,全无艺术的完整性。对于这些粗俗的事件,我的功绩可能看起来很了不起——普通人困惑地难以理解你如何能从一封简单的密码上发现出字母‘e’——对我来说那像它们所揭示的罪行一样普通。经过了一生的对证据科学的学习,现在对我来说,似乎可能能够犯下不止一起,而是一千起完全无法被侦破的罪行。而那些罪犯们却在继续犯错,并以同样的老方式,泄漏他们自己——没有创造性,没有闯劲,没有个人的理解,没有新的想法!一个人可以想象那儿有个有4万个坐席的犯罪学会。
“渐渐地,当我反复思考了这个想法以后,我有了一种犯一件能迷惑侦查的罪行的冲动。我可以设计几百个这样的罪行,并通过想象它们被完成来自娱自乐;但是它们实际上是否真的可行呢?显然我的试验的执行者只能是我自己;而试验对象——是谁或者什么呢?由机遇而决定。我渴望从谋杀开始——首先去对付最困难的问题,而且我急切地想让世界震惊和困惑——特别是那个我不再进入的领域。表面上我是镇静的,和人们像往常一样谈论自己。内在的我急于释放科学的激情。
“我炫耀我最喜欢的理论,脑子里把它们安到每个我见到的人身上。每一个坐着和我聊天的朋友或熟人,我都在谋划着如何不留痕迹的谋杀他们。没有一个我的朋友或熟人是我没有在脑子里杀过的。里面没有政府官员——别害怕,我亲爱的内政大臣——我不打算进行秘密、神秘、难以理解、难以发现的刺杀。啊,我该如何给那些平庸的罪犯建议啊——他们有二流的动机,陈腐的观念,普通的细节,他们缺乏艺术感和克制。”
人群再一次开始欢呼。尽管作为旁观者感到不耐烦,他们认为没有消息也是好消息。内政大臣所准许的和辩护协会的主席的会面时间越长,他的固执能被解消的希望越大。人们的偶像能够被救下,而“格罗德曼”和“汤姆·莫特莱克”的呼声混杂在欢喜的喝彩中。
“死去的亚瑟·康斯坦特,”伟大的犯罪学家继续说,“过来几乎住在我对面。我和他相识了——他是个可爱的年青人,一个绝佳的试验对象。我不知道我是否对一个人如此感兴趣过。当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我们之间就有一种奇特的共鸣。我们相互吸引。我直觉地感到他就是那个人。我喜欢听他热情地讲人与人间的兄弟情谊——我知道对人讲兄弟情谊就像对猩猩、蟒蛇或是老虎一样——他似乎喜欢从他专注地自愿的工作中抽一点时间和我聊天。这样一个宝贵的生命将被夺去真是可惜。但必须那样。
“在12月3号9点45分他来找我。自然我在审讯中和庭审上对这次来访只字未提。他的目的是神秘地向我咨询关于什么女孩的事。他说他私下里借了她钱——她会在合适的时候还钱。他不知道她拿钱是干什么用的,除了某种程度上联系到了他曾经模糊地鼓励过她的自我放弃上。那个女孩失踪了,他对她感到苦恼。他不肯告诉我她是谁——当然现在,先生,你和我一样知道那是杰茜·戴蒙德——而只是寻求寻找她的建议。他提到莫特莱克第二天一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