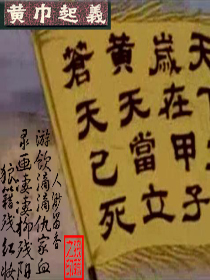永不瞑目 -海岩 著-第5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姑娘拿出了一叠信纸和一张信封,又拿出邮票。肖童说:“借我一支笔行吗?”她又拿出笔。肖童在信纸上快速地写下一行字:“西藏,乃巴,萨噶鲁村”,下面写了“肖童”二字。在写信封时他突然发觉自己根本不知道庆春的通信地址,他知道她家知道她单位怎么走,但说不清街道胡同门牌号码。情急之下,只好写了:“北京,公安局,欧庆春收”几个字,犹豫了一下,又在欧庆春下面,写了“李春强”三个字,他想欧庆春在公安局的知名度也许不如李春强那么大。
他把信装进信封,递过去,那女营业员慢吞吞地看着,一脸疑惑,似乎担心这样简单几个字会不会成为盲信。她最后还是决定替他发出这信,但把信封又递回来,指着上面的六个方格,说:“邮编号!”
肖童愣了,他说:“我不知道邮编号,麻烦你帮我查一查好不好。”
“可以,那你得告诉我具体地址。”
肖童依稀记得前门东大街那边有个院子门口挂着公安局的牌子,信寄到那里大概总能转到庆春的手里。于是他说了前门东大街。那姑娘翻开一个大册子在上面慢慢查找,直急得肖童满头是汗,门外的每一个响动都让他心惊肉跳。他想说不定欧阳天他们现在正在找他,说不定马上就会找到这里。他对姑娘说:让我来查吧,我地名熟。姑娘说:你先交钱吧,我自己查。他身上没有一分钱人民币,他毫不犹豫地拈了一张百元的美钞送了上去。不料姑娘盯着那美钞左看右看不明白。
她问:“这是什么钱?”
“这是美元、一百美元相当于八百多人民币。不过你不用找。”肖童说。
姑娘却把钱推给他,“我们不收这个,只收人民币。”
真是民风朴实,连美元都不认。肖童急得眼睛冒火,比比划划地解释说,美元很值钱的,你不信可以去问。你以后要去北京吗?去上海吗?去南方吗?这钱那些地方都认。他不知该怎样让那姑娘相信他不是个骗子。
姑娘坚持原则一丝不苟,“我们这儿有规定的,不能收外币,我们也不清楚你这钱是不是真的,有没有过期。”她一边说一边收回了柜台上的邮票和那叠已经用了一张的信纸,说:“你下次带人民币来,我再帮你发这封信,这信纸我先扣下,下次带钱来就给你。”
正说着,门口一暗,肖童没回头也知道是有人进来了。他飞快地将已经写好的信封和钱都揣进怀里。果然后脑勺响起了欧阳兰兰的声音:“肖童,你在这儿干什么?”
肖童回头一看,是欧阳兰兰和建军。脸上挂着程度不同的怀疑。他竭力自然地笑着,说:“这儿有个人会讲汉语,我们聊聊天。”
他说完便搂住欧阳兰兰的腰肢,亲热地拥着她出门,还回头挥手向那营业员告别:“以后再和你聊,欢迎你到北京去!”也许他的声音和动作太自然了,自然得一点不像临时的编排,所以欧阳兰兰马上半嗔半笑地骂了句:“你怎么见着个年轻顺眼点儿的就上去套磁,守着我你还这么不老实。”建军在屋里东看西看看不出什么破绽,便也跟了出来。
在回去的路上,男人们在一个荒凉的沟崖停车方便。肖童慢吞吞地留在后面,他看见他们走上车子等他,便背向他们掏出那封未能发出的密信,扔进了泥灰斑驳的峭壁之下。那是一个可能永远不会有人迹光顾的深壑。这时,黄昏的夕阳正使这里变成一个巨大的阴影。
整个儿晚上他的心情都有些恍惚和压抑,也很疲倦。熄灯后欧阳兰兰拱到他的被子里,在他耳边喃喃地说着肉麻的话,手脚并用地糊在他的身上。这是入藏以后她第一次向他表达床第之事的信号。但肖童厌烦地坐起身子。
“怎么啦?”欧阳兰兰不满地问。
“没什么,我很累。”肖童说:“我不希望现在伤了身体。”
“怎么伤身体啦,你这又是闹什么情绪呢,我不明白我又怎么你啦?”
肖童闷声闷气地说:“我想戒毒!”
“戒毒?”欧阳兰兰疑惑地也坐起来,“在这儿?”
“对。”肖童突然产生了这个念头,并且马上就决定了。他看着欧阳兰兰,冷冷地说:“你愿意帮我吗?”
“在这儿怎么戒?你也没有药,也没有医生。你怎么想起现在就戒?”
“对,我想现在就戒。”肖童语气坚定。他说:“你要是同意我戒,就帮我。
我想在离开这儿的时候,在我将来有朝一日回家的时候,我要像个好人一样地回去!“
“好,”欧阳兰兰似乎被他的决心所感染,“我同意,我帮你。我知道你这毒一天戒不了,你就会恨我一天。”
肖童恶毒地望着她,他觉得和她呆在一起真不是个滋味!她的每一个表情,无论软硬,都带出一股子主宰的欲望,和她在一起他的每一句言语,每一个动作,都像是一种挣扎和抵抗。他咬着牙说:“对了,是你毁了我,所以我恨你。我这毒戒不了我就恨你一辈子!”
欧阳兰兰说:“我也恨你!你老是羞辱我,晾着我,我有时候真觉得杀了你也不解气。可谁让你是我爱的第一个男的呢。我他妈爱你都爱得不是我自己了。没准儿我将来早晚有一天得毁在你手里。你这人的心其实狠着呢,我都看出来了!”
四十三
戒毒的艰难对肖童来说并非初次,但这一次的痛苦却来得异常凶猛。在这里找不到一点戒毒的药物,无论是代替性或麻醉性或辅助性的戒毒药物全都没有。肖童忽略了药物在减轻痛苦方面的作用,他只是依靠自己的体力和意志与之抗衡。也因为突然增大的对氧气的消耗,他的高山反应并发而来,有几次竟活活窒息过去。所有的痛苦都极尽能事地给他意料之外的袭击,打乱他的招架,让他昏昏醒醒。而最终支持他拼死抵抗的力量源泉,就是与庆春共同拥有未来的幻想,和那篇烂熟于胸的对祖国母亲的赞颂。那不知背诵了多少遍的演讲词配着疾风急浪的黄河协奏曲,常常响彻在他的耳畔脑海,让他的苦难变得伟大和充满牺牲的激情,让他从肉体的折磨中找到心灵的感动。他想欧庆春如果知道他的默默挣扎那一定会爱他的。她是一个爱慕坚强崇拜成熟喜欢深沉的女人。
在他最难熬的时候,欧阳兰兰让老黄和建军把他绑起来,绑在床上,任他呻吟,喊叫,哭泣,谩骂。谁也不去理他,有时他实在闹得厉害了,欧阳兰兰就忍不住跑进屋去看他,看他的涕泪交加和苦苦哀求。他说我不戒了,你给我一口烟吧,你给我烟我保证永远听你的了,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欧阳兰兰摆着冰冷的面孔不为所动,她说你再坚持坚持吧,已经熬这个份上了,再坚持坚持就熬出来了。到后来她也说累了,说皮了,索性不再说话,就坐在他身边看他折腾。那样子几乎是在欣赏他的痛苦,脸上甚至还能看出一丝得意的笑容。肖童那时心里突然清楚起来,欧阳兰兰的表情让他一下子看懂了她的性格。她是一个既缠绵又残忍的女人,既可以委曲求全柔弱如水,又在内心深处充满霸欲、热烈、执著和冷酷。妄为兼而有之。
他恨恨地想,有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经历,这样的父亲,她能学出什么好来!
她给他喂饭,给他吃烧得香喷喷的牛肉和羊肉,他不知是出于胃里的厌恶还是心里的厌恶,摆着头坚决不吃。欧阳兰兰没办法,左哄右劝最后把碗往桌子上一顿,骂了句:“你他妈爱吃不吃,谁还求着你!”她当着他的面自己吃,吃得吮吸有声津津有味。肖童转过头不去看她。他万箭钻心般地想念着庆春,就觉得自己万分地孤独。在这举目无亲的异乡的角落里,他一天到晚绳索交加,一动也不能动地忍受着酷刑般的痛苦和心灵的荒凉,他为自己而流泪。有一两次,他怨恨地想到了他远在德国的父母。他们大概充实得几乎忘了他这个儿子。他们至今也不知道他们的儿子,这半年来经历了什么样的变故。他想象着他们大概又要和那些友善的德国同事去慕尼黑郊区的乡村度假了。他知道那儿有一年四季都绿荫不断的山丘,有幽静的树林,湿润的林间小路和小路两侧时隐时现的木屋。山脚下是一片湖水,深蓝的湖里常常游犬着几只雪白的野天鹅,把平滑如镜的湖面犁出一个个人字形的微澜。是的,他相信他的父母此时就在那里,悠闲地散步,坐在湖边原木搭就的钓鱼码头上,喝着气泡丰富的啤酒,把面包撕碎了丢进湖里,让野天鹅觅食。他们对小动物一向充满了爱怜和人道主义。当然他们间或也会想起他来,会议论起他的学业,担心他被一些不好的女人勾引。但那只是一瞬,很短很短的话题,说说就过去了。从他很长时间才能收到的那一两封由母亲执笔的短信中,他知道关于他的话题就是如此。
于是他集中了一个念头,那就是一切要靠自己,他一定要坚持到底。因为他要是带着毒回去,庆春和她正统的父亲,是不会要他的。他要让他们看见,他已经彻底地把毒戒了,是一个好人了,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人了!
四天之后,他从床上爬起来,拖着虚弱的身体走出屋子,走到充满阳光的院子里。也许是这里离太阳太近的缘故,冬天的阳光也像春天般的温煦。他仰着苍白的脸,看着碧蓝如洗的天空,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想放开沙哑的喉咙大声地朗诵,想拼尽身体里最后的余力,一句一句地,仰天大喊:“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壮士常怀报国心!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他停了一下,看着站在阳光下惊奇地发愣的钟老板的小女儿,他笑了一下,冲她轻轻地念道:“这是每个龙的子孙永恒的精神!”
他觉得整个儿身心终于透出了一口气!
一周之后,他开始有了胃口,能够如常地吃饭和出门散步,晚上也能睡好,体力在明显地恢复。他甚至能骑上一匹邻家的老马,歪着肩膀一颠一颠地在坡地上小跑。晚上,他借口身体不能再有消耗,拒绝欧阳兰兰碰他,但他自己却在夜深人静时闭眼想着庆春。他几乎每天都要在幻想中和庆春做爱一次,否则就不能入睡。但每当和庆春“爱”过之后,他又会陷入一种心灵的空旷和虚无。于是他常常在梦中用各种浪漫的方式与她相会。他梦见他和她一起到了松花湖上,坐着马拉爬犁,在铃铛和欢笑声中扬鞭飞驰。湖上没有人,四周的冰峰雪峦只属于他们自己。他梦见他们去山上滑雪,像专业选手那样高水平地在雪道上互相追逐。他还梦见开冰捕鱼的夜晚。他和她一齐用力拉网,一网出水,金鳞毕现,灿若头顶的繁星,他们失去重心滑倒在冰上,周围的渔民们皆欢声大笑。他有时也会梦见明朗辽阔的天空和一派银色的山系,那当然是西藏特有的雪域风光。他和庆春驾驶着吉普车,穿越着旷野和湖泊,远处是奔腾的野马,身边是背负鼓鼓囊囊的毛织口袋,成群结队涉过河滩的羊群。天上的云白得耀眼,低得像是伸手可触。他们看见了寺庙群落五彩的经幡和辉煌的金顶。他们像朝圣的藏人一样在释迦牟尼。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像前五体投地,匍匐而拜。肖童一拜再拜长拜不起,这种藏式的拜礼像做操一样让他觉得十分有趣。拜毕起身,不见了庆春。他大声呼喊找遍了寺院,遥遥看见庆春和李春强携手走远。他拼尽全力疯狂追去,半路杀出欧阳天、黄建军和欧阳兰兰,他们拦住他,挂着满脸的怀疑,责问他上哪儿去了,是不是去通风报信?他矢口否认竭力辩解赌咒发誓。不料那位邮局的女营业员突然惊喜地喊着他的名字不期而至。她递过那封未能发出的密信,兴奋地说那个邮编号我帮你查到了,你找到人民币了吗现在可以去寄。肖童面如土色,知道死期已近。欧阳天劈手夺过那信看后缓缓撕碎,将白色的纸片从寺庙的殿顶重檐洒向空中。然后他们把肖童五花大绑,给他吸毒,注射海洛因,看他毒瘾发作,嘶声惨叫,然后把他抬上山崖绝壁,向不毛的山谷里狠狠地抛下肖童凌空大喊,灵魂已然出窍。他用力睁开双眼,酥油灯下,欧阳兰兰正在俯身温柔地看他。
她用毛巾帮他擦头上的汗,问:“你做恶梦了吧?”
他闭上眼,想从惊恐中恢复一下。
她又问:“梦见什么了?”
他睁开眼说:“梦见我让人杀死了。”
她吃惊地笑笑:“你心里准是有什么鬼了,怎么老做这种梦,谁要杀你?”
他说:“你,还有你爸爸。”
她更乐了,蛮有兴趣地问:“我们怎么杀的你?用枪,还是用刀?我要杀你,一定要让你一点一点慢慢地死,我最喜欢折磨人了。你梦见我把你大卸八块了吧?”
“你们用毒,给我吸了好多好多毒,还给我静脉注射,打进好多海洛因,然后把我扔在山谷里不管了,我就死了。”
欧阳兰兰收住笑容,把毛巾用力扔在他的脸上,说:“你到底有完没完!你吸毒可是老袁使的坏,你要记仇就找他去。甭跟我念叨。我真后悔这么费心费力地帮你戒毒,喂你吃饭,我对你有千条好万条好,你还是看不见!”
肖童拉开脸上的毛巾,眼睛看着黑黝黝的屋顶,冷淡地说:“我用不着你对我好。”
欧阳兰兰急了,扑上来揪住他就打,嘴里哭着骂着:“肖童,你给我说清楚!你得了我的好现在又说用不着了,你这个没良心的家伙!你为什么这么欺负我!”
肖童用力和她扭打,互相用东西砸对方。老黄和建军闻声赶来,叫门门不开,便破门而入,把他们拉开。欧阳兰兰扑在床上发着狠地无声哭泣,老黄连声劝着:“你们这是搞什么呀,猫一阵儿狗一阵儿的,这是什么地方你们还吵成这个样子。
要吵,动动嘴也就行了,怎么半夜三更动起手来了?“
建军见欧阳兰兰咬牙切齿哭个不停,便恶狠狠地揪住肖童质问:“你对她都干了什么?你为什么总是欺负她,啊?”
肖童挣扎着,你拉我扯又和建军扭打起来,他最讨厌建军那土匪似的架式和垮里巴唧的外地口音,以及总是刻意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