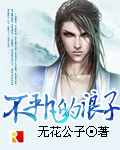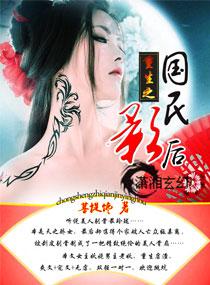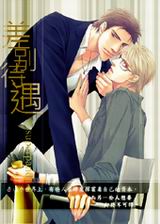国民待遇不平等审视-第3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2000年8月,北京市在海淀区翠宫饭店召开了首届“北京经济发展论坛”。其中有一个会场的主题是“北京如何率先实现现代化”。我也被邀请在此会场作演讲。十个专家,每人15分钟的发言时间,大家都顺着一条杆往上爬,我排在倒数第二。只是在我的发言里,才对计划经济的思路、对现代化的标准提出了一些质疑。人民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顾海兵先生提出了“非农化”的思想。但在那个时候,几乎没有一个人的认识达到了今天大连学者宫希魁先生的境界。
最近,宫先生在2001年6月15日的中国经济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质疑局部‘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文章。文章不无辛辣地指出,一个国家内少数城市和局部地区有可能依托资源优势、人文基础、历史遗产和权力干预等条件率先发达起来。但这种“发达”绝不能等同于实现了现代化。这不仅不是国家整体意义上的现代化,也不是局部“发达”城市和地区的现代化。因为这些局部“发达”城市和地区不是一个个孤立的实体,在被大量非发达地区保卫和渗透的环境中,它的肌体中不停地注入和流淌着非发达的血液,不管表面上如何光泽和艳丽,其内质上丑陋的一面总是存在的。
我认为这篇文章深刻就在于它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这种“现代化”的弊端:某些城市和地区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对欠发达区域的资源掠夺和生态环境破坏上,把少数人的富裕建立在多数人相对贫困的基础上,把某些繁华的城市镶嵌在衰落的乡村中间。这种局部现代化与真正的现代化标准是格格不入的,因为中国所要的不是少数人的现代化,而是多数人的现代化。企图游离于整体之外,建立起一块块“飞地”式的现代化是缺乏整体思维的一种偏私之见。
宫喜魁先生文章的可喜之处是深化了对残缺现代化的认识。他指出了局部现代化的三个危害,第一是资源过度向局部现代化地区聚集。为了保证少数城市和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在公共资源有限或短缺的情况下,有关当局必然采取倾斜政策,把有限的公共资源大量投向那些可能”率先“入现的地区。优惠政策说到底是一种公共资源。在过去的20年里,特区、开发区等享受了优惠政策,因此先富了起来。今后再也不能搞这种”锦上添花“式的优惠政策。
局部现代化第二个危害是不利于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宫喜魁同志说得好: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没有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瓶颈卡在农村。离开了包括农村在内的对现代化的通盘考虑,而采取少数城市孤军深入的战略,只能是一种失去根基的没有依托的供少数人欣赏和享乐的现代化。鉴于以上原因,宫希魁同志建议今后各地区各城市政府不要再搞什么现代化的时间表了。否则,这种局部现代化将导致更加严重的地区封锁和盲目攀比。
今天,中国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建国后50年来优先发展战略的弊端,越来越多的人将精力投入到消灭地区差别和减少城乡差别的事业中去。但在怎样缩小中国的地区差距和城乡差别上面,当前存在明显的几种思路。一种是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靠长官来拯救贫民,靠国家配置资源,加大西部地区的公共设施投资,增加这些贫困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另一种思路是看重制度创新,打破生产要素流通的各种关卡,取消对公民自由迁徙的限制,取消各种不公平的国民待遇,按市场经济的法则办事,按平等的原则办事,穷富地区的差别会自然缩小。试问:这么多年来,几千万四川民工流入东南沿海地区做工,这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吗?不!完全是千千万万人民自发的创举。人民不需要什么救济和恩赐,人民最需要的是合理的制度和公平的国民待遇。如果户籍制度早被取消,现在不知有多少贫困地区的人口已经在发达地区安家落户。
中国今天最重要的事情是体制创新和制度创新,没有新制度,任何量的调整都是短期行为。胡鞍钢同志认为东西部地区的知识发展差距要明显大于其经济发展差距。西部人均综合知识发展水平仅相当于东部的35%,获取知识的能力仅相当于东部的14%,吸收知识的能力仅为东部的81%,交流知识的能力仅为东部的31%,人均外国投资和互联网普及率分别是东部的8%和12%。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国情背景,导致中国形成了明显的三大发展差距,即经济发展差距、人类发展差距和知识发展差距。因此,缩小这三大差距的方法是知识投入。
在这里我要提出一点疑问,不进行制度改革和国民待遇改造,光进行知识投入和资金投入能管用吗?落后地区和贫困人口所需要的仅仅是外部输入知识、技术和资金吗?错了,重要的还有制度,重要的是打破束缚人们自由流动的桎梏,重要的是平等的国民待遇和公民权利。
胡鞍钢同志看到中国城乡之间和东西部之间存在的知识差距,但教育落后并不完全是东西部差异的真正根源,也不是这些地区贫穷的根源。在统计数字上,西部地区的受教育水平和程度都不低,新疆、青海、内蒙和宁夏地区的从业人员大专以上的文化程度都远远高于福建、浙江和山东,但经济实力却差得不可同日而语'请参看下表'。对此现象如何解释呢?
1999年各地从业人员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所占百分比
地区 大专以上 地区 大专以上 地区 大专以上
全国 3.8 江苏 5.0 浙江 3.0
北京 23.0 广东 5.0 重庆 2.7
上海 15.1 黑龙江 4.9 贵州 2.7
天津 11.1 宁夏 4.4 河南 2.3
新疆 10.5 陕西 4.2 四川 2.2
辽宁 7.0 湖北 4.0 山东 2.2
吉林 5.9 河北 3.9 安徽 2.0
青海 5.3 湖南 3.4 云南 1.4
山西 5.1 江西 3.3 广西 0.9
内蒙古 5.1 福建 3.2 西藏
海南 5.1 甘肃 3.2
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版,《经济日报》2001,3,11,
看完这张表,我们可以得知,影响人们贫富的真正原因不是技术,也不是知识,而是制度,是思想观念。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人们就可以明白这种现象,有些国有企业在技术、设备和人才方面都比民营企业高得多,但就是竞争不过民企,甚至最后破产倒闭,其原因就在于它的体制。中国今天在地区开发上不注重体制创新,仍然想靠单纯的资源倾斜和技术开发是不会有好效果的。因此,胡鞍钢同志尽管在地区差距研究方面有不少独到的发现,但说到底,这种研究仅仅停留在政策和技术的层面上,而没有上升到制度、法律和权利的高度。
由此,我们进到了一个敏感的领域,即技术救国还是制度救国的问题。我和一些工科出身的学者最大的不同是从人性出发来看问题。影响人发展的因素不仅有物质的还有法律的。经济学者决不能仅在经济圈子里打转转。
最近,樊纲的研究所和茅于轼、张曙光的研究所都测算出了数字。从经济活跃程度上看,民营经济成分越高的地区经济越活跃,经济效率和效益越高。反之亦然。在2001年5月18日天则经济研究所举办的双周学术报告会上,茅于轼先生向大家给出了更详细的数字:民营经济成分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当地人均GDP就增加1640元。这种研究就上升到了制度的和体制的高度,使人们一下子看清楚了问题的实质。
因此我认为,开发西部不能做表面文章。不在体制上加大改革力度,不公平国民待遇,不搞活民营经济,不在公民权利上加大落实,经济不会活跃。就象青海和宁夏,尽管从业人员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所占的比例在全国排第七位和第十四位,但其经济就是没有这一比例低得很的浙江和福建。至于说新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从业人员中所占的比例高达10。5%,位居全国第4位,但人均GDP却位居全国第12,与教育程度并不相称。我于1999年冬天去新疆昌吉州做报告时,顺便问了一下州委副书记当地民营经济的比重有多大,他说大约5%,或者8%。我听后感到吃惊。这种经济比例从理论上讲基本上没脱出计划经济。人民大学经济系的顾海兵教授在1999年写过一篇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文章,他经过分析,认为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比例不超过50%,可能还更低。
中国地区间到底该如何发展?我的基本思想就是打通流通渠道的关卡,一切问题一切差别都会解决。蔡昉先生在2000年《经济学茶座》第一期中有篇文章写得特别精彩,题目是“尼雷尔效应与西部开发”,建议大家有空时可找来看看。我想,这一派学者的共同思路可能就是让政府少管事的思路。你政府官员们根本用不着操那么多的心。只要实行人人平等的政策,放开关卡,地区差距自然会缩小。50年来,你已经通过人工的手段制造出一个东西部差距来,现在又要用人工手段去减小这种差距。当然我不怀疑这种手段的功效,但它决不是治本的办法,一旦手段力度减弱,差距会继续显示出来。因为,任何政府行为都是新的特权、新的特殊政策和新的不平等。其结果也可想而知。
总之,中国巨大的城乡差别和地区间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是人身歧视性的发展战略的结果。在这种发展战略的指导下,中国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正在越来越严重,问题也越来越多。集聚起来之后,早晚要爆发出来。
4,缓慢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由于严格的户籍限制和城乡两元化结构,中国的工业化发展也出现了独特的特征,这就是80年代乡镇企业的兴起,导致中国工业发展的分散化。这种村村点火式的“点”污染,对中国的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破坏,其工业发展的成果有的比不上带来的恶果。特别是这种分散式的工业化不利于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大批工业人口仍然散居农村。乡镇企业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农村农业生产的工业化和机械化发展,这种农业的工业化运动,反过来又对农村的劳动力人口形成巨大的积压作用,造成农村的剩余劳力越来越多。当城市吸纳不了这些过剩的农业人口时,剩余劳动力便在中国农村积攒起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忠法等人的研究十分有价值。他们三人于2000年11月29日在《中国经济时报》上发表一篇十分有份量的文章,文章说:目前我国农业的从业人员3。48亿,占到农村劳动力总数的70。7%。进入90年代以来,农业领域容纳劳动力还出现绝对量下降的新情况,平均每年下降0。83个百分点。这种加速下降意味着农业要素投入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资本要素加速向农业流入,我国农业已进入资本替代劳动的加速时期。国家及社会各方面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力度,使农业资本积累的速度明显加快。变现在资本存量上,1980…1990年全国农村年末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从1082亿元增加至3898亿元,年均增长13。7%,1990…1998年,农村年末生产性固定资产值增长至17940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21%。比前10年提高了7。3个百分点。农业资本和劳动比率的提高,这一趋势今后还会进一步强化。
韩国、菲律宾、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四个国家在70年代初和90年代初期,都曾推出农业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措施,其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新增就业之比分别为1:1。5、1:2。9、1:2。5、1:1。9。将四个国家的情况平均起来看,第二产业每增加1个就业岗位,第三产业相应地增加1。5到2。9个就业岗位。但在我国乡镇企业高速发展的1979年到1996年,乡镇企业中的第二产业职工净增7839万人,交通运输和商业饮食等'不是第三产业的全部'仅增加2739万人,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新增就业之比为1:0。35。按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对我国乡村劳动力行业分布的统计口径计算,1984年到1996年,上述比例也不过是1:0。65。如果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就业比达到1:1,20年间至少可多创造3000万到4000万个第三产业的就业岗位。要是比例达到1:2,那就要多增加大约一亿五千万人的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据此判断,我国第三产业的就业容量有很大潜力。到2015年,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应达到3。7亿,比现在净增1。8亿人。
中国经济的工业比重已经达到83%,农业比重只有17%。按理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这个时候,至少要有一半的人口集聚到城市里去。但我们国家目前只有16%多一点的人口在城市里生活。我国现在所说的城市人口,其中包含了近年大规模县改市、县改区带入的农业人口。如果以户籍管理的非农业人口计算,城市人口比重仅为16。1%。从个例中更能看出城市人口中存在虚数。例如山西晋城市人口200多万,城镇人口比率达到72。2%,但非农业人口比重为仅17。2%,城市建成区内人口仅占全市人口的11。4%'见王远征的文章,《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9月1日'。
所以,当前对外宣传的中国城市化率30%这个数字,实际上是建置城市化的数字,而非人口城市化的数字。建置城市化是把一个城市所管辖的农村人口都算做城市人口。譬如,青岛市市区人口仅200多万,加上几个郊区县的人口为700万人。对于这种现象,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苏刚同志曾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发表在2000年9月1日的《中国经济时报》上,他在政策建议中提出了“建置城市化还是人口城市化?”的问题。他说:“建置城市化带来的负面效应,一是虽然增加了“城镇”人口,却没有相应减少农业人口。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可以归结为农民大军的消亡,即农业的工业化。否则,城镇人口就是一个无意义的数字。美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2500人以上的聚居地就定义为城市,单照此口径,我国早已城市化。二是城市行政辖区扩大和城镇数量增多之后,城市功能却没有相应增强,人口、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