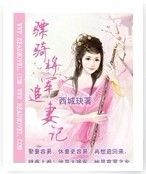将军令1-3部全 by偷偷写文(古代 君臣 强强 虐恋)-第6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陈则铭本来低着头只做恭顺状,听到此处忍不住抬眼望了望萧定。
萧定一直注意他的神情,正双目紧盯着他。
于是这一眼两人都没躲得过。
视线一交错,两人都是暗惊。对视了片刻,陈则铭到底先垂下眼帘,道:“臣曾误入歧途,所言所行大逆不道,实在是为家族蒙羞,怎么敢称这个忠字”他说完离座跪倒。
萧定起身,亲手托住他的右臂,将他扶起来。再往他脸上瞧了片刻,郑重道:“爱卿此刻为国出战,即为忠。”他说这话时神情语气都是异常诚恳,容不得人半点怀疑。
陈则铭静静看他,明知他大概是在做伪,居然也有几分感动。
待谈话完毕陈则铭告退出殿,近侍将他领到隆宗门内北排房处,那是侍卫及轮值大臣们的值房,陈则铭曾任宫内守卫之职多年,对这里各处景致真是熟之又熟。
那近侍择了一间无人的房子,送陈则铭入室。出门后身后突然一暗,回头看那屋里的灯已经熄了,这才放心离去。
此处地近宫门,哪怕深夜门楼上也是灯火不熄,是以那屋里头虽然暗,但还是隐约看得清楚陈设。那内侍若是多事,临走前往里头瞧上一眼,便会看到床上被褥丝毫未动,而桌前,陈则铭衣甲未除,正坐在那里出神。
萧定叫了他来不过是笼络之意,并没什么紧急之事。
这显示出了萧定心中的纷乱。局势太严重,谁也不曾经历过。少粮便会引发暴动,从民间到朝上,问题一层层在剥离显现,萧定只怕也已经开始弹压不住局势,才会深夜召他入宫。有时候人需要一个同伴才不会觉得压力有那么难撑。
陈则铭甚至想,此刻的萧定貌似沉着,可实际上应该有些方寸大乱了。如果自己在方才的见面中追问当年的事情,萧定甚至也许会立刻摆出悔不当初的低姿态来。三代忠良?陈则铭几乎要笑,萧定要克服多大的心理压力才能面不改色这么夸他。可萧定这个人,关键时刻拉得下面子,别人忍不了他也能硬忍着,这是陈则铭最佩服他的地方。
最终陈则铭什么也没说,他让这段戏如同它剧本上所载的那样和和乐乐地演了下去。
那些往事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以后的某个时刻。他隐忍着,等待着,韬光养晦,为的都是期待有一天能一偿所愿,在此刻的他看来,只有那个秘不可宣的愿望是要紧的,其他的都没什么。
何况萧定那种焦头烂额的感觉他也有,他们同扛着一个重担,坐着同一条漏船,同舟共济才是解决之道,暗下绊子只会自取灭亡。
但萧定的防备他也还是看得到,他警惕着,并不让自己的真意露出来,又有些怜悯之意。在两人交谈的过程中,他看到萧定咳了好几次。当初三度梅他只来得及下两次,但那药性情大寒,到底还是有作用的。
奇怪的是萧定一个字也不提,陈则铭很感慨,他居然真做得到一个字不提。
如此静坐,直到醒过神来,窗棂上不知何时已经透了些微光。时近天明该开宫门了。
陈则铭行到宫门前,正见到宿值将领领队过来,两人恰是旧识,那将领与他寒暄几句,叫人牵了他的马来。
陈则铭接过缰绳,并不立刻上马,拱手辞别后,却徒步而行牵马出了宫门。
在他的脚步声和衣物摩擦声中,马蹄得得回响的节奏显得很是突兀惊人,走了一会,陈则铭回过身。秋日的晨雾稀薄冰冷,隐约可见远处宫门洞开,似如蟒兽之口。
朦胧不清的天光中,只有高大巍峨的宫殿默默地注视着他。
他看了良久,最终上马疾驰而去。
这是个雅致的小院落,白墙黑瓦,墙头上探出来的全是绿得仿佛能滴水的青竹枝,跟水墨画似的。
陈则铭站在门前,轻叩门钹。
金属敲击声在巷子中悄然回荡,也没人出来看,不知道是这街上的人背井离乡全走了,还是这情景众人早习以为常。
良久,那门才“吱——”地一声打开,门槛内站着个俊秀小童,无精打采地边打哈欠边擦眼的样子慵懒可爱,几乎也能入画。
陈则铭道:“这位小哥,你家王老先生可还在京都?”他声音轻柔低沉,似乎是怕打破了这一片悠闲宁静。
那小童把手垂下去,仰头看了片刻,这才恍然大悟:“你是陈将军?”
青青已经很多天没见过陈则铭。
作为一名身怀六甲的孕妇,她实在是很希望有人能偶尔来自己跟前嘘寒问暖一下,可她的丈夫在打仗,她只能在家里等。
陈家虽然是号称将门,可在这方面的消息并不灵通。主要靠顾伯每日往返送药,才能从军中带回些讯息。
于是每天送药之后,青青总是要叫上顾伯问上半天。
然而顾伯说出来的东西却总是很有限——他见到陈则铭的机会也很少。他只知道仗天天在打,人不断在受伤,而陈则铭总是很忙。
青青很郁闷。
顾伯的回答千篇一律,她几乎都能背出来了,然而她还是坚持每天亲自与顾伯问一遍,哪怕从顾伯口中吐出来的只是相同的那几句话,可知道了陈则铭依旧平安,她也能安心些。
日子在等待中一天天过去。
渐渐地,身处深院的她也知道情况不妙了。顾伯不断地叫苦,让全家人都知道了米价飞涨的传闻。粮油越来越贵,所幸家中仍有富余,还支持得了几天,可几天之后呢。全城都开始陷入一种惊恐的情绪中。顾伯每天都反复叮嘱下人仔细锁门,唯恐有人借乱生事。
这些都有老管家在管,并不需要青青过问,青青也没心思搭理。此刻她最忧心的是陈则铭,城里头这样的情况,陈则铭心中该多难受呢,这时候这卫城的任务多艰难哪。
她没料到这天清晨一开门,她抬头第一眼看到的,居然就是让她牵挂得无法入眠的这个人。
陈则铭站在屋外,抬着手似乎正准备敲门,看到她出来,不禁有些讶色。他目光往下滑,此时青青腹部隆起的程度较先前已经更加明显。
陈则铭看了片刻,抬眼再看青青,微微笑了。
青青目瞪口呆,张口看着甲胄未除满面倦容的丈夫,半晌叫不出一个字。
眼见青青眼中已经要滑下泪来,陈则铭伸手将她拢入怀中。
青青将头靠在对方肩上,泪眼朦胧地看着本来站在不远处的顾伯突然局促起来,然后蹑手蹑脚地离去。
陈则铭回家已经有一会了,与顾伯商谈了家中事务,才绕到后院来看青青。
待入了屋中,陈则铭又叮嘱了她几句,无非是要小心身体之类的话。青青小心翼翼地仔细来回看他,陈则铭笑道,你没见过丈夫戎装的样子吗?
青青心跳不答。
两人谈笑了几句,陈则铭从怀中取出一封信笺,叫她仔细收着。
青青接过,那笺上不过写着一行地址,字迹也很熟悉,就是陈则铭自己写的。
青青心中纳闷。
陈则铭收敛了笑容,道:“这是陈家一脉保身立命之要物,你收好。将来我若是战死沙场,你便找个机会将此物呈给杨大人或者韦大人,再找机会离开京城,陈氏如今只我一个独子,总不能叫血脉断在我这里。”
听完这番话,青青怔怔看他,不禁焦急惊慌起来。
陈则铭微微叹息,合掌将她的手握住,道:“只是以防万一。”
青青被他握了半晌,冰冷的手指才暖回来,看他面上笑容,心中痛楚又不忍多问,只能按捺心中的忐忑将那纸笺藏入自家的首饰盒底。
青青一直记挂他头痛之症,问询之下陈则铭道自己方才已经去寻了新药,叫她不要在意。
这么说了一阵,到了陈则铭再要离家时,青青黯然想这一别两人也不知道何时能再见,终于忍不住道,老爷你要好生保重。
陈则铭回身笑一笑:“将死战是种福气,可不是人人轮得到。”
青青知他是在说笑,只想凑趣挤个笑容,挤了半天却是满眼泪花。
陈则铭慌了手脚,连声道是自己说错了。
青青泪中含笑:“老爷你就不能忌讳些吗?”
陈则铭看她半晌,微微叹息了一声,又振作精神出言安抚她。
顾伯那里早将马牵了来,在门口候着。待青青平静些,陈则铭出门上马而去。
青青追到门前,只见街头那个纵马的身影越来越小,终于转个弯不见了。青青心中难定,回屋拿出那纸笺细看,却还是看不出端倪。又见那字迹遒劲,铁画银钩隐有金戈之声,不禁将那贴子捂在胸前,半晌方能安心些。
几日过去,京中粮荒愈加严重,青青这日身子沉重,起身晚了些。正洗漱间听得院外喧嚣,连忙派丫鬟询问。
隔了一会,不见丫鬟回转,倒是顾伯慌张奔跑而来,一路叫嚷挥舞着手臂。青青惊讶,只听顾伯口不择言道:“不好了不好了,乱民乱民在砸门。”
青青不禁惊骇。
这些日子,因为粮荒,京中纷乱异常。左右邻舍中也有家境雍实被饥民抢的,陈府因为陈则铭早年驯了几名护院,身材壮硕,弓马强劲,还有些震慑力,一直无人敢上门,可如今也有人敢撩虎须了。
青青慌乱过后,定一定神,想来那乱事的也不过是饥饿难耐,并不是与人寻仇,连忙道:“要不,就分些粮给他们?”
顾伯顿足道:“这时候哪里给得。一来是家中米粮也不多了,二来此刻若是给了一个,立刻闻声而至就会跟来上百个。人一多,场面更乱,区区几个护院和两扇大门怎么挡得住?”
正说间,门外喧嚣叫骂声更盛。
顾伯失色:“糟糕糟糕,这还没散粥,人已经越来越多了,听动静只怕是要硬抢。”话音还没落,外头一声轰响,却似乎大门被人强行砸开了,鼎沸之声立刻传了进来。
青青吓得花容失色,顾伯此刻也顾不得男女避让之嫌了,扯着她袖子直往后院地窖处跑去。
正手忙脚乱惊慌失措间,突然远处一声惊雷,恍惚间大地震动,直教人站立不稳,众人都惊住,不明所以。再愣了片刻,巨响又起,这下便听得仔细些,那闷闷的声响似乎来自城外,地面应声而颤,一声接着一声,无止无尽。
强入陈府的诸人面面相觑,虽然不明白这动静是什么,却也知道是大祸临头的征兆,顾不上口粮没到手,纷纷抢出门奔逃四散。
顾伯和青青呆了半晌,才觉察自己逃过一劫。其间,那巨响宛如闷雷,声声不绝,青青仔细辨了许久,心中猛跳,僵立原地不能动弹。
那一声声蹊跷的轰鸣,正是来自城头两军交战之处。
而此刻,城楼内本来鳞次栉比的街道早已经是一片废墟狼藉。
那残瓦破砾中嵌着一块块巨大的石头,这些巨石从天而降,入地深达七尺,所中之物无不摧陷,砸得殿前司诸军找不着北。
匈奴一夜间在城下架起了数百架巨型石砲,待天光大亮,便对着城内狂轰。丢的就是这数百斤一块的石块。这石砲从来没人见过,相似的抛石器天朝也是有的,可没法抛这种巨石,谁也不明白那些木架如何能承受这样沉重的石块而不垮塌。
前阵子的伤亡在这时候看起来已经算不上什么,在如雨般的落石下,军士的伤亡数量急剧上升。殿前司的士气一下子便散了。
这东西太吓人,发动起来声音震天动地,中者无人生还。
陈则铭突遇变故,惊骇之后,牙也要咬碎了,他总算明白了前阵子匈奴攻击不紧不慢的真正原因,原来律延是在等这个砲,可恨自己一心反击居然无知无觉。
是我偏执了!!
他的心肺都快被那股巨大的焦灼烫成灰,他不甘心自己就这么失败,然而老天总是不帮他,他恨得眼中要冒出血来。援军,杨如钦,独孤航,你们在哪里!!
京城的城墙是用糯米煮的粥合着泥砌的,号称固若金汤。然而在这样大的冲击下,它们开始龟裂垮塌。陈则铭立刻派人去修,垮一处修一处。这样的石雨中,去一百个,运气好的能回来七八十人,运气差的只回得来一半,但他没办法了,只能派人送死。
所幸这样大型的石砲难以瞄准,否则匈奴只需要对着一个点持续攻击,想修都没得修。
这样的石雨砲击持续了几个时辰,城楼上毫无还手之力。
陈则铭几乎要绝望,这时候对方终于停手。战后粗粗清点,伤亡竟达千人。陈则铭赶紧巡营,每到一处,兵士们都是惊魂未定,呐呐不敢言。陈则铭心中直往下沉,如果这个时候没些刺激,这仗是打不下去了。然而下一次石雨谁也说不准是什么时候,他吩咐众将赶紧找好隐蔽之处,以备下一轮攻击,另一方面只得破釜沉舟,大肆宣称自己已收到信息,援军正在途中,士气这才一振。
然而陈则铭心中的焦躁惊惧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做,该怎么做,该怎么做,他只念着这一个念头。
用火?石砲的木架一点即燃,可石砲的射程远在弓箭之上,射不到。用床弩?床弩的射程是够远,可缺点和石砲一样,因为过于巨大无法精确瞄准,很难射中。偷袭毁之?律延必定防着这招,定然是重重陷阱。
陈则铭绞尽脑汁,终究无果。
他心中绝望,莫非老天非要为难他,所以不肯给他赎罪的机会。萧定都给了他,可天公不给,为什么?难道他的敌人不是萧定,不是律延,是老天?他恍惚起来,可为什么,为什么要让这样多的人陪葬,他做了什么要担这祸国殃民的罪名愧入黄泉
不,不,那不是天意!他又振奋了精神。
一切不到最后,天意如何谁也不知道。他甩开那些有的没的重的轻的瞎想的可能的揣测,他没时间想那些,他想做的也远远不止于此。
他看不清脚下的路,那便只有继续往前,直到粉身碎骨的那一刻。
到傍晚,对方砲击又起。兵士们在城楼上看到匈奴兵们一队一队拉着车,车后载的就是那一块块巨石。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