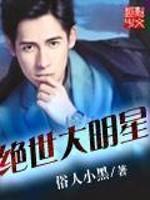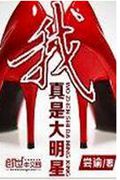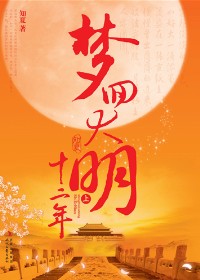大明二十四监-第42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里朱由校谈及的是一个在古代相当敏感的话题,那就是官与吏的区别。在后世也许看不出来什么,也就是一个市的局长和该市的一个县长,都是地市级干部而已。
但在大明可不是这么混淆不明了。官是官、僚是僚、吏是吏,等级相当的森严壁垒。
地方上有官,有僚,有吏。官就是正职,即长官;僚就是副职、佐贰。即僚属;吏就是办事员,即胥吏。
官和僚都是官员,有品级(比如知县正七品,县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叫“品官”。又因为自隋以后,官和僚都由zhōng yāng统一任命,因此也叫“朝廷命官”。
吏则“不入流”,由长官自己“辟召”,身份其实是民。也就是说,官僚都是“国家干部”,吏却只好算作“以工代干”。他们是官府中的“服役人员”,其身份与衙役(更夫、捕快、狱卒之类)并无区别,只不过更夫、捕快、狱卒或服劳役,或服兵役,胥吏则提供知识性服务而已。因此胥吏地位极低(常被呼为“狗吏”),待遇也极低(往往领不到薪水,不在体制内,工资有时是由官发的)。
此外,还有一条规定,就是胥吏不能当御史(监察官),也不能考进士。官和吏,就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了。
从身份上讲,官是上等人,是人民为他服务的;而吏则是下等人,是为官服务的。
当官的职责是根据自己施政理念发号施令,治理辖区,所谓“一朝把权握,便将令来行”是也。而吏的任务则是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为自己顶头上司服务,所谓“学成文武术,售与帝王家”是也。
官与吏的不同归宿。这归宿简言之就是官流吏留。过去说“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是三年一任,而吏则不然,他们是土著世守。
不过在京城,这种壁垒已经被收入的巨大差异打的乱七八糟了。京官穷得不得了,京吏却是富得不得了。京官念经书写八股出身,做官后什么都不懂,除了靠那点可怜的俸禄之外,并没有什么外快可捞,相反那可怖的迎来送往以及京城的高消费,让他们的日子过的苦不堪言。这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言官们一个个靠着‘卖嘴’过日子,而没有这种发言权的,只能干靠了。比较李祖白就是如此人物。
京吏却是世代传袭,每一官署的一本账簿都烂熟于他们胸中,官员非仰仗他们不可。他们要是拿了蹻,则什么事都办不成。
吏、户、礼、兵、刑、工,国家的大事,都出于这六个部,试问吏部的官员对升迁、铨叙、捐纳、京察、大计等等,主管的官如何懂得了许多。
户部的天下钱粮会计、向朝廷入库银两的成色,户吏色色当行,jīng明无比,若不讲好“斤头”,解京饷的官员休想完成任务。
礼部虽比较清简,但如果想弄点封诰、易名等虚名,若不向礼吏打点,势必一事无成。(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m。阅读。)
**书网更新快纯文字;
第733章吏制改革
兵部更是不得了,尤其是出兵讨伐后的军费报销,若不与兵吏打点讲好“斤头”,则种种挑剔,层层驳回,穷年累月,不得竣事,而且这种打点是公开直言不讳毫无顾忌的。诸将想拿到粮饷,不掏点羊蛋钱,当然是不可能的了。辽饷贪墨案中以兵部这些吏员伸手最多。
刑部的书吏也是利薮。但他们却有着生杀大权,人命关天的大案、要案,都要经刑部这一道坎。谁不要起生还生或死里逃生,刑吏能够把已定刑要正法的犯人救活过来,这不是深谙律例的刑部司员办不到的。传说刑吏都有舞文弄法瞒天过海的办法。说是江南有一富家子弟犯了死罪,部文已经核准,钉发文书递到便要行刑。刑吏得了巨贿,把发往江南的文书和发往云贵的文书互换一下,到达后双方发现犯人之名有误,只得退回刑部更正,如此往一来,耽搁年月不少。而刑吏又早已算好,在这期间必逢着皇帝、太后万寿之类的庆典,一定颁施覃恩,赦免或减刑天下罪犯。这样,一个死囚便不致斩决了。而刑吏这种错封文书之失,则并非什么重罪,只是革去吏职而已。
工部虽居六部之末,其利更厚。皇帝死后葬的坟墓,叫作“山陵”,其建造工程便叫“陵工”,当皇帝的毫不忌讳,一登了基,便要兴建陵工,而且皇帝一天在位,陵工一天不能修竣,拆拆修修。有的命长皇帝在位六十年,陵工便要兴建一甲子,这笔费用每年报销,其实都入中饱。此外如皇帝的大婚,官殿的缮修,尤其是特大的工程项目,;以及黄河惟恐不决口,决了口便得发放大量治河经费,叫做“河工”,种种工程费用。能够实际到工的。据说能有四成,便可算是廉洁奉公的了。当然,工吏凭着他们的本领和商人勾结去搞那些银钱,自然不便独吞。工部司员乐得沾些光。开一眼闭一眼。
六部书吏之富。可以敌国。有了钱便可使鬼推磨,若有人敢得罪或惩治他,报复起来。可使一二品大员丢官。书吏的气焰之嚣张比起闲散的京官要强的太多了。
所以京吏比那小京官更加的牛气轰轰,京官只能守着这个官是官,吏是吏这块遮羞布了。
朱由校对此情况也通过情报部门了解到了一些,但管又能管得了谁,风气尽然,他一个皇帝工作者整天把心思放在吏员的反腐倡廉上,还干不干点正事,最好的方式就是把这些吏员全部的撤换掉。
对于官员的大材小用,朱由校也是相当的看不惯,在他看来,一个市长,不去为百姓办点实事,把经济发展上去,整天的泡在公安局、法院、教育局,税务局里办着各局、院一把手的事,这是多么可笑又可悲的事。这种情况必须得改过来!
“皇上请慎重,这官与吏之间,绝非可以并提之事。官为与国同休之人,而吏只是被官员役使之人,岂可同日而语。”
朱由校,将官与吏这层壁垒要给捅破,这一下如果让官员们知道,还不一下子捅个马蜂窝?从九品官到一品官,这十八级官员,估计一下子都能跳起来反对,十年寒窗、铁砚磨穿,考取的功名,却与下等人看齐了。这让他们情何以堪?
孙承宗相当的激动,他也是官员,当然无法接受这等等于践踏蹂躏官员权威的评论。半天不说话,憋出来了这话。那样子就差跳起来大骂昏君了,这是官员不能忍受的极大污辱,就象是有一天,县太爷与一叫花子一齐坐堂审案一样。
“孙老师无须着急,现在官不如吏的情况比比皆是,说是官员贪墨,其实比起酷吏的吃喝拿卡来,对百姓所扰更重。朕免除天下税收,最大的原因恰恰针对的就是酷吏。而在京官之中,吏的待遇比起京官更是强上数倍不止。有的官员的确在办事能力方面不如一位能吏,这些都是一种畸形的现象。”
“皇上此言倒是符合时政,吏的素质参差不齐,的确害人菲浅。”朱由校的话的确如此,读书人的出路很窄,最地一用是书生,直到考出了秀才来才可以有免税、免遥役之类的好处。再到中了举人之后,路子才宽了起来,要么直接的考中进士为官,要么当个西席教个书,当个幕僚之类的。孙承宗就是选择了教书。
“朕想着改革吏制,朕所要做的是天下无吏,并非将如今天下的吏一一的变为官,而是让越来越多的有官身之人却闲置在家的举人,取代吏。首先是人员问题,想我大明,每三年才有一次会试,名落孙山者何其之多,这些人空有一个举人的名号,却没有实际的职责,空闲在家等着实缺。可以将这些人组织起来培训专门的业务,然后再经考核,充抵到各地去担任。”朱由校想的不是将原有的吏提到官的位置上来,而是将‘官员预备役’提了进来。
对于大明的酷吏,朱由校没有半分的好印象可言,他们仗着身份,在大明狐假虎威,四处的渔肉百姓,甚至敲诈低级官员。这种‘大明窗口’的**,直接导致了百姓对于大明政权的一种极大的不满,再加上一些诱因。使得遍地峰火,一发而不可收拾。大明的灭亡有人说亡自自身,而这个自身之中,酷吏占的比重相当之大。
所以挖掉这块大明的腐肉,是重中之重。朱由校废除税收制度,利害攸关最大的就是这些酷吏。所以他们的反对也是最大,各地冒天下之大不韪违反这种硬性规定的,也就是这些酷吏,没有了税收这块收入,他们的损失相当之大。朱由校对此实施了最为严厉的打击,抄没财产、没收房屋,罚款苦役,受百姓围观嘲笑,以敬效尢。
想要将酷吏们清理出去,在这种那就得找一批人一代替他们,否则只会是一鸡死,一鸡鸣,治标不治本。大明的举人大军也是相当多的。有明一代二百余年,出的举人总共有十万之众,而在各个时期也存活在各个时代的举上也是几千之多。
现在将新科进士一网打尽,收拢到自己的麾下,以皇庄的形式让他们学习,接受自己的改革方式。而后再把全国的举人来个一锅端,慢慢的以实务出发进行培训,让他们接受自己的相对高效的机关效能。长此以往,这天下的官员都将是出自自己之手,都是自己的势力。各地的发展当然的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各项改革还不是自己说了算,哪里会有什么阻力可言?
开创以官为吏的局面,这是一项最为省心的一种方式。乡试之后所中的举人,这个举人就代表着有了一张官场的入场卷,他们的身份就是官,但如果没有官位实缺给他们,他们只能在家里闲为吏之职却担着吏职。
所以说乡试也可以当作为官员资格赛。中举了,就拥有了这个资格,但有了资格,并不一定就能当上官,许多的人,终生与官场无缘。他们这批举人在百姓眼里是个举人老爷,但在官员眼里比秀才也就高一级而已,什么都不是。以前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有个免税权,有人将产业安置到他的名下,借以逃税、遥役。国家是一分钱都不会给他们。
如此将这批人拉过来,集中办个职业学校,专门让他们学习一下吏的业务。他们带个从九品或者八品的官身到各地去,不会引起太大的反弹。几年下去,潜移默化之下,中举之后就有官当,并不误考进士,这个条件对闲云野鹤在家,看着官员无比渴望的举子们也算是多了一条路。
而随着每年举人的选出,加上全民教育的推广,举人们会越来越多,吏这个词,就会成了历史,而不必等孙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再来去除了。
“皇上之计倒是两全其美。举子的辛苦,老臣也是经历过的,因不愿靠着免税而占大明的便宜,所以老臣当年也是充当了教习,辗转到了大同教书谋生。直到中了进士,情况方能好转。”
“孙老师之言朕道知晓,比如宋家兄弟、孙元化、蒋秉采他们中举已经十年了,但并没有什么俸禄在身,宋应升哥俩,坚持着走进士之路,四次未中。孙元化则跟着徐爱卿或者是袁崇焕以谋生,而唯有蒋秉采幸运一些,到了山西当上了一个县令,之前也是毫无生计。他们在举人当中,还是幸运的,多数的举人,则只是靠着祖产,或者接纳族中、邻里的土地,以免税名额而取利。如今天下免税,这项收入也被朕给堵死了。此次正好给他们找条出路。”
举人免税赚钱的方式很简单,就是收了别人的土地,本来按国税该交一两银子的,搞到他的名下不用交钱给国家了。然后举人自己再收个半价七折之类的。(未完待续。。)
第734章海西女真
这个损失当然是国家的,本来好好的税收,让举人一搅和,收不成了。而这种事情又恰恰是大明土地兼并的方式之一,这种方式都是百姓自己带枪投敌的,怪不得别人。
因为假借举人的名义以达到免税的目的,是他们私下达成的协议,这种私下协议一般是没有纸面上的东西的,好家伙,这是明显偷税漏税的违法行为,谁会找头疼来个白纸黑字?只是大家这样实施罢了。
但那假土地买卖协议却是白纸黑字的契文,并且由官方认可的。程序相对复杂一点。
契文先由卖主买主双方商定写就,并经中见人册坊、里甲的见证,这就是世俗所说的“白契”,白契有约束力,但缺乏最终的法律效力。要使它具有法律的效力,必须获得官府的认可。要想获得官府的认可,必须将白契变为“赤契”。使白契变为赤契还必须经过买主的税契程序。税契就是由买主或买卖两主呈请县衙查验明白,如果条件具备(主要是田地差粮推收过割),再由买主缴纳契税,县衙于契书上钤盖县印。一经钤盖县印,白契就变成赤契了。而后官府用来确立土地产权的鱼鳞册与定遥役的黄册也相应的作出了更改登记。赤契给还买主,田地买卖的程序便告完成。
这点有点象后世的房屋、汽车船舶买卖,是要式法律行为,但私下的协议一样有效。
以后的事情谁又能知道多少?当时的举人在世还好说,以后呢?过了几代之后。这块土地的产权谁又能说的清?土地兼并自然的也就产生了。
朱由校对这种情况的百姓,只能是衷其苦、悲其命、厌其贪。不过更恼这天下酷吏,大明是三十税一的税收比例,是任何百姓都能承受起的,到了酷吏的放大器手里,百姓们却不堪重负苦不堪言起来。族中、乡亲但凡有人中举,那是削尖了脑袋瓜子挤着要把田地给人家送去。
“孙老师,如此就先按着内阁出题,朕着徐爱卿代朕在京城走一下程序吧。”徐光启虽是工部尚书,但也是德高望重之辈。将此荣誉让他来做。还是比较合适的。“然后将这批新科进士送到辽东来,朕亲自赐其御宴。”
“是皇上。”
两人又在进士来辽东的问题与举人培训吏员职能的事情上商量了一会,最后敲定下来。
“侯家的破灭无甚可说,赵率教此战倒是给蓟州铁血长脸。送到沈阳没有多大的意义。还是送到京城行刑更有教育意义。大明百姓现在最关心的就是辽东之事了。”话题一转。开始谈及了辽东之事。
赵率教被扔到了山海关。特别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