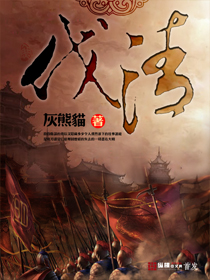伐清-第26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以就将计就计,送贼人一点银子,争取时间以加固城防”
“这都是废话,”林起龙听梁化凤把他们商量好的、万一朝廷对这里事情有所耳闻时的辩解之辞又拿出来说了一遍,不耐烦的催促道:“邓名就是来敲诈勒索的没错,但他说这话是为了什么呢?”
“邓名见我们给他贺中秋,又送去了重礼,知道银子多半能够到手,所以也想帮我们找个台阶下,就说他这次是来武装走私的,这样他不攻城略地也就是顺理成章了嘛。”梁化凤一直觉得邓名很上道,在南京的时候虽然两面下注,但确实遵守诺言,信用很好。
“哦。”林起龙细细品味,觉得确实是这个道理,点点头道:“久闻邓提督一诺千金,果真是盛名之下无虚士。不过这个理由找得太牵强了,这说出去没人信啊。嗯,不过也就是一个理由而已,我们只要都装作信了也就是了。到时候他退兵也只能证明他就是个蠢货,一点走私的蝇头小利就心满意足了。”
不过林起龙也明白,将来邓名是不是肯退兵,依旧取决于他肯不肯答应邓名的要求,现在既然邓名开始释放出了善意,那他就得开始认真对待邓名的提议。
不久以后,南京的蒋国柱听使者汇报完邓名的说法,脸色却是十分阴沉:“这种说法连三岁小儿都骗不了,他是在蒙鬼呢?”
和林起龙、梁化凤不同,蒋国柱从中嗅到了阴谋的味道,对幕僚们叹道:“邓名地想干什么?”
如果邓名除了上次的那笔钱,还向蒋国柱讨要一笔可观的赎城费,那蒋国柱或许就会放心。但现在江宁巡抚对邓名的真实目的一无所知,就感到非常紧张,又对周围的幕僚说道:“上次邓名是要我们放心,要银子,固然条件十分苛刻,但本官也好见招拆招。这次邓名却遮掩着不肯说出他真实用心,难道他真的想打江宁吗?”
没有幕僚能够回答蒋国柱的问题,听江宁巡抚这么一分析,两江总督衙门的幕僚们也发觉事态严重,只要能守住城市,私下里的交易怎么都好办——能掩盖就掩盖,掩盖不住还可以强辩是欺敌之计,反正城市没丢,怎么都是大功一件。
可邓名越是不肯说出来意,那就说明他所图越大,这就不能不让两江总督衙门感到紧张了。
“我手下缺人才啊。”见幕僚们都束手无策,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蒋国柱不禁有些羡慕起张长庚来,明明湖广紧贴着虁东,以前的家底也都被上任总督胡全才败光了,但张长庚就能把武昌守得固若金汤,不管背后到底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起码表面上看全无破绽。不像江南这里已经一塌糊涂,通邓通得各个府县官员人人心里有数。
“周培公。”蒋国柱轻轻念出这个名字,一年前这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举子,但现在已经名字上达天听,官升的得和做火箭一般地快。在湖广方面的宣传中,这当然是因为周培公智勇兼备,能和邓名周旋而不落下风,蒋国柱现在对此非常怀疑,并猜测张长庚是用通邓的手段保得武昌平安的。不过不管张长庚到底用的是什么办法,蒋国柱断定周培公都在其中起到了重大作用,飞黄腾达如果不是因为他特别善战,那就一定是因为他特别善于通邓。
形势非常险恶,明军五万大军就在镇江府,两江府县一盘散沙,而蒋国柱却连邓名的真实目的都猜不透。火烧眉毛的关头,蒋国柱也不在乎是不是会欠张长庚人情了,当机立断给朝廷写奏章,在奏章中蒋国柱称江南屡遭兵祸,不久前还竭力供应达素的大军,现在防御空虚无比,机动兵力被朱国治败光后已经完全没有野战能力。为了不让邓名在江南耀武扬威,蒋国柱要求立刻把达素的精兵强将从福建调回来——这个蒋国柱知道朝廷不可能答应,优先消灭郑成功,彻底消除东南沿海的隐患是朝廷一早就定下的战略。
关键在于第二条,蒋国柱称若是达素一时无暇抽身,那他强烈要求湖广派出军队进入两江地盘协剿,而他作为代理两江总督的巡抚,胸中完全没有门户之见,并不强求湖广援军听从两江总督衙门的调遣,而愿意反过来全力配合客军。而湖广援军的统帅,蒋国柱更是声称非闻名遐迩的现任武昌知府周培公莫属。
写好了给朝廷的奏章后,蒋国柱又马上开始写给湖广总督的公函,请求他派周培公率领援兵到江南来剿灭邓名。写好了公函后,蒋国柱又写了一封私信,信里蒋国柱暗示他已经无计可施了,不得不设法虚与委蛇,但却没有得力的人手去施展神鬼奇谋,说服邓名退兵。
蒋国柱在私信里恳求张长庚无论如何也要拉他一把,并拍胸脯许诺,若是能度过眼前难关,将来当上两江总督后一定百倍偿还,以后无论张长庚遇到什么难题,只要蒋国柱还坐镇南京,那整个两江就都会是湖广总督的坚强后盾。
写好了私信后,蒋国柱派心腹火速和公函一起送去武昌,同时还封了两份厚礼一同带去:一份是给张长庚的,一份是给武昌知府的。
在蒋国柱给张长庚写信的时候,邓名这里的军营里也闹了起来,张煌言本来对邓名如何对外宣传并不打算干涉,但当他问起邓名的真实目的时,仍得到了和给清军一样的答案。这就让张煌言气不打一处来,觉得邓名骗骗清军也就罢了,居然连自己都要隐瞒,真是太不信任自己了。
让张煌言生气的还不止这一件事,之前他曾私下里找过邓名,说起鲁王打算收养他为嗣子一事,并问邓名对此有何打算。结果邓名死命推辞,说什么也不肯接受——开玩笑,邓名很清楚一旦同意,势必要报出传承、族谱,这个邓名无论如何也编不圆,只能一口咬定自己绝不会宗室。
可张煌言哪里肯信,联想起文安之、郑成功的态度,张煌言就把心中的不安吐了出来,追问邓名和唐王到底有何关系。邓名依旧是推得干干净净,坚称自己和唐王府毫无瓜葛。若是邓名真和唐王没有关系当然最好,对鲁王来说,邓名是一个远房分支自然是最好不过,张煌言选择了相信,但让他生气的是,邓名还是不肯承认他是宗室。
若是邓名是某个宗室的单传,就算不是什么显赫宗室之后,张煌言也不好强逼邓名同意他的本家绝祀。如果这样的话,张煌言倒也能理解,但可恶的就是邓名说话不尽不实,死活不肯光明正大地说明他为什么拒绝鲁王的好意——若是一个无关轻重的远支、没有继承问题需要考虑的镇国将军之流的话,这当然是对鲁王的侮辱。
张煌言有心痛斥其非,但邓名死活不说身世,那张煌言想责备都无从谈起,他发现邓名这招确实很损,若是对方根本不是宗室,那继承鲁藩一事当然无从谈起。可看看文安之的信任,还有郑成功的不正常,邓名自称不是宗室就行了吗?他以为张煌言是傻子,会相信这种鬼话吗?
在继承鲁藩问题上张煌言憋了一肚子气,现在见邓名又公然撒谎,盛怒之下顾不得团结,当着马逢知的面大声斥责起来。张煌言责备邓名心胸狭隘,全然不信任其他的忠臣义士,更断言邓名若是不痛改前非,势必会断送中兴大业。
马逢知在边上又惊又佩,在心里忍不住再次感慨起来,张尚早早设局在邓名身边部署了大量心腹,现在说话就是有底气啊。当然,马逢知是绝对不会搅进这番混水里面去的,他虽然决心抱定张煌言的大腿不动摇,但邓名更加不能得罪,因此马逢知在两人说话时始终一言不发,如同一个犯错的小学生般,向后躲开两步,低头看着地面。
邓名解释了一番,但他越说张煌言越是生气,见对方根本听不进自己的话,邓名犹豫了一番,只好拱手道歉:“张尚书莫怪,其实我最初来南京,主要目的就是敲诈南直隶这里的官员一些银子。只是这个理由说出来太不好听,所以才想否认,张尚书恕罪,恕罪。”
“这又什么不好说的呢?邓提督觉得这个理由不好听,可那个最初是为了商人来南直隶的说辞,岂不是更加难听?”张煌言见邓名诚恳地道歉了,气一下子也就消了,毕竟邓名给他很大帮助,不但提供了大批的粮饷,还把从朱国治、董卫国哪里缴获来的盔甲武器都交给了舟山军,这一万多套装备和军粮、瓷器一样,对张煌言来说都无异于雪中送炭。
邓名又连连道歉,两人间的气氛就此缓和下来,见邓名和张煌言都心平气和了,马逢知又恢复了说话能力,他先是大赞了一番邓名的神机妙算,然后又恭维张煌言道:“张尚书也是天下奇才、见微知著,一开始就把邓提督的心思猜得清清楚楚,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啊,有道是风云际会、龙虎聚首”
狠狠地奉承了一通两人后,马逢知先行告退,向邓名和张煌言点头哈腰道:“末将先去视察部队了。”
两人都让马逢知自便,等马逢知出帐后,邓名奇怪地问张煌言道:“马提督说话总是这样颠三倒四的吗?”
“不是啊,这大半年来,一直挺正常的。”这几天张煌言也感到有些不妥,马逢知好像和在舟山时变了个人。
“越来越不喜欢说话了,总是神不守舍的样子,古怪得很。”邓名记得一开始见马逢知时,对方好像也不是这个样子的。
“是啊,”望着马逢知离去的背影,张煌言向邓名表示他也有同感:“就是从合营后开始的,刚到镇江的时候还不这样,嗯,就是从合营后第二天开始的,说话就开始云山雾罩的,总让人听不懂。”
“合营后吗?”邓名想了想,迟疑着问道:“莫不是马提督在我营中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张煌言摇头道。
又过了一天,邓名跑到张煌言营帐中找他:“张尚书,我每月至少都会和将校们聊一个晚上,给他们讲学,今天下午就会有一场,张尚书有兴趣来看看吗?”
“岂能不去?”张煌言一听就来了精神,他知道邓名时常会给手下军官讲课,这也是邓名训练军队的手段之一,既然如此那他想看一看。
除了执勤的那些人以外,邓名手下有三十几个上尉到场,不轮执的任堂和周开荒也和军官们一起坐在邓名的对面。侧面还有一把太师椅,是给参观的张煌言预备的。
“想必大家都记得离开武昌前,我们讨论过为何要出兵江南;到了江南后,我们也讨论过为何要控制航道上的贸易——为了打击清廷的商业,发展我们的商业。今天,我就来给诸君讲一讲,为何我如此看重商业。”邓名顿了一顿,让军官们有时间先猜测一下他的答案,然后才继续说道:“我们都知道,军队依靠国家的财富,国家财富越多,军队就越强大,而我以为,农夫、工匠和商人,在为国家创造财富。”
张煌言脸上微微露出不以为然之色,不过他礼貌地保持沉默。
“如果没有农业,我们就都饿死了,什么也别想制造,因此可以说所有的社会财富都有农业的参与。”邓名在黑板上画了一条线,指着它说道:“这就是农业,是财富的开始。”
“而如果没有工业呢,我们就只能采集野果,无法大量开垦荒地,没有船只和渔网,没有衣服,不能在冬天会下雪的地方居住、耕作。因此我想我可以说,除了采野果、光着脚下河捕鱼以外,剩下的财富都是农业和工业一起创造出来的。”说完邓名在一条线上又画了另外一条直线,然后在两根直线对面做出了平行线,画了一个矩形出来:“有了工业后,国家的财富就不是只是一根金线,我们得到了一张金箔。”
“如果没有商业,那会发生什么事呢?”邓名又停顿了一会儿,再次给军官们思考答案的时间,然后才说出自己的想法:“每个人都需要自己去挖矿、去冶铁、去打造农具,去种植棉花、去制造针线,然后给自己做衣服以我们的都府为例,如果我们没有商人,那都府的十几万人就都需要每人都有一套挖矿的工具、每人都有一个铁匠铺,每人都必须会养牛、都必须会制造并且有时间制造农具不然都府的百姓就只能穿着树皮、拿着木棍去种地。”
邓名又画出了第三条线:“这是商人从事的商业。”他画出了一个立方体:“我们得到了一块金砖,这就是国家的财富、军队的根本。”
“刚才我说的是商业极端差的情况,如果商业极端好会是什么样的呢?”邓名问了第三个问题,并马上给出了答案:“擅长种田的一对夫妇不需要自己去制造农具,甚至也不需要自己去维修农具,他需要鞋子,不需要让妻子去纳,只要努力种田就可以了;他需要衣服,不需要妻子去纺织,只要继续种田就可以了。而擅长制衣的人也是一样,他不要自己去种田,去捕鱼、甚至也不需要自己去纺纱、织布、做扣子,只要做他最擅长的那份制衣工作就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一切。”
邓名说的已经涉及到了社会分工概念,在他的前世,依靠发达的商业,人们就可以专注于最熟练的本职工作来满足一切生活需要。
给军官们一些消化时间后,邓名拿出了下一个问题:“为何鞑子需要用鞭子逼着包衣种地?”
“因为鞑子生姓凶残。”马上就有人给出了答案。
“那为什么我们的军屯也需要制定大量的惩罚规则?”邓名追问道。
“因为总有懒骨头?”大部分人都不说话,只有周开荒吞吞吐吐地答道,他对袁宗第的军屯也有所了解。
“我们生产是因为我们需要,我们饿了所以要种地,冷了所以要纺织,包衣、哈食的吃穿都被鞑子包了,他们没有需要,所以他们不需要生产。”
“对,提督说过,他们是按需分配。”周开荒记姓很好。
“是吗?”邓名哈哈笑了起来,其他人都有些惊愕,不知道为何邓名会觉得这个词如此可笑。
笑过之后,邓名点点头:“对,所以需要鞭子和酷刑,如果鞑子的包衣和我们的屯兵需要不挨打、不受苦的话,他们就需要工作,这也是一种商业。”
“有需要才会生产,通过商业我们可以向百姓提供更多的东西,如果他们需要肉类、水果、酒类、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