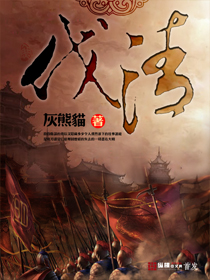伐清-第36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无妨,我要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
在李国英的坚持下,仆人七手八脚地把封死的窗户拆开。一推开窗户,就听到隆隆的鼓声和人声,声音能够传到衙门深处,可想而知城内到底有多么热闹。
“这鼓声是从朝天门那边传过来的?”李国英疑惑地问道。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几千清军昂首挺胸,在嘉陵江另一面排开阵势,还唱着嘹亮的军歌。
“用力擂鼓,大声唱!”
胡文科用力地向部下们喊叫着:“让总督大人看看我们的威武军容!”
王明德他们在忠县老老实实地呆了一个月,然后通报袁宗第,一直等到明军完全撤走才开出营地踏上归途。而袁宗第也把上次王明德他们被俘的亲兵交还。从袁部口中得知渝城无事后,返回的清军毫无心理负担,优哉游哉地慢慢返回,路上还打猎娱乐了几次——秋高气爽,马壮鹿肥。打到肥美的猎物后,王明德他们和满洲太君把酒言欢,感情更是融洽。
眼看到了渝城城旁,王明德他们决定给效忠多年的总督大人一个惊喜,他们深信等李国英得知他们把盔甲都完整地带回来后,一定会高兴得开怀大笑。
高明瞻向传令兵问清了喧哗的缘由后,不知道如何是好,回过头向床上看去:“总督大人,这个”
王明德这句话没能说完,他一个箭步跃到床边,焦急地伸手去扶又一次软倒在枕头上的川陕总督。听到了高明瞻和传令兵的对答,李国英又一次昏死过去。高明瞻大叫:“大夫,快叫大夫啊!”
第六节 密议(下)
邓名离开叙州前安排李星汉留守成都,负责训练部队;同时让任堂去奉节报信,由他自行斟酌怎样向文安之汇报咒水之难。任堂无可奈何地上路了,背地里还嘀咕为何要让自己负责去报告这个坏消息,已经两年半了,奉节从邓名手下收到的从来都是好消息。
穆谭也与任堂同行。周培公似乎要和邓名谈什么事,已经派了密使到达奉节,邓名分身乏术无法亲自去见周培公的密使,就让穆谭代劳。用邓明的话说,那就是穆谭比较善于谈判,而且和两江官员的关系也不错。
“到了奉节,我们俩一起和督师说咒水这件事。”乘船的时候,任堂满怀希望地对穆谭说。
“不,提督说了这个事是你负责的。”在人前的时候,穆谭和任堂已经开始用邓名的爵位和军阶称呼他,但私下交谈时,还习惯姓地用老称呼,不止任堂和穆谭,四川的同秀才们也是一样。
穆谭把头摇得如同拨浪鼓:“我笨嘴拙舌,不会说话的。”
“谁说的?”任堂愤然反驳道:“提督都说了你善于谈判。”
“唉,”说起这个任务穆谭也是一肚子的牢搔:“什么善于谈判,明明是臭名昭著,现在连都府都有人对流言信以为真了,偏偏我还不能说我收下的礼物都被提督拿走了。”
“不是还给你剩了些么?”
“我背了多大的恶名啊,那一点点津贴算什么啊再说,我完全是为提督效力,不然谁肯为了那么一点钱自毁名声啊?”
两人向邓名要求加薪的提议遭到了否决,邓名表示很理解他们的难处,所以给他们招聘幕僚的权利,而招募来的幕僚和参谋政斧会发给工资。
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恨不得让官员一个人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做了,怎么舍得给他们多发工资?后来朝廷也意识到实际的工作超出了官员的个人能力,一个知县要负责司法、教谕、税务等工作,需要好几个师爷协助他。但官府认为这些幕僚是官员私人的助手,朝廷没有理由承担他们的费用——无论贪污、收仪金或是其他什么灰色收入,反正由官员自己解决,朝廷不会掏钱帮官员养人。
而结果就是这些人确实成为了官员的私人助手,如同亲兵拴在将领的效忠链上一样,师爷也拴在了他们的东家身上。或许亲密程度没有将领和亲兵那么牢固,但当东家和朝廷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这些人都会毫不犹豫地站在东家一边,哪怕帮东家策划投敌也是义不容辞。
因此邓名决定把这个关系改一改,任堂和穆谭这两个人还好办,只要成立一个参谋机构就行了;但这两个人的要求提醒了他,邓名临走前制定了一个大方针,那就是包括知府在内,他们如果需要幕僚的话,可以列一份需求名单,然后像志愿兵一样签署两、三年的短期雇佣合同,幕僚的薪水一律列入官府的开支——邓名把这些人称为临时工。
在邓名看来,雇佣这种临时工有许多好处,他们属于官府的人,拿着官府给的薪金,上下级的关系会松散一些。好比知县固然会向知府拍马屁,但肯定不会像幕僚那么死心塌地。不过邓名也知道,对于旧的主人、幕僚关系,这种改变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还很难说。
最大的问题就是审核到底需要雇佣多少幕僚。以前都是官员自己雇,他们肯定不养一批光吃饭不干活的闲人;现在由官府出钱,搞不好就会有人拿这个职位送人情,安插亲戚朋友——尤其是成都和叙州的两位知府,他们既有权决定雇佣的人选和数量,又掌握拨款的权利所以邓名暂时只定了一个大方针而没有具体措施,他打算在路上慢慢琢磨如何制衡。
到了奉节之后,任堂和穆谭发现这里的大人物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夷陵的刘体纯、巴东的党守素,连以前和邓名相当疏远的施州王光兴也来了。既然刘体纯来奉节了,那李来亨自然不能动,不过他也派了一个副将和刘体纯一起来;而且据刘体纯所说,郝摇旗也正在赶来的路上。郝摇旗和贺珍达成协议,让贺珍负责指挥汉水流域的明军,而他抽空来奉节参加委员会的会议。
咒水之难让文安之的心情很不好,本来因为渝城大胜而一片欢腾的奉节也因此陷入了沉寂。不过夔东众将的反应并不是这么强烈,他们在文安之面前显得非常沉痛,但在文安之离开委员会后,大家的话题马上就转到了他们更关心的问题上。
刘体纯认真地再次确认:“左都督肯定不会来了,对吧?”
“是的。”任堂答道,他全神贯注地等着刘体纯向他说明为何奉节会聚集这么多重要人物,他看到周开荒也是一脸严肃。
“嗯。”刘体纯脸上明显地露出失望之色。
“这件事和剿邓总理有关。”
刘体纯的话让任堂又楞了一下,他当然知道剿邓总理是周培公,不过有必要在明军的会议上对敌人用敬称么?
“这位就是周布政使的密使,”刘体纯把一个富商打扮的中年人介绍给任堂和穆谭:“他是和我们一起来的。”
周培公的使者向川西众人行礼,然后开始介绍长江中下游的情况。据密使所说,明军走了之后,两江的经济形势急剧恶化,而蒋国柱和张朝都束手无策。
赋税积欠是明朝的常态,在崇祯朝以前,明朝对于积欠常常进行减免,即使实行了考成法以后,一般收到七成的税赋就视为合格。但考成法是一件威力巨大的武器,当崇祯朝把清理积欠和考成合格挂钩后,官员们为了自己的前途就拼命地征税,导致大批农民家破人亡。而满清入关以后,继续清理积欠。不过满清主要针对比较富裕的江南而不是已经破败的北方;而且清廷一直注意对灾祸地区实行减免,再加上满清的武力威胁和用屠刀建立起来的凶恶名声,清廷得到了大量的赋税,但却没有引起大规模的起义。
到顺治朝后期,为了维持洪承畴的五千里防线,清廷对两江和湖广的考成一直是以十分为合格,也就是说不管中途有多少损耗,不管用什么办法,官府一定要拿到足额的赋税。这种严厉的考成使得东南百姓的负担大增,平民一年到头辛苦地劳作,却没有丝毫的结余。至于底层的佃户更是悲惨,田租平均已经高达产出的六成。
顺治十六年,在万历年曾高达每亩数十两的南京田价就只有十两了,苏州则不到十两。农民被沉重的赋税压得喘不过气来,自耕农的负担渐渐向军屯士兵看齐,而佃户基本已经与军屯无异——没有人愿意花钱去扮演军屯屯兵的角色,当买地无利可图时,田价就随着不断地下降。
郑成功和邓名两次攻打江南,而福建、四川各条战线上的开支依旧浩大,这让满清政斧必须坚持以前的赋税政策。现在两江的小地主也开始破产,他们为了完税不得不借贷,然后卖地偿还,这导致田价继续走低。
在种地难以养活自己后,农民的购买能力也越来越低,越来越舍不得购买布匹,过年做衣服都舍不得购买商家的产品,而是完全依赖妻女的纺织,这让两江的经济作物区也开始萎缩。简而言之,满清为了继续把战争打下去而全力压榨东南数省的百姓,导致东南的财力到了枯竭的地步。
“今年秋收过后,又有很多人出售田地,而愿意购买的人非常少。江宁周围的水田,现在花个五两银子就可以买下一亩,如果买得多,三、四两也不是不行。”周培公的密使说道。
田价已经贱到这个地步,地主和佃户都不可能再购置农具,不可能增添牲口,可想而知明年的产量会继续降低。更多的人要靠借高利贷来偿付赋税,然后不得不想尽办法抛售土地还账——偏偏还没有多少人肯接手。就算是对经济原理一窍不通的两江官员,也知道这意味着离经济崩溃越来越近。
如果放在从前,蒋国柱和张朝不会有丝毫的犹豫,那就是继续按照朝廷的命令收税,如果发生民变就出动军队镇压——反正他们只是流官,民生根本无法与朝廷的权威相提并论。但现在蒋国柱和张朝都有了别样的心思,他们也和吴三桂一样,不能对民生凋敝熟视无睹了,无法一味横征暴敛下去。
只是燕京的税赋任务依旧要完成,今年他们不是战区,没有减免赋税的借口。
“周布政使的打算是什么?要我们攻打两江吗?”穆谭听完后立刻问道。
“是的,原本希望邓提督能够去江南转悠一圈,至少为几个府争取下来明年的免税。不过这次我们实在无法提供足够的粮饷了。”
“不给我们粮饷,那我们为什么要去?难道要我们自己带粮食吗?”任堂顿时怒形于色。虽然川西早有攻打江南的计划,但这个时候要是不愤怒地嚷上两声,怎么让对方知道自己的难处呢?
而穆谭没有立刻叫苦,他偷偷看了刘体纯一眼,觉得大概周培公那边还有什么名堂。
第七节 仲裁(上)
设立在奉节的委员会让夔东众将都对航运的盈利能力有所了解,对其中一些些人来说,邓名还与他们分享了一个重要的情报,那就是川西和湖广、两江的关系。其中李来亨、刘体纯早就清楚此事,郝摇旗和贺珍也心里有数,但对王光兴、党守素来说就完全是新闻了。
李嗣业抵达奉节后,根据邓名与李定国的协议,也让他知晓了川西和湖广、两江的一部分协议——高邮湖一战的内幕当然不会在委员会上公开,而其他的协议邓名认为有必要让同盟有所了解,这样才能起到委员会的协调作用。知情人都是坚持抵抗到最后的将领或是他们的子侄、心腹,第一不会到处乱说,而且他们这些人无论说满清官员什么坏话,都不可能被清廷相信。
长江航运的利润大大超过李来亨和刘体纯与邓名联合发布夷陵宣言时的预期,即使不算舟山分润的那部分,刨除给李来亨、刘体纯以、袁宗第及汉水二将的补贴,这一年来还给川西带来价值超过两亿元的收入。现在这部分收入就是邓名的财政支柱,保证着欠条的信用和川西政斧的运转,至于折合成多少银两,则会根据银价的起伏有些轻微波动。
今年郝摇旗和贺珍也采用了类似李来亨和刘体纯的政策,调整了他们和缙绅的关系,从委员会那里获得补贴,而李来亨和刘体纯则盼望着能够再提高一些他们的补贴。
不过今年的东南漕运开始后,委员会的利润就开始下降了。
首先去年很多收入是邓名勒索来的而不完全是商业收入,其次就是去年明军往来于长江上,起到了替代商船的作用。若是商业发达,沿江的百姓还可以向商船出售土产,或是提供薪柴、江鲜、粮食等物品,就像去年对明军做的一样,这些收入可以补贴一下家用,还可以进一步传递到不临江的地区,让农民可以通过多干一些杂活来补贴家用,承担赋税。而今年为了完成漕运,湖广和两江都不得不进一步征用民船,这进一步榨空了本来就疲惫不堪的长江中下游地区。
长江的航运变得更加萧条,即使农民想多做一些零活,也变得无利可图,即使把这些余力全部投入土地,也不可能进一步提高粮食产量了,只依靠土地所出本来就难以承担赋税,更不用说粮食、蔬菜、水果以及棉花的消费量和价格都在下降。
而禁海令给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以最后一击,大量的渔民和水手失业,正常的出口贸易完全中止。面对禁海令,山东、两江和福建、浙江的渔民开始冒死偷偷出海,但清廷手段极为严厉,下令各地官兵勒石为界,越过的百姓格杀勿论,为了生计而冒险的沿海百姓很多都死在巡海官兵的屠刀下。
即使是在江南也是一样,蒋国柱同样执行了严格的禁海令,第一,他根本没有把老百姓的姓命当回事,只有面对邓名这样手握重兵的人时才会容易说话;第二,蒋国柱虽然和崇明有协议,但是他同样不想把这件事搞的尽人皆知,所以除了少量几个走私码头外,其他地方执行禁海令时并无丝毫不同;最后,蒋国柱暗自盘算,若是禁海令执行的好,他和崇明的交易就可以取得垄断地位,比较容易抬价了。
现在两江的经济即将窒息,蒋国柱和张朝除了劝农桑就没有其他的应对方法,毕竟朝廷的赋税不能停。而因为不敢减轻清廷规定的赋税,所以劝农桑也就是一句空话,就算没有未来的经济理论,祖先也早就总结出来,想恢复生产就要轻税。因此现在两江的办法就只能是动员更多的官吏下乡,检查春耕、秋收,打击逃民,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