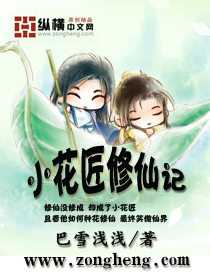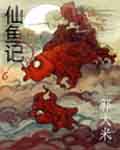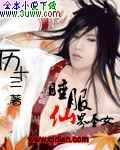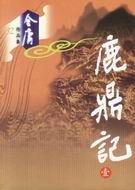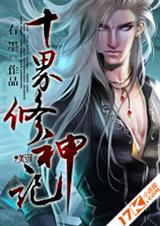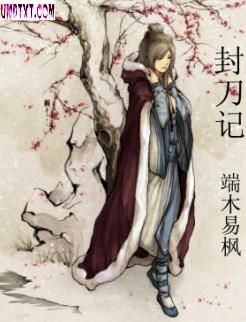清朝求生记-第18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耿额,就是造谋结党以附太子的主使之人熙命令将这些人锁拿,监禁宗人府,严加审讯,最后康熙下旨:“耿额居心暗昧,临事苛刻”,“此辈之党应族诛,以昭国法”耿额、齐世武,步军统领托合齐(即九门提督京师卫戌司令)~犯有受贿罪,全部绞刑缮被夺官幽禁,迓图则是入辛者库,去守安亲王墓了。
康熙这次虽没有对太子做什么实质的处罚,但却重创了他自复立之后聚集起来的人脉,让他不只是现在的实力大减,也使得以后也不会有人再敢投到他的门下了。太子经过此事,又遭到了康熙严厉的训斥,很是偃旗息鼓安守本分了一段时间。
太子这边是暂消停了,可是其他的事儿又出来了,因此元寿进宫的时间也是一拖再拖,不过云锦觉得这样也好,等他再大一些,抵抗力也会更强些,这样自己虽然不能和他一起进宫,但多少也能放心些。不过等云锦知道拖延元寿进宫时间的事情之后,她的心里也是有些不'炫'舒'书'服'网'。
影响元寿进宫时间的首的一件事情,就是清初著名的文字狱之一的《南山集》案发了。
在康熙五十十月,左都御史赵申乔以“狂妄不谨”的罪名弹劾戴名世,谓其“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逞一时之私见,为不经之乱道,……今名世身膺异教,叨列巍科,犹不追悔前非,焚书削板;似此狂诞之徒,岂容滥侧清华?臣与名世,素无嫌怨,但法纪所关,何敢徇隐不言?……”
赵申乔的弹劾,是依据了一本文集《南山集》。这《南山集》,并不象赵申乔所说是戴名世自己私刻的,而是他的弟子尤云~把他抄录的戴名世所写的百余篇古文刊刻行世,因为戴名世居住在南山冈,所以将此书命名为《南山集偶抄》,也就是著名的《南山集》。而赵申乔所说的“臣与名世,素无嫌怨”一语,也很有些问题。
戴是在康熙四十八年以会试第一名、殿试一甲第二名进士及第(俗称榜眼),授的翰林院编修,而殿试上的状元赵熊诏就是赵申乔之子。因为戴名世在士林中素享盛名,赵熊诏却是才名不显,所以有不少人传言他是因为贿赂才成为状元的,赵申乔此次弹劾,也有人传是他要先发制人,罗织罪名置戴名世于死地,以断他人追究之想、塞他人议论之口云云。
至于说这个赵申乔到底是是这个心思。四阿哥和十三阿哥在谈论之时并不能肯定。也不想去追究。因为这个时候。起因已经不是主要地了。现在四阿哥与十三阿哥担心地是。此事牵涉过众。已经株连到数百人之多。震动了儒林。政界和学术界地知名人士如桐城派开山鼻祖方苞、韩尚书、侍郎赵士麟、淮**王英谟、庶吉士汪汾等三十二人俱都被牵连其中了。
康之所以会龙颜大怒。是因为《南山集》地《与余生书》一篇中。直接写出了南明政权弘光、隆武、永历三壬年号。且信中又将南明小王朝与三国时期偏居川中地蜀汉、南宋末年退守崖州地宋帝相提并论。
其实这《与余生书》。就是戴名世写给他地一个门人余湛地一封信。余湛曾偶然同僧人犁支交谈。说及南明桂王之事(南明桂王朱由榔。就是后世所称地永历皇帝)。这才知道犁支原来是南明桂王宫中地太监。在桂王被吴三桂所杀后。他削发为僧。皈依了佛教。也就是说。犁支是亲自(炫)经(书)历(网)过南明朝之人。他所述地事情应当是比较可靠地。戴名世得知这个消息后。忙赶过去。可惜犁支已经离去了。
戴名世之所以对这件事这么上心。是因为他很以自己在史学方面地才能而自负。因为明史资料散逸颇多。有些又失于记载尚无人能写明史。所以他就想仿效《史记》地形式。写出一本明史。并因此广游燕赵、齐鲁、河洛并江苏、浙江、福建等地访问故老证野史。搜求明代逸事。不遗余力。这次没能和犁支见面。让他很是遗憾。于是就嘱咐余湛把所听到地情况写给他名世把余湛写地东西与方孝标所著地《黔纪闻》加以对照。考其异同发现了一些可之处。
于是就写信给余湛。询问犁支下落。欲与其“面谈共事”。这封信就是《与余生书》了。
戴名世既然问地是明史中事儿。信中提到南
号也就不应该是什么大事了,本来是不至于让康熙的只是这个案子发的时候不好,现在明清之际的一批遗民如顾炎武、黄宗羲、冒辟疆等人虽然已经故去了他们提倡“反清复明”、讲究“夷夏之别”的影响却还很广,他们的弟子也是布于天下熙这次陪同太后避暑,居然也受到了这些人士的一点小小骚扰虽没造成什么影响,毕竟也是扫了康熙的兴。
赵申乔选在这个时机弹劾戴名世,也可谓是用心良苦,体察圣意了,既报了私仇,也得了圣心,真是一举两得。而康熙借着此案大做文章,是想起到敲山震虎、杀一儆百、巩固政权的作用,于是《南山集》案就由单纯的年号、明史的事儿被渲染成了旨在谋反的叛逆之举。
四阿哥和十三阿哥虽然也认为戴名世做事行文很有些不检点,但却爱惜其才,觉得他虽有错,但错不至此,且他在士林之中很有一些影响,如果轻率处置,怕会引起读书人的不满,只是康熙态度坚决,连大学士李光地亲自出面“欲疏救于万死一生之地”,也“卒不可得”,而他们做皇子的,更是不能轻举妄动,以免招了康熙的嫌忌,也只有在云锦这儿,发发感慨了。
“爷,如果这个戴名世真的被定了叛逆,会怎么样啊?”云锦在现代也是写书之人,对文字狱的受害者自然有份同情之心,这个案子自己在现代虽然听到过,但却不记得最后的处罚结果,不过“叛逆”的罪名,听起来就很严重。
“叛逆是那么好当的吗?抄家灭门都是有可能的。”十三阿哥皱着眉头说道。
“有那么惨?”云锦了拍胸口,“还好,听爷和十三爷刚才说,就现有证据来看,尚不够定叛逆的。”
“现在不是证据的问题,”十阿哥面色严肃的说道,“而是要给那些反清复明的人一个教训。”
“可是,”云锦心叹息,老康这是要杀鸡给猴看啊,只是这鸡招谁惹谁了,就这么被处置了,是何等的无辜,“这个戴名世并没有反清复明啊,爷和十三爷刚才不也说了,他只是想写本明史,无意中触犯了忌讳而已。”
“皇阿哥自有皇阿玛的量,”四阿哥摇摇头,“那些反清复明的人也是闹得有些不象话了,需要给他们点儿震慑了。”
“可也不能用这件事儿啊,以言论罪,怕是矫枉过正啊,”云锦想到雍正时期也是有文字狱的,虽然他处理的比康熙和乾隆都要轻,但能劝着点儿也是好的,所以她看着四阿哥说道,“如果读书人均不敢开口,不敢写文,怕也是与朝廷无益的。”
“也不至于这么严重,”四阿哥是没听进去,“不过是一个案子,哪里会有那么大的影响?”
“爷,可不是这么说,”云锦很严肃的说道,“今儿个是因为用了前明的年号而被治罪,明儿个就保不齐因为用了前明的诗句而受审,如此发展下去,备不住说个‘明’字就是错呢,那就不光是读书人不敢写文的问题了,可能连百姓都不敢开口说话了。”
“哪里就有这么严重了?”十三阿哥倒是先笑了起来,“云锦就是会危言耸听。”
“十三爷,要是任由事态发展下去,这都是保不齐的事儿。”云锦很认真的说道,“而且不光是‘明’字,怕是‘日月’也不能说,他们加一起就是‘明’啊,凡是有影射明朝之嫌的都不能说,最后就只好什么都不说了。”
“行了,不要随意瞎编排,”四阿哥瞪了云锦一眼,“皇阿玛不会让事态发展到那样的。”
“总是要防患于未然啊,”云锦还是不死心,“爷,就真没办法劝劝皇上了吗?如果罚得太狠,怕是会寒了天下读书人的心啊,那样岂不是对我朝更不利吗?”
“云锦虽然想得离谱了些,”十三阿哥看着四阿哥说道,“但总算也是为朝廷考虑,说的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其实我们不也是觉得这样办有些不妥吗?”
“现在你我如何想并不重要,关键是皇阿玛怎么想?”四阿哥平静的说道,“现在他老人家主意已定,这时候去劝,不只是劝的人遭殃,还会带累戴名世那些人被重判的。”
“如果会连累到爷,那还是算了,”云锦承认自己比较自私,如果在不连累自己的情况下,救人没问题,可是要把自己赔进去的话,那还是再说吧,现在自己也有儿子了,总不能让他父亲为了帮人而受到牵连吧,何况那个人跟自己还非亲非故的,“云锦只是觉得他一家人有些可怜而已,可是不管怎么说,爷的安危是最重要的,云锦早就说过了,要救人,得先保护好自己。”
“其实照我想,皇阿玛也许并不会太过重判,至少不会牵连太广,”四阿哥看了看云锦,语气放缓和了些,“也许开始会做出个重判的样子,给那些人不安分的人看看,但最后还是很有可能法外开恩的。”
“希望真的如爷所说。”云锦姑妄听之。
事实证明,四阿哥还真是对康熙有所了解的,这件事的走向也真的就是象他所分析的一般,先是轰轰烈烈的抓人审查,经过三个多月的合议,刑部判戴名世立即凌迟,方孝标所著《纪闻》内也有大逆等语,应其尸骸,二人之祖父子孙兄弟及伯叔父兄之子年十六以上者俱拟立斩,十五以下者及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给功臣家为奴。方氏族人拟发往乌喇、宁古塔。汪、方苞为戴名世书作序,俱应立斩。
而康熙对此判决却并没有马上表态,而是又拖了三个月,才让九卿议奏,着刑部等衙门再议此案,最后《南山集》案处理结果是:戴名世立斩,其家人从宽免治罪。方孝标之子方登峰等免死,并其妻子充黑龙江,受牵连的汪
:、方苞等免予治罪,入旗。
虽然戴名世终究还是难免一死,但以“叛逆”之名,判成这样,已经是从轻的多了,当然这是后话了,这个案子只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影响到元寿进宫的时间,后来就不是他所影响的了,而是因为江南那边又出了事儿。(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m,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
正文 第二百一十九章 秀才们的雅趣
南那边出的事儿可不象福建那边的农民起事那样,武力镇压的,因为这次闹事的都是秀才中的佼佼者,弄个不好是要动摇国本的。当然这些秀才们也不是为了戴名世那个《南山集》的事儿在闹,他的事儿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定论呢,而且戴名世虽然在士林中有很高的威望,但还不至于在江南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至少是不会闹得这么热闹。
江南这边发的是科场案。科场,按字面的意思就是指科举考试的场所,也可以引申为科举考试。说起中国的科举考试,那可是历史悠久了,它从隋炀帝时期就开始了,目的就是为朝廷从民间提拔人材,是读书人进官阶的主要途径,由于它是采用的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来说,科举考试无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就是今天的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算是科举制度的延续。
中国实行的科举制度,不仅让东亚的一些国家,例如日本、韩国、越南纷纷效仿,甚至在也得到了欧洲人士的推崇,经过传教士在游记中的介绍,在十八世纪时的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的思想家就很推崇中国这种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国在十九世纪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务员叙用方法,规定政府文官通过定期的公开考试招取,渐渐形成后来为欧美各国彷效的文官制度,其考试原则与方式就与中国科举十分相似在很大程度是吸纳了科举的优点,故此也有人说,科举是中国文明的第五大发明。
现在清朝的科举考试共分为两大阶段,先是初步考试,这个阶段分为童试、岁试、科试三级。
“童试”,一般又叫做“小考”,凡初应试者不分年龄大小都称“童生”,童生在县里面选拔了以后到督学进行考试,督学考试合格就可以称做“秀才”了,因为秀才是一年考一次以叫做“岁试”之后就是每三年一次大的“科试”,主要是为了推举举人考试的资格,通过这个考试的提名,便有资格科举的正式考试了。
科举的正式考,也是分为三级别是乡试、会试、殿试。“乡试”通常每三年在各省的省城和京城举行一次,又称为“大比”子午卯酉年为正科,遇皇家有喜庆之事加科称为恩科,由于它是在秋季举行,所以也叫做“秋+》”。只有通过本省学政巡回举行的科试,成绩优良的才能选送参加乡试,乡试考中后就是“举人”了第一名称为“解元”,第二名至第十名是“亚元”。而“会试”则是在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天在礼部举行以会试又被称为“礼闱”,也叫“春闱”参加会试的是举人,取中之后就是“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殿试”当然就是皇帝主试的考试,参加殿试的是贡士,取中后统称为“进士”。
殿是分三甲录取的,第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第一甲中的前三名,就是俗称的“状元”、“榜眼”、“探花”,合称为三鼎甲,第二甲的第一名俗称“传胪”。一般来说,状元会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则授儒林院编修。其余的诸进士还要再参加朝考,选擅长文学书法的为庶吉士,其余的分别授主事(各部职员)、知县等(实际上要获得官职,还须经过候选、候补,终身不得官也是有的)。庶吉士在翰林院内特设的教习馆(亦名庶常馆)肄业三年期满举行“散馆”考试,成绩优良的授以翰林院编修、翰林院检讨(第二甲的授翰林院编修、第三甲的授翰林院检讨),其余的也会分发到各部任主事,或分发到各省任知县。
因为乡试考了以后就是举人了,而举人实际上也是候补官员,按清朝的科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