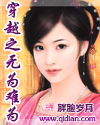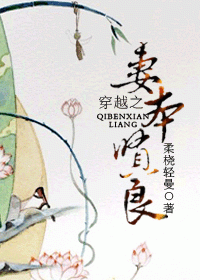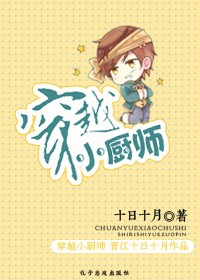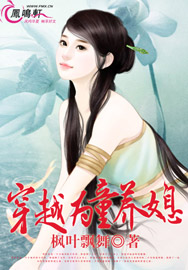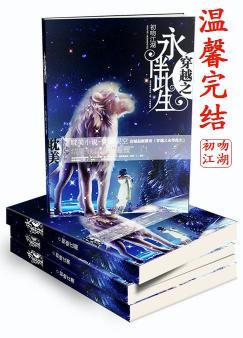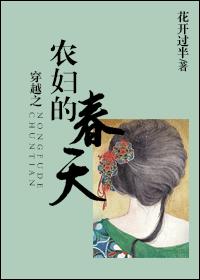穿越之范家娘子-第7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会过礼部,虽避过了朝堂公义,却又不是在朝堂上郑重宣布的。
一阵小小的议论之后,这件事就这样定了下来。
其实,会有议论这件事本身,就出乎了李静的预料。再怎么说,这也是个君主□的时代,皇帝都写成圣旨公布的事,居然还有朝臣敢提出质疑议论。不得不说,赵家虽然得天下的方式不地道,赵匡义又是夺了自己侄子的皇位,但是,赵家人皇帝当得,倒真是仁厚能容。
端午节的宴饮,自然还是文会。就连皇帝后妃,都有节目。
李静倒是没有关注节目自身,反正不管是文章还是歌舞,她都没有太大的兴致。除非文章是枪手写得,歌舞有貂蝉、赵飞燕的神韵。
不过,有一点,李静倒是颇为震惊。
都说皇帝后宫佳丽三千,可是,眼前这位皇帝的后宫,却只有皇后一名,婕妤一名,才人一名,美人一名。子嗣更是单薄,只有一位年仅五岁的皇子,和一位尚在襁褓中的公主。
不过,四位后妃,却是跨过了二十、三十、四十三个年龄段。
刘禅悄悄告诉李静,那位沈美人,是在郭皇后病逝第二年入宫的,入宫时,年仅十四岁。
李静远远看着那位播弄琴弦弹奏高山流水的美貌与气质并存的美人,再看看与刘皇后坐在一起胡子一把,眼袋下垂的皇帝,面纱之下,嘴角不以为然的一撇,暗自叹道“果然天下乌鸦一般黑”。
刘皇后苦守了三十年,皇帝却还要在郭皇后去世的隔年纳一位豆蔻年华的青葱少女入宫。
看向坐在皇帝身边笑得雍容的刘皇后时,李静眼中,又多了一份怜惜。
虽然,她自己也知道,以刘皇后的身份地位,以及她作为这个时代女子的价值观,知道李静怜惜她,多半会觉得她可笑。而且,比起刘皇后来,那位沈美人还更加可怜一些,老夫少妻就罢了,还是做小。
可是,李静心中的天平,早就因为她身上的这件据说出自刘皇后之手的衣服,而脱离了她的理智,完全一面的倾向了刘皇后。
沈美人之后,那位地位最低的李才人,诵了一首她做的小令,不是特别出彩,倒也应景和韵。
按说李才人才是皇帝宫中最可怜的人,皇子是她生的,却过继到了皇后名下,担任教养之职的,却是与她年龄相近的杨婕妤。
可是,李静看着她,却起不了的同情之心。或许真的是先入为主了,她把那个娇颜中难掩愁苦的李才人,看作了不守本分,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
当然,这件事的罪魁祸首,还是那个坐在上位的皇帝。明明已经有妃子了,怎么还能吃自己苦恋了二十几年的恋人身边的侍女呢。
这件事,做得太缺德、太不地道了。
不过,想到刘皇后最终却是因为那个皇子才登上了后位,李静又觉得,皇帝和刘皇后之间,倒是一个不怨一个。
刘皇后有容乃大,皇帝虽则管不住下半身,却并未因为宠幸新人,而忘却旧人。
只是,眼睁睁的看着皇帝这“一家”坐在一起,李静心中,对于刘皇后和皇帝三十多年的感情,却不再觉得可贵、羡艳。
这份感情,与李静心中“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爱情,相去甚远。
在李静胡思乱想之际,刘皇后的侍女绿萝抱着苏畅为李静重金买来的那一把与焦尾同样质地的出自名匠之手的古琴出场。
起先,李静本也是想弹奏一首技艺高绝的古琴曲的,可是,沈美人高山流水都弹奏出来了,李静要是再炫耀琴艺,把沈美人比下去了,是她对后妃不敬,比不过沈美人,有辱了她师傅解容子第一琴师的声名。
好在,端午节的文会,本就不是特别正式的宴会,或者说,中国人宴会上的献技,最重要的,从来不是技艺本身。
李静微微权衡,弹唱起了她初入京城时,听薛艳姑娘弹过的晏殊的那首《浣溪沙》。
弹奏《浣溪沙》
李静一曲奏毕,宴厅中出现了短暂的诡异的沉默,随后,是刻意压低声音的窃窃私语。
李静刚刚演奏的晏殊的《浣溪沙》,是文学史上评价很高的流传千古的文采很高的词曲没错。
但是,在那之前,在这个时代,它首先是汴京城中群芳阁花魁名妓薛艳演唱了一个多月的成名曲。
众所周知,薛艳以前就以琴艺名动京城,而那首《浣溪沙》,更是让她击败了群芳阁的花魁娘子,一举成为群芳阁,不,是一时之间汴京城中风头无两的新花魁。
而那首最先由她公开演唱的《浣溪沙》,有意无意间,也就成了她的每位裙下之臣必点的保留曲目。不管是真懂得欣赏词曲意境的客人,还是半懂不懂附庸风雅的客人,还是那些完全不懂得欣赏的纨绔子弟,每个出得起缠头的人,都会点这首《浣溪沙》。
不夸张地说,这段时间京城最紫红的歌伎,薛艳称第二,无人敢称第一。
薛艳这样的风头无两,几乎已经到了妇孺皆知的程度,她夜夜演奏的这首《浣溪沙》,自然也是整个京城,男女老幼,耳熟能详。
与这首词曲的名动京城相对的,却是它被打上的瓦肆勾栏的烙印。
尽管这首词是昔日的“神童”,如今皇上跟前正红的太常晏同叔所作。可是,这一事实本身,并没有抬高这首词曲的身价。
当然,也没有对晏殊的声名产生什么影响。毕竟,作曲填词,从来都不过是一个“玩意儿”,正统士大夫看重的,还是文章诗赋。
而饮酒狎妓,在这个时代,也是文人之间,附庸风雅的稀松平常之事。偶尔为交好的歌伎随手写一篇词曲,别说晏殊的只是伤春之词,哪怕他夜永酒阑之际,写下闺房之乐的艳词,被人知晓,也不过是知晓的人私下之间的笑谈,和交好的友人的促狭而已。
既不会太影响晏殊的声名,更不会影响他的仕途,这个时代,还没有“公务员的作风问题”。
但是,这首词既已被贴上了名伎薛艳的标签,就不能再登上大雅之堂,李静这种新近册封的郡主,作为大家闺秀,别说弹唱,不合于礼的东西,听了,都有失身份教养。
她这样公然弹奏这一曲,不仅是坏了她自己的声名,更是两个耳光左右开弓扇在了皇帝和皇后身上,尤其是皇后,虽然也是出身官宦之家,但是,父亲早逝,早年为了生计,她还在勾栏瓦肆演唱过大鼓词。
这段过往,一直让她为朝中的众臣所病诟,而她登上后位之后,也千方百计的通过封赏已去世的父亲、祖父、甚至曾祖父这些已逝之人,来抬高自己的身价。
今日宴会之上,她的节目,也是一篇可圈可点的纪念屈原的文赋。
而李静,虽说是皇上册封的,她的座位与皇后最宠爱的侄子刘禅安排在一起,不管是因为两个人的身份都格格不入还是其他,这都昭示了一点,她是皇后的人,在皇后的庇护之下,他日,即便她不能与刘禅成亲,她所嫁夫婿,若能有所建树,那也是得了皇后的提携。
可是,李静这般上不了台面,受辱的,不仅仅是她自己,还有废了一番心思为她亲手缝制公服的皇后。
李静的这一行为,简直是在明晃晃的告诉众人,皇后自己出身低微,品味、看人的眼光也同样的差。
她宠溺不成器的刘禅,还可以当做是长辈对自家幼侄的亲近,为一直无嗣的她树立了一个仁爱的形象;那么,她抬举李静,就不得不让众臣怀疑,她的识人之明。就算仅仅是对刘禅的爱屋及乌,也有包庇近亲的昏聩嫌疑。
这无疑让才在后位上坐了不满两年,仍未被大半朝臣所认可的她,给了众臣一个攻讦的借口。
甚至于,有心人还能想到更多。吴王是怎么死的,虽然这件事已经过去了近四十年,当年知息那件事的朝臣,或告老归天,或已与先皇一般故去。
可是,毕竟吴王本身活着的时候就很出名,他带过来的朝廷,当初先皇为了显示仁厚,在吴王去世后,也都各自安排了官职。那件事足够轰动,本身也很有话题性,虽然是明面上的禁忌,私下却流传了下来。
吴王因为一首词获罪,如今,得蒙皇帝看得起封赏为郡主的李静,又在被封赏的场合弹奏一时之间名动京城的词曲,是真的纨绔无知,还是婉转的在表达对先祖获罪赐死的怨念?
后来,还是司礼监反应过来,报了接下来的节目单,只是,之后的节目表演,无论多么精彩,晚宴的气氛都没有炒上去。
最后,宴会在一种低沉、诡异的氛围中草草结束。
对李静那一曲激起的千层浪毫无所觉的李静,跟众人一起行礼过后,就拉着刘禅的手腕(不这样的话,她会因为穿不习惯的公服走路不稳而跌倒)离开了皇宫。
至于她身周各怀心思的百官,以及身后因她那一曲被推到尴尬境地的皇帝和皇后,李静完全没有需要请罪道歉的自觉。
刘禅也感觉到了宴会的气氛诡异,可是,本来就因为不学无术而被人嘲笑惯了的他,并没有太把这种诡异放在心上。倒是为李静的用心表演为众人所不齿而气愤,更加不会想到拉着李静一起到皇帝和皇后面前请罪。
两人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牵手(不是牵手,只是抓着手腕而已)偕行离开皇宫,更加给了有心人弹劾的话柄。
第二日,因为折腾了一天太累,尚在床上深眠的李静,却在朝堂上,收到了雪片般纷飞的弹劾。
那么多的奏章,主旨自然是弹劾李静有失大体,辱没圣听,不堪郡主身份。只是,根据个人利益的不同,这个主旨被引申到了各个方向。不得不说,古代文人的想象力和无中生有以及巧舌如簧,绝对达到了相当的境界。
只不过是一首无伤大雅的词曲,都能让他们做出那么多的文章。
前夜,众臣离去后,皇帝和皇后两人几乎彻夜未眠,商量着如何应对两人,尤其是皇后的“失察之责”。
李静的琴艺,刘禅提过,他们也调查过。别说高山流水,就是那难度高绝的广陵散,李静弹起来,也丝毫不费力。
刘皇后让李静自选琴曲,一来为了表示她对李静的亲近宽和,二来,她觉得,李静再怎么纨绔,毕竟身为一女子,且是大家贵族出身,像昨日那种场合,最起码的规矩,她该是懂得的。
她之前给李静讲规矩时,李静也是一副明了受教的表情。刘皇后看来,李静虽然单纯,却并不是不懂事。
只是,她万万没有想到,一向与她不亲近的沈美人的节目,居然也是弹奏琴曲。本来,虽然各人要表演的节目,都是直接派人告诉司礼监,但为了不与人撞车,也会买通司礼监知晓其他人的节目单的。
可是,刘娥近两年贵为皇后,只有别人避她锋芒的份儿,哪有她刻意规避讨好别人的礼。
况且,端午节的文会,在宫中一年到头大大小小的宴庆中,虽说不上最不重要的,却也着实不是什么重要的。
而刘娥之前一直忙着为李静缝制公服,也就一时失察了。
刘娥毫不怀疑,李静演奏那一首琴曲,是为了另辟蹊径,不与沈美人争锋。
这是她的体贴,只是,用心虽好,后果,却很糟糕。
而李静面纱遮面,本是为了显示她的尊贵,她唱出那一曲《浣溪沙》,反而让她的面纱遮面显得轻佻、诱惑。尤其是,适合了刘娥审美的重色公服,她的面纱,不是白色,而是艳丽的红色。
单纯论琴艺来说,李静自然高出薛艳许多,只是,她的嗓音,却不如薛艳的训练有素,但是,更添了一丝别样的稚嫩、干净。
加上水榭下面是真正涌动的河流,而不是人工的流水。因此,李静弹唱的效果,其实,是比薛艳好出许多的。
或者说,剥离了勾栏瓦肆之地那种卖笑逢迎的场所,单纯就技艺以及词曲意境来说,无疑,李静的演奏,更能表达《浣溪沙》的意境。
刘皇后与皇帝,商量一夜得出来的结论是,无视那些弹劾,直接就词曲本身,让它的作者晏同叔评价李静的琴艺表演。
是讨巧的做法,也有些祸水东移的不地道。
不过,说到底,引出这件事的人,还真是晏殊。如果不是他一时兴起请李静留宿晏府,如果不是他家的丫鬟大惊小怪传出那样的流言,也不会給皇帝召见李静的借口。如果不是他饮酒狎妓,卖弄文采,让那首《浣溪沙》贴上了勾栏瓦肆的标签,李静在昨日文会上,弹唱《浣溪沙》的行为本身,也不会招来那么多额外的非议。把所有矛头指向他,也算是责任到人了。
昨夜,乍见李静之时,晏殊跟其他人一样,是震惊的。不过,他的震惊,比在座的众人更胜,毕竟,当日与他饮酒听曲的,是男装的李静。晏殊下意识里,虽然也曾把李静幻想做姑娘过,不过,也只是瞬间,他就否定了自己的想法。
世家大族的闺中小姐,再怎么大胆,也不会不知分寸到女扮男装出入风月场所。
可是,先前的惊鸿一瞥,确实与他一个多月前见到的李静有七分相像,更主要的,那一朵未被面纱遮住的明艳绽放的独特的红莲印记,晏殊并不认为,随便什么人脸上都会长。
之所以用“长”,而不用“画”,是因为唐朝覆灭百年,如今早就不再流行效仿杨贵妃额间贴花的妆容了。更主要的,他初见的李静,是做男装打扮的。一个男子,再怎么爱美,也不会在额间画上一朵红莲印记。太妖娆、太女气了。
如果先前的震惊只是怀疑,后来,李静弹唱那一首《浣溪沙》,却是坐实了晏殊的怀疑。虽说如今《浣溪沙》是名动京城的名曲,可是,起初,却并没有多少人知晓。
甚至于,那虽然也不能说不是晏殊的得意之作,他却并没有想过让歌伎演唱。因为,被唱得滥了,三教九流都知晓了,会失了词曲的意境。
那是他的一时情绪之作,是他看着妻子阑珊独处时的有感而发,虽然风流,但是,晏殊对自己的妻子,还是放在心上的。
本来,他还想着再过几日,至月末妻子生辰时,亲自作上一幅画像,把词填好,裱糊成卷轴,送给妻子作生辰礼物呢。
可是,在那之前,薛艳却擅自把他的词曲演唱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