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批判现实社会的黑暗与腐朽,反对愚昧的乐观主义,那么《老实人》则是用风趣十足的讽刺文学来揭露社会生活的种种丑恶,一层一层地戳穿“先天和谐论”的画皮。
《老实人》中,伏尔泰精心安排了一个老实人在威尼斯巧遇六位失去王位的国王的情节:这些曾经嚣张煊赫一时的国王们,在威尼斯度狂欢节时,竟然现出了付不起饭钱的穷酸相。敏锐的伏尔泰已经从封建专制势力的疯狂猖獗中,预感到它穷途末日的来临。30年后的1789年,一场荡涤封建残渣余孽的革命风暴,终于如火如荼地爆发了。
伏尔泰在《老实人》中,不仅揭露了专制制度和封建教会的腐朽与黑暗,而且也为人们展示了一幅理想社会的美好蓝图。老实人无意之中来到了黄金国,在这一自由的国度里,人们安居乐业,丰衣足食,既无迫害,又无牢狱;有高耸入云的现代化建筑,有摆满数学和物理仪器的科学馆。国王英明有为,民众虔诚和睦。显然这一理想中的黄金国,只不过是伏尔泰乌托邦式的社会和政治理想的图解,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国。然而,它作为封建专制社会的对照物却也显得赏心悦目。伏尔泰正是希望通过黄金国的理想生活图景,来激励人们解放思想,崇尚科学,追求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远大理想。
《老实人》是伏尔泰哲理小说的代表作,它以朴素的题材,鲜明的形象,生动地概括了17、18世纪欧洲各种哲学派别的论争,并把这种争论从谈玄说理的神秘迷雾中解放出来,使之面向现实社会,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和浓厚的哲学含义。它所描写的荒唐可笑、奇异怪诞、幽默有趣的故事表明,伏尔泰作为古典主义的文学大师,也开始娴熟地运用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和技巧。
第八章 费尔内的抗争
1。 消灭败类
几十年来,伏尔泰一直坚持不懈地与宗教迷信、狂热、褊狭或不宽容作斗争,宣传启蒙思想,但是他明目张胆地公开抨击教会势力的时候毕竟很少,他比较讲究斗争的策略,一般情况下都是通过间接的、隐秘的手段与他们作斗争的。
1758年10月,《瑞士报》登出一篇匿名文章,这篇文章宣称伏尔泰即使不是无神论者,也是被自然神的兴趣冲昏了头脑的疯子。对这一无耻的攻击,伏尔泰给予了坚决的回击,同年12月,他也在《瑞士报》发表署名文章《斥一篇匿名文章》,公开地向宗教势力发出了挑战。这时的伏尔泰之所以能够勇敢地站出来,直截了当地抨击宗教的罪恶,首先是由于法国和瑞士当局勾结教会势力,恶毒攻击《百科全书》和他的一些著作,使他怒不可遏。其次或者说更主要的是由于他在瑞士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独立和自由,他对自己的力量产生了信心。以前,他一直是在社会地位显赫的人的庇护下侥幸求安:年轻时,他仰仗贵族中的熟人和朋友;在英国,他得到权倾朝野的社会名流的支持;在西雷古堡,夏特莱侯爵夫人、里舍利厄公爵和法国王后的父亲波兰前国王斯坦尼斯瓦夫二世等人经常保护他;在普鲁士,他又得到普王弗里德*y希的荫庇。现在,他在日内瓦、在洛桑、在费尔内或图尔内,都有比较自由、宽松的环境。同时,他已是众望所归的欧洲知识界的元老,海内外慕名而来的造访者不计其数,即使是日内瓦的政府首脑或各地权贵也常常成为他的座上客,他已不必像以前当朝臣时那样诚惶诚恐、阿谀逢迎,用自己的人格去换取一时安乐。现在他可以为自己的利益与权利同别人抗衡,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见,因为他已无坐牢或死亡的危险。
伏尔泰在费尔内时期发现了一个新的敌人的名字,或者说他给自己的敌人取了一个新名字:败类。“消灭败类”成为了他这一时期工作的主要内容,他在致哲人党朋友的信中都要署上他们的战斗口号:“消灭败类”(écraserl’infame)。有时干脆缩写成“Ecr。linf”,以致有一位拆看他们信件的检查官以为这些信的作者是Ecrlinf先生。
1759年,伏尔泰完成了民族历史题材的悲剧《唐克莱德》和悲剧《苏格拉底》。《唐克莱德》1760年秋在法兰西喜剧院上演,由克莱龙小姐和勒坎主演,获得成功。
《苏格拉底》是伏尔泰“消灭败类”战斗中射出的一发重磅炸弹。剧本按照自然神论的观点,把这位希腊著名哲学家描绘成了一位宗教宽容斗争中的殉难者。伏尔泰自信他的这部悲剧会使宗教狂热者发抖。他在剧本中赞扬了苏格拉底的宗教观念,坚信它是以道德,而不是以形而上学为基础的。苏格拉底在崇拜神性,给人类以帮助、培养友谊和学习哲学时,自以为已经履行了责任,所以遭到当时的僧侣诅咒。这一剧本还公开讽刺了百科全书派的死敌、耶稣会机关报《特雷沃报》的主编贝蒂埃神甫。
1759年11月,贝蒂埃神甫在报上发表文章攻击《咏自然法则》和《百科全书》,伏尔泰立即写了一篇尖酸刻薄的反驳文章《耶稣会士贝蒂埃患病、忏悔、死亡和显灵的记录》。他在文中写道,贝蒂埃由于在报纸上发表了太多的恶毒言论而中毒,还染上了瞌睡病,不停地打呵欠。为了医治这一怪病,医生建议他吞下一页《百科全书》,但病情只能稍稍缓解。贝蒂埃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令人讨厌的,最后,他在平静中死去了。死后,他又奇迹般地显灵,他告诉噶拉斯神甫的侄子,他在被认为是谦卑和温和的人之前,一直处于地狱之内,噶拉斯神甫的侄子后来告诉《特雷沃报》的编辑同仁,他从贝蒂埃的显灵认识到,骄傲是最致命的罪恶,是耶稣会士最害怕的东西。伏尔泰在这里把他痛恨的贝蒂埃神甫及其耶稣会士狠狠地戏弄了一番。
报刊专栏撰稿人佛勒龙也是反对狄德罗和伏尔泰的重要干将之一。1754年,年方35岁的佛勒龙就当上了里热、蒙多邦、南锡学院院士。他长着鹰钩鼻,有一张渴望肉欲的嘴和一双机灵而不明亮的眼睛,一副学究派头。他贪图享乐,生活奢靡,早年因冒犯当局蹲过文森监狱和巴士底狱,曾在圣路易中学教过书。1754年8月,他在《文学年鉴》上辛辣地讽刺伏尔泰,1755年又抓住达兰贝尔在《百科全书》第5卷卷首撰写的纪念孟德斯鸠逝世一周年的文章,攻击作者,指责整个《百科全书》。1756年,又在《文学年鉴》上大肆攻击狄德罗的《私生子》。1760年,他又胡说什么伏尔泰的作品没有普遍性,嘲笑这些作品只能在法国昙花一现。
伏尔泰对佛勒龙的恣意妄为早已恨之入骨,1760年7月,他把刚刚完成的喜剧《苏格兰女人》交给巴黎喜剧院公演。这是一部挖苦讽刺佛勒龙的喜剧,伏尔泰希望借此出出心里憋了很久的怒气。在剧中,佛勒龙被刻画成一个热衷于诽谤而生活的人,他居然宁肯作假证也不放过一个使他反感的无辜女孩。他自诩“是一个杰出的编辑”,无耻地宣称“我称赞低能者,我蔑视真正的天才”。佛勒龙厚着脸皮出席了该剧公演之后,马上动笔反击。他发表了一封臭名昭著的公开信,对伏尔泰进行恶毒攻击和责难。伏尔泰也激动起情绪来,不肯善罢甘休,第二年初,他发表了《佛勒龙轶事》,对他展开人身攻击,指责他把侄女当情妇,使她两次怀孕,并在第二次怀孕时把她匆匆嫁给了别人。
1759年9月,法兰西学院任命小诗人蓬皮尼昂接替莫伯都依的职位。1760年5月10日,当他出席就职仪式发表演说时,突然恣意攻击哲人党,指责法兰西学院对一些危险学说的宽容。他首先就对伏尔泰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伏尔泰进入法兰西学院时的就职演说是以种种伟大的大拼盘拼凑出的最平庸、最无味的演说词。接着他肉麻地吹捧莫伯都依、黎世留、路易十四都是伟人。他演说的其余部分都是对当代哲学家和文学家的咒骂。
蓬皮尼昂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说中大放厥词,引起了伏尔泰的愤怒,他立即以克洛多雷的笔名,发表了一篇题为《何时》的文章,嘲笑蓬皮尼昂的放肆和无知。随后,百科全书派的莫尔莱神甫也写了《如果》和《为何》进行驳斥。伏尔泰意犹未尽,又以德利斯的笔名续写了《是》和《否》。这些文章像一连串的炮弹,对启蒙哲学的政敌进行猛烈轰击,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小品词大战”。蓬皮尼昂恼羞成怒,便写了一篇《陈情书》呈交国王,希望得到至高无上的国王的同情和支持,结果也未能如愿以偿。
启蒙思想家们还有一名危险的敌人帕利索。他像佛勒龙一样,对百科全书派咄咄逼人之势甚为不满,曾抛出一篇题为《论大哲学家的几封小信》的文章,责备哲人党夸张偏执,互相捧场,对敌手妄加中伤。还对狄德罗的《私生子》大加讽刺。1760年5月,帕利索精心炮制的一出喜剧《哲人党》在法兰西喜剧院上演,这一闹剧把哲人党的理想描绘成了有害公共秩序和社会道德的东西。它的上演虽然遭到法兰西喜剧院著名演员克莱龙小姐等的抵制,但是得到王室的认可,帕利索的保护人罗贝克公主在公演时亲临剧场以示支持,王储也表示欣赏。教会人士更加拍手称快。由于它具有一定的煽动和欺骗性,当时颇受到一部分人的欢迎,因而对哲人党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一时间,它成为巴黎上流社会茶余饭后谈论的焦点。客观地讲,这部喜剧如从艺术的角度加以评价并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剧情安排和人物性格刻画都很一般,舞台上也没有什么创新之举,它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其对启蒙思想家进行了别出心裁的人身攻击。剧中的克里斯潘被描绘成四只脚走路的人,这显然是代表崇尚原始主义的卢梭;罗狄德明显是狄德罗的代名词,他被刻画成为无耻的骗子,经常利用自己关于人性的丰富知识,来骗取天真无知的妇女,他还在七年战争中表现出不热爱祖国的情绪。《哲人党》还影射了杜克洛、爱尔维修、格里姆等一大批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帕利索为伏尔泰的崇高威望所迫,不敢在剧中对其妄加攻击,达兰贝尔大概是因为退出了《百科全书》的编辑队伍,也得到了帕利索的“饶恕”。
帕利索侮辱哲人党,损害启蒙思想家的恶劣行径,激起了百科全书派的极大愤怒。狄德罗开始撰写《拉摩的侄儿》,他搜集了帕利索的种种卑劣言行,在书中对其进行了有力的还击。一向温文尔雅的百科全书派重要成员莫尔莱神甫也一反常态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他出版了《作为喜剧〈哲人党〉前言——夏尔·帕利索之幻想》一书,严厉谴责帕利索,甚至还直接指责其宫廷的庇护人罗贝克公主,并暗示她末日将要来临。国王当然不能容忍这种冒犯行为,莫尔莱神甫不可避免地被关进了巴士底狱。
帕利索一直非常尊重伏尔泰,他在《哲人党》序言中宣称,他和伏尔泰关系很和睦,他把剧本寄给伏尔泰并声明,他攻击的只是哲学中的弊端,而不是像伏尔泰这样真正的哲人。伏尔泰虽然对这位坦率的学生抱有好感,但是他把启蒙事业看成是自己的神圣事业,把对这项事业的责任和对同志的义务放在个人感情和礼节之上,坚定地反对帕利索对哲人党的挑衅行为。在给朋友和支持者写信时,伏尔泰表示,他坚决反对帕利索在舞台上嘲笑哲人党,他认为全体巴黎人民应该明辨是非、分清敌我,团结起来反对帕利索可耻地歪曲哲人党的理想。在与帕利索的通信中,伏尔泰也毫不隐瞒自己与《百科全书》的密切关系,承认自己为它写了12个条目,认为这一杰作是教育人民和维护国家荣誉所不可缺少的,他拒绝帕利索对百科全书派及其自由思想的一切批评。
伏尔泰、狄德罗、达兰贝尔、卢梭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运动的代表人物,但是由于他们的思想基础、政治见解和斗争策略上存在差异,因而难以形成稳固的统一战线。卢梭第一个走上了分裂的道路。伏尔泰在《哲人党》的问题上,对帕利索只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批评态度,远远没有达到狄德罗和达兰贝尔所希望达到的激烈程度,这又引起了他们之间新的一轮争吵。伏尔泰抱怨哲人党们对帕利索的攻击持观望态度,没有积极反击。达兰贝尔则反驳伏尔泰作为哲人党的众望所归的领袖,没有很好地保护和引导哲人党,为受辱的同志雪耻。伏尔泰此时虽已无所畏惧,但是为了整个启蒙事业他还必宣考虑斗争的策略,他不愿意让人们把哲人党与“阴谋集团”等同起来。他认为掌握国家权力的那些人决定着国家的前途,因此必宣注意培养与他们的友谊,不论是外国君主、本国君主,还是王公大臣,如果他们能接受哲人党的主张,就可以实现启蒙运动的理想,建立开明政权,消灭败类。达兰贝尔和哲人党其他代表人物则认为王公贵族是敌视启蒙事业的,他们不可能接受哲人党的主张,因而不能信任和依靠他们。达兰贝尔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提高哲人党的声望和荣誉,从气势和影响上压倒对立派,然后保持相对的独立性,通过自身的影响左右舆论,实现社会变革。
尽管伏尔泰与达兰贝尔等哲人党的代表在斗争策略上存在分歧,但是在具体斗争的方式上,他却是非常激进的。他在反对专制斗争中一直冲锋在前,不心慈手软。按照达兰贝尔的解释是因为伏尔泰有独立而殷实的财富,有极高的声望,又远离专制统治的中心,因而无所顾忌。而达兰贝尔他们没有这些条件,他们只能采取相对委婉的、间接的、尽量不针锋相对的斗争方式,来逐步实现启蒙思想运动的理想。伏尔泰感到达兰贝尔在“消灭败类”的斗争中有些踌躇,便热情地鼓励他:“勇敢而有力地讲出心中的话吧。打击后把你的手藏好。我完全相信他们是机敏的,有良好的嗅觉,会认出你的手,但是他们不能判你有罪,你将和好伙伴一起摧毁空谈家的帝国。一句话,我把败类交给你。①”他在另一封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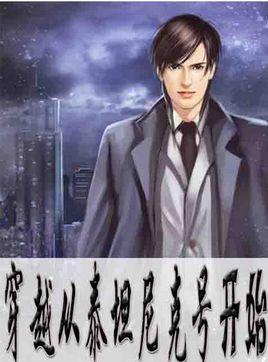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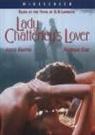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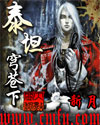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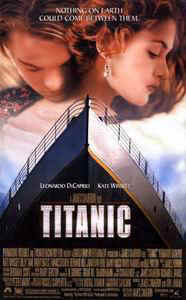
![[泰坦尼克]真爱永恒封面](http://www.8btxt.com/cover/15/15993.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