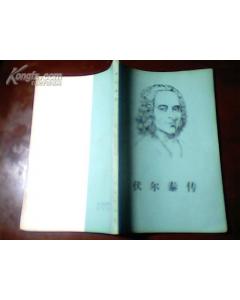伏尔泰传-第1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文章,并在征文中获奖。卢梭认为,文明的发展并不能促进人类和社会的进步。他以中国为例,证明他的“文明否定论”, 中国古代科学和艺术都很发达,文明很进步,但文明进步并不能纠正中国人的恶习,也不能使中国免遭异邦的侵略和征服。在中国,文艺是受人尊崇的,如果科学和艺术能够淳化风俗的话,文明的进步就应该能鼓舞中国人的勇气和斗志,中国人民就应该是聪明、自由而不可征服的。可是事实是,中国众多的文人学士并未给中国的进步与发达带来什么帮助,中国仍旧遭受异族的统治。
伏尔泰收到卢梭寄来的第二本书后,给卢梭回了一封信,信中没有提及对卢梭这本著作的看法,而是和卢梭讨论了他的第一本书的内容,指出反对卢梭文中所谓的文明否定论及原始主义,并且说不愿意像动物那样用四条腿走路。他还说,大的罪恶都是著名的无知之徒犯下的。
卢梭收到信后立即给伏尔泰一封回信,信中提出,如果一个作家的作品不是为了反对政府的腐败,反对 恶行而写,那么他就没有必要去写了。如果他不曾读书或写字,也许会比现在生活幸福。他还写道 :“人类的一切罪恶都是来自错误而不是来自无知,一无所知对我们的伤害要少于自以为知。”
由于伏尔泰和卢梭有着完全不同的观点,而卢梭在文中以中国为例证明自己的文明否定论,因此伏尔泰对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产生了研究的兴趣,并且把中国的哲学和伦理道德作为启蒙运动的有力武器。他选择的着眼点是中国古代悲剧《赵氏孤儿大报仇》。
《赵氏孤儿大报仇》, 或称《赵氏孤儿》, 是中国元朝剧作家纪君祥作的杂剧,其取材于《史记赵世家》。大概内容是:春秋战国时期,晋国权臣屠岸贾残杀赵盾一家,并搜寻赵氏孤儿赵武,想要斩草除根。赵家门客程婴与公孙杵定计救出赵武,并由程婴将孤儿养大成人,最后报仇雪冤。
伏尔泰在一些书上看到译成法文的《赵氏孤儿》,觉得很受启发,决定以这部元剧为原本,写一部悲剧《中国孤儿》。 但中国元代杂剧的原剧情十分复杂,不易改写,并且缺乏恋爱情节,这样的悲剧在欧洲剧坛恐怕不会受欢迎。因此,伏尔泰对原剧大加删改,使之符合欧洲戏剧的审美观。改编后的悲剧《中国孤儿》的大致情节是: 成吉思汗率领鞑靼军队灭金之后,侵入中国,占领了中国黄河以北的地区。他回到北京,发现他所心爱的女人依达姆嫁给了一个高官盛悌。盛悌曾从入侵者手中救出王室最小的王子免遭侵略者的杀害。成吉思汗让依达姆作出选择,要么与丈夫离婚嫁给他,要么与丈夫及那孤儿一起被处死。依达姆和盛悌宁死不屈。最后成吉思汗被他们所感动,放了他们及那个孤儿。
伏尔泰的《中国孤儿》虽然是从中国戏剧改编而成,其实与中国原剧已有极大的不同。他把故事的背景从公元前五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往后推移到1700多年后的元朝,又把一个诸侯国家内部的文武不和的故事,改编为两个民族之间的文野之争。在艺术上,他按照“三一律”的戏剧法则,把剧情的时间从20多年缩短到一昼夜,删掉原剧中的弄权、作难、搜孤、除奸、报仇等情节,突出托孤、救孤两个情节,再加进去一个爱情故事,就布局成了一部标准的古典主义五幕悲剧《中国孤儿》。
伏尔泰一生中对戏剧的热爱都非常浓厚,并且创作过不少很成功的戏剧。 这次改编的《中国孤儿》,也如他所希望的那样,获得很大的成功。这种把中国的戏剧故事搬上法国舞台的作法,在伏尔泰之前的中法文化交流史上,还没有发生过。伏尔泰改编的成功,激发了不少英法等国家的戏剧艺术家们对中国戏剧的兴趣,随即,有更多的中国戏剧被引入欧洲,改编成欧洲式的戏剧。伏尔泰也因这次的改编的成功而获得更高的声誉。当时的《爱丁堡评论》曾写道 :“伏尔泰先生也许是法国最有名望、最有才华的作家……在他最近的悲剧《中国孤儿》里,他的创作天才尤为突出。我们读了这部作品,一方面觉得高兴,一方面又觉得奇怪,因为他把中国道德的严肃与鞑靼野蛮的粗犷一齐搬上了法国舞台,而同时与法国人最讲究的严谨细致的种种规矩毫无抵触之处。”
《中国孤儿》改编的成功,使伏尔泰从事戏剧的热情更加浓厚。专门在快乐园建造了一个小剧场,排演自己的剧作。每当新戏上演时,周围的群众就会蜂涌而至,快乐园里热闹非凡,伏尔泰为此而感到兴奋。但那时,日内瓦是禁止戏剧娱乐的,伏尔泰的行为违反了政府的规定,当局便发出禁令,严禁日内瓦居民到快乐园看戏,并勒令伏尔泰停止戏剧活动。伏尔泰不甘示弱,与日内瓦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
正当这时,另一位启蒙思想家达兰贝尔来到快乐园,向伏尔泰请教《百科全书》中关于“日内瓦”条目的撰写问题。伏尔泰便建议达兰贝尔在辞条中写上要求在日内瓦建立公共剧场的内容,达兰贝尔遵照伏尔泰的授意写下了这一条目。关于这个问题,也涉及到各个启蒙思想家之间的分歧。卢梭反对这一内容,便写了一篇名为《达兰贝尔谈戏剧书》的文章,批驳达兰贝尔的观点。伏尔泰因此与卢梭展开辩论,卢梭又用《中国孤儿》一剧攻击伏尔泰。于是,在当时就开了一场针对社会实质性问题的,遍及整个法国的大论战。
卢梭认为,“自然状态”下原始的,未开化的人,是善良的、高尚的、纯粹的。在自然状态之下,没有工业、农业,没有法律,没有私有财产和私有观念,没有战争、奴役与统治,天赋人权给人们的广泛的平等和自由,人在自然面前具有自由主动者的资格。这种自然状态下的人,在与自然进行斗争,保护自己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在斗争中增长了才智,发明了工具,引起了社会革命, 私有制随之产生,“自然状态”结束,而“社会状态”取而代之。于是,人类天赋的自由、平等与和平都消失了,人与人之间产生了妒嫉、谋害、欺诈等恶劣行为,为使个人欲望得到满足,产生了无数的社会邪恶。因此,卢梭主张“生活简单化,回到自然去。”
这种观点与伏尔泰的观点是完全相背的。伏尔泰认为,卢梭所描述的“自然状态”, 其意在于寻求人的纯粹的自然本性,并借以论证当时法国的封建专制统治并不是永恒的自然规律,而是违背人的自然本性的。他的“回到自然去”也并不是真正的要恢复到原始的自然状态,而只是要借此激起人们对现实专制制度的憎恨,唤起人们对自由和平等的向往,以便动员人们为建立一个符合自由和平等原则的社会而斗争。这不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从理论上也非常成功地运用了否定之否定的矛盾辩证法。伏尔泰对卢梭的观点进行了深刻的精辟的分析,但同时又尖锐地指出,卢梭把“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完全绝对地对立起来,美化前者而谴责后者,把“自然状态”美化为体现完善人性的人类黄金时代,这是反历史主义的,是历史的倒退。卢梭把产生社会恶习的一切罪恶都强加于科学、艺术和文明的头上,说什么科学和艺术日益进步,可是人变的愈来愈坏了;辩别善恶的树长大了,可生命之树却枯萎了;人的自我完善化能力正是人类一切不幸的源泉,这都是十分错误的。伏尔泰对这些错误论点进行了无情的批驳。他认为文明是应当提倡的,他歌颂理性,推崇文明,强调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和社会生产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历史的进步。他还把卢梭和教会神父相提并论,一概斥之为“可怜虫”。 这下子可引起了日内瓦当局的严重不满。再加上他在文章中称赞新教的牧师既不相信《圣经》, 又不相信地狱,只是与他一样的自然神论者,这样的称赞可是牧师们谁都不愿接受的。他又说宗教改革家加尔文的心是“残酷的”, 更加令人不快。虽则他写信给印刷所,争辩他原稿上写的是“严峻的”, 被误印为“残酷的”, 这种申辩方式是他惯用的伎俩。但事情最终演变的结果,是日内瓦当局的蛮横干涉。这下子,快乐园可不再是乐园了。他说 :“我极爱自由的人民,但我更爱我个人的自由。”
既然法国和瑞士都不能使他得到安宁,伏尔泰便觉得,最好站在两国中间,一只脚伸在瑞士,一只脚伸在法国,或者干脆就有四只脚。在瑞士内瓦湖畔有两座宅邸,在两国边界上再有两座,那么一旦哪边有什么风险,就可以立即逃跑,等待风声平息。刚好这时在靠近日内瓦的法国边境有两块田地出售,一处是多奈伯爵的封地,连着一切贵族的特权出让,还有一处是法尔奈庄园。伏尔泰这时早攒下大笔的财产,他把两处产业同时买下了。这样,他的三窟就布置起来了。“我左脚踏在于拉峰上, 右脚踏在阿尔卑斯山巅,阵地的前面是日内瓦湖。一座美丽的宫殿在法国边境,一座隐居的精舍在日内瓦,一个舒适的住宅在洛桑,从这一窟到那一窟,我终于幸免君王及其军队的搜索了吧!” 这位老人在安排好这一切后,终于满足地感叹了。
十五 卡拉事件
伏尔泰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反对宗教、反对教会,反对宗教狂热、宗教迫害。他几乎是多年来教会最难对付的敌手。伏尔泰不仅在言词上反对宗教狂热,而且在行动上坚决抵抗;不仅自己站起来抵制宗教狂热,而且号召一切社会进步力量同宗教作斗争。伏尔泰是教会不共戴天的仇敌。在伏尔泰看来,基督教就是建立在“最下流的无赖编造出来的最卑鄙的谎话”。 的基础之上,是“最卑鄙的混蛋作出的各种最卑鄙的欺骗”的产物。宗教迷信和教会统治是人类理性的大敌,蒙昧主义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他认为,全部教会史是充满迫害、抢劫、谋杀等罪行的历史,是教会僧侣煽动宗教狂热和宗教偏见的罪恶史。他说 :“自从圣处女的儿子死后,恐怕没有一天没有人不因他而被杀。” 的确,在基督教产生之后,千百万人遭到宗教的迫害死亡或流离失所。伏尔泰对这些人充满同情。他运用各种方式与教会和宗教狂热作斗争,用他手中的笔,向人民灌输对教会和宗教偏见的仇恨,宣扬理性、科学、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思想,在启蒙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战斗作用。他还利用现实事件,抓住正在发生的宗教罪恶,揭露宗教的反动性,抨击教会和僧侣的罪行,平反冤案,解救那些受到宗教迫害的人们。
1761年11月13日, 在土鲁斯城, 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宗教迫害事件。一家绸布店的店主让卡拉,是一位胡格诺教徒。他为人和善、宽容,有六个子女,均已成年。大儿子叫马克安东尼。卡拉夫人出身在贵族,颇善于治家及教养子女。马克安东尼这年29岁,性情抑郁。这一天,家里来了一位客人,是一位天主教徒,曾劝说马克安东尼和弟弟皮埃尔改信天主教。卡拉一家热情招待客人,没有发现儿子的异常表现。马克安东尼在大家都在吃饭时,独自到了厨房。女仆让娜对于他的突然出现很感惊讶,询问他出了什么事,是否受了凉,要不要来烤烤火。马克安东尼只说了一句“我热死了”, 便离开了厨房。
饭后,卡拉夫人让皮埃尔下楼送客。皮埃尔走到楼下,惊奇地发现门敞开着。他预感到发生了什么事,便点上蜡烛。烛光下,眼前的景象令他惊呆了: 安东尼吊在门框上。他的惊呼把全家人都引了过来。大家一齐放下安东尼,并请来了医生。但是一切都无济于事,安东尼已经死了。
卡拉一家开始还以为儿子是被谋杀的,及至他们确信是自杀时,所想到的就是要瞒住安东尼自杀这件事。因为天主教的教义是不允许自杀的。但是,这时已有不少人闻讯赶来。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说是让卡拉杀死了自己的儿子,因为安东尼改信了天主教。其实这种流言是毫无根据、毫无道理的,然而却被教会当成了真情。因为有的狂热的天主教徒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诬蔑说,马克安东尼是被他的父母杀死的,因为他最近改信了天主教,明天就要声明脱离胡格诺教,而按照胡格诺教的传统,做家长的宁愿置儿子于死地,也不愿他改教。这种说法如此荒谬,然而听起来却象真的一样。于是警察被召来,逮捕了卡拉一家及他的客人。
其实胡格诺教并没有禁止改教的规定和传统,并且熟悉卡拉一家的人都知道,让卡拉是一个慈爱、宽容的父亲,对子女的信仰并不加以干涉。就在这件事发生不久前,他们的一个儿子因受女仆让娜的劝说,改信了天主教,让卡拉也并没有加以责备,甚至仍旧将女仆让娜留在家中。信仰天主教的女仆让娜也为主人辩护,一个老人怎么能制服一个年富力强的青年而把他缢死呢?要么就得这样推论,全家人,包括来访的客人,都是共谋杀害马克安东尼的凶手。但这怎么可能呢 ? 父母兄弟联合起来谋害一个嫡亲的骨肉,谁能置信呢?就连安东尼死前要改教的说法,也是没有证据的。
但就是这样荒谬的事情,被教会拿来当作耀武扬威的事例。他把马克安东尼宣布为神圣的殉道者,并且将尸体抬到教堂,念念有词地说,神灵将使尸体复活。这当然是自欺欺人。天主教是禁止自杀的,可这个违反天主教禁令而自杀的人,却得到教会的百般推崇。人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教会为真正的殉道者举行的仪式都没有这么壮观,教堂中悬挂着一副向外科医生借来的骷髅,一只手握着棕榈叶,这是殉道的标志;另一只手握着据说是他签署放弃异端声明的那支笔,作为他被谋杀的证据。
案件被提交土鲁斯高级法院审理。检查官迪库觉得,一个头发花白、年近古稀的老人卡拉,怎么能吊死一年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呢?于是他勇敢地出庭,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