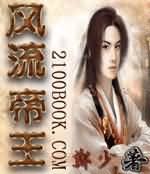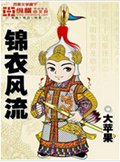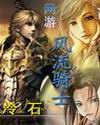庶子风流-第74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们这些新官,反而成了众矢之的。”
叶春秋顿了顿,又接着道:“那些靠着八股,金榜题名的文武百官,还有不少读书人,他们未必敢骂天子,可是对你们这些新官的敌意,显然是最重的,到时是少不得要口诛笔伐,甚至是气势汹汹的嘲讽臭骂,这些新官,心里势必要积攒怒气的,那么谁来反击呢?靠一个两个九品小官?不,到了那时,势必要开始抱团了,而接下来……你们说,谁来做这个首领呢?”
“所以二位兄弟的职责,就是召集这些人,向上,随时协助陛下以及内阁首辅大学士王公,向下,则是团结新官。这是何其大的重担,关乎到的,乃是新政的大局,所以你们的前途,指日可待,十年八年之后,即便是入阁,也未必没有机会的。”
这叶春秋说得头头是道,陈蓉和张晋也不禁心潮澎湃。
张晋犹豫了一下,目光炯炯地看着叶春秋道:“我一个举人,也有资格入阁?”
叶春秋倒是想了想,眼带笑意地道:“陈兄的机会大一些。”
张晋顿时白了叶春秋一眼,哼了一声,道:“你就是瞧我不起,不说这个了,说的气闷,来喝酒,反正这酒花的是你的钱,我喝着解气。”
几杯酒下肚,一切拘泥早已丢去了九霄云外,张晋红光满面起来,便道:“你认为我不能入阁,我偏要入阁给你看看,我乃楚庄王是也,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第一千八百九十章:骄傲的资本
他们这三人,少年时认识,到现在,已有十多年了,虽是后来因为彼此都有了自己的生活和所要奋斗的目标,相聚的时间少了,可是对于张晋的性子,叶春秋依旧是再了解不过了。
这个家伙,遇到什么大事,口里虽是说得振振有词,可事实上,并不是一个真正有什么大志气的人。
反而是陈蓉,性子较为内敛,素来不怎么露声色,却是个心思很缜密的人。
所以对于张晋略带嚣张的话,叶春秋大抵是笑一笑便过去,不会太记在心上。
倒是他见陈蓉满是踟蹰,便忍不住道:“我就知道这一次的酒,一定喝得不甚痛快的,大家心里都有心事啊,说罢,陈兄,有什么话,但说无妨。”
陈蓉叹了口气,才道:“我这辈子啊,其实也没多大出息,唯一做成的一件事,就是这太白诗社了,至于我个人的荣辱,其实早就不敢巴望了。”
“这天底下的人都想读书,读书是为了什么呢?无非就是金榜题名,成为人上之人而已。春秋,说实在话,当初的我,确实也是这个心思,可是很快我便明白了,我这辈子有了更大的意义,不是金榜题名,是将这诗社,好生地壮大。”
“原以为,诗社是以文会友,可是哪里会想到这诗社本就是不如意的人聚在一起,相互切磋一些学问,而那些如意的人,倒是不太愿意进这诗社,反是这一个个不如意的人,而今却是成了新政最至关重要的突破口。”
“我若是现在说我已经无心功名,你一定不信我,不过……说完全没有,那的确是假的,只是已经没有别人那般热衷罢了。人生在世,无非求的是这史笔上留一个名而已,所以既然陛下托付给了我重任,我就一定要将此事做好。”
说到这里,他情真意切地看着叶春秋,继续道:“可我终究是想不明白,若是不以八股取士,当以什么取士呢?”
叶春秋笑了,道:“你们可有想过,当初太祖开了八股,是为了什么?”
其实自八股取士以来,到了如今,大家已将八股文奉若神明,这毕竟是求取功名的唯一渠道,所以大家只知道埋头去读八股文,可是叶春秋这时反问出这么一句话,却是让人深思了。
是啊,开八股是为了什么?
是检验读书人的学问!
这是有道理的,谁都知道,八股文可不好做,能做好一篇八股文的人,那这人的水平都不会太差。至少这四书五经,肯定是熟记于心,而且一定是聪明伶俐的人,死读书的人,固然有机会能够得一个功名,可想要在成千上万个死读书的人里脱颖而出,一定会拥有超高的智慧。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也正因为如此,但凡能金榜题名的人,没有一个人是大家不佩服的,绝不会有人敢说,考中的人是不学无术。
而朝中的百官,也证实了这一点,历经了百五十年,大明的进士们,没一个不是省油的灯,涌现出了不知多少人物。
所以,陈蓉没有犹豫太久,便条件反射地道:“自然是将读书人中的龙凤,收入囊中。”
叶春秋却是摇了摇头,道:“错了,若是要检验学问,八股文可以作为检验的标准,那么诗词可以不可以呢?能做好诗词的人,莫非就不是人才吗?可为何是用八股检验,而非是诗词呢?”
这时莫说是陈蓉,便连张晋也来了兴趣了,忍不住道:“春秋,不要卖关子了,你就给我们说出答案吧。”
对于张晋的急性子,叶春秋抿嘴一笑,道:“八股文的本身,并不在于八股,而在于规矩。”
顿时,张晋和陈蓉都不约而同地呆了一下,显然还不是太理解叶春秋这话里的深意。
叶春秋看了一眼他们的反应,倒没有觉得意外,便接着道:“真正有权势的人,他并不需要告诉天下人,自己如何尊贵,也不需要告诉天下的读书人,我要和谁来坐天下,他只需去制定一个规矩,这个规矩之中,有足够丰厚的奖励,只要你在我的规矩之中脱颖而出,便可以教你一朝富贵,可若是你不按我的规矩来办,固然你有天大的才干,有无以伦比的才华,可是……你不按我的规矩走,不写出我所规定的八股文来,你就是一个庸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读书人。”
“这……其实才是太祖皇帝本身的目的啊,他草莽起家,未必能得到读书人们的支持,他自己对儒生也不甚敬重,甚至心里是很不屑的。”
“对于这些读书人,太祖却深知,虽然自己不喜欢他们,可是这并不代表自己不用他们。可是该怎么用呢?那些有才华的人,恃才傲物,眼高于顶,太祖皇帝,莫非还要降低自己的身段,去三顾茅庐吗?”
“不,太祖皇帝用了一个衡量才学的办法,那就是八股,那些恃才傲物的人,固然眼高于顶,可是一旦他想做官,他就得按着规矩来考,考中了,就能做官。我来问你们,这些恃才傲物的读书人,都乖乖迎合了太祖皇帝,还有什么骄傲的资本呢?可若是你清高,不屑于作八股,问题却又来了,你有再大的才学,你不去参与太祖皇帝所制定的规定,又如何证明你有才学呢?那么……你便再有才华,又有多少人会瞧得上你的才情?你既不敢去科举,去做八股,你还有什么骄傲的资本?这些人,自然而然的就成了闲云野鹤,反而成为被人轻贱的目标了。”
“诗仙李白很了不起吧,他的才情,放在咱们大明,足以称得上是第一才子了,可又如何?他若是不作八股,不将无穷的精力放在这破题、承题、起股上,他不过是个乡间的狂士而已,只会被人瞧不起,被人轻视。”
在陈蓉和张晋久久不语的发怔中,叶春秋勾唇一笑,最后道:“所以这……才是太祖皇帝的本意啊。”
第一千八百九十一章:以什么取士为好
叶春秋的一席话,听得陈蓉和张晋目瞪口呆,陈蓉微微一愣,便陷入深思,他不可否认的,叶春秋口里所说的标准和规矩,确实是令人耳目一新。
叶春秋看着他们的表情,便知道他们已经理解了他话里的深意了,此时,他又笑着继续道:“其实,对于太祖来说,他并不在乎读书人真正有什么才情,他所在乎的是,但凡是读了书的人,大多都是士绅之家,寻常人连饭都吃不饱,哪里还有闲心读书?只有那些有闲心的人,若是不给他们一丁点事做,不将他们的精力用在太祖皇帝所希望用的地方,那么,一干多少在地方上有些声望,又有一些家底,再加上还有些学识的人凑在一起,若是妖言惑众,或是图谋不轨,那么,这大明可是要出大乱子的。”
“所以才学高低不重要,他要的,是大家看到了金榜题名的期望,为了这个金榜题名,耗费掉那些过剩的精力,同时,这些人若是高中,正好为太祖所用,而至于那些不中的,却只好期望来年再考了。”
“因此,八股取士与否,都不重要,八股不取士,诗词也可以取士,诗词不取士,即便是用算学取士,又如何?”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规矩!”
说到了这里,叶春秋再无轻松之色了,反而一下子摆出了他鲁王的威仪,正色道:“立下了规矩,就等于是谁有才学,谁是草包,都是朝廷说了算,今日立下了新规矩,一年之前,八股文作得再好的才子,若是不乖乖地去学习新的知识,他便是一无是处。”
“那么,春秋的意思是,考诗词?”陈蓉又是愣了一下,轻皱眉头地看着叶春秋问道。
“不。”叶春秋认真地道:“八股文,对于治理国家,有丝毫的作用吗?对于治理一方的百姓,又有什么用呢?都没有用,太祖皇帝制定的规矩里,所谓的八股文,其实就是一块敲门砖罢了,让他们把门敲开了,做了官,再让这些聪明人,自己去领悟怎样去做一个官,现在既然要改,以诗词取代八股,又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啊,现在既然要设立新的规矩,所以制定新的标准的同时,还是需要务实的。”
陈蓉也是很认真地听着叶春秋一一分析,到了现在,他连连点头道:“春秋说的不错,只是既非八股,又不是诗词,那么……该以什么取士为好呢?”
叶春秋笑了,道:“律法如何?”
“律法?”
陈蓉想了想,不禁沉吟起来,律法确实实用,毕竟将这律书熟读与心,对律令了然于胸,这不是什么坏事,至少将来做了官,本职之中,就需承接百姓诉讼的。
可事实上,许多做了八股文起家的读书人做了官,对于律令的条文,只怕所知也是有限的,判起案子来,多是靠自由心证,说你有罪就有罪,说你没罪就没罪,很多时候,所谓的冤案,怕也并非是什么官官相护,或是收受了财物,实际上,却全是地方官胡判乱判。
此时,叶春秋又道:“律令也是朝廷的规矩,这个规矩里,便要求所有人都能够遵守。大明一直都有律令,可百姓们却不将律令当一回事,陈兄,你认为是什么缘故?”
陈蓉苦笑道:“春秋别总是反问我,不要卖关子了。”
叶春秋开朗一笑,喝了口酒,赔罪道:“是我的不是,好吧,我就直说了,其实大明自有律令,除大明律之外,太祖当初,还专门颁布了大诰,太祖皇帝为了将大诰深入人心,甚至要求各家各户,都需收藏大诰,可事实上呢?事实上,百姓们并不将这些当一回事,这不是因为百姓愚蠢,而是因为,连决定刑法的地方官吏,对于律令尚且一知半解,你百姓就算是遵守了大明律又如何?所以,在大明,律令和一张废纸,并没有太多的分别,官员所知不多,做了官,也懒得去翻阅那堆积如山的各种律令,而百姓们呢,知道决定一切的,并非是大明律中的条文,那么,谁还会将这大明律当一回事呢?”
“所以,考大明律,唯有如此,天下的读书人,方才会纷纷去学习大明律,做了官,才可以学以致用,而一旦官员们开始在律令之中寻找各种条文来断案,那么寻常的百姓,方才知道律令的好处,于是人人都不敢去触碰那些大明律中的禁忌。因此,百姓们多少会学习一些律令,读书人更是如此,官员断案,一旦脱离了大明律,就少不得要被那些精通律令的读书人抨击,被那些略知律令一二的百姓所质疑,这种冤案错案,也就可以得以收敛了,即便是官官相护,或者与人勾结,也就没有那样轻易了。”
陈蓉连声说是,甚至连张晋也觉得极有道理地点着头认同。
以律令来做标准,确实有极大的好处,这会使大量的人像熟读四书五经一样,去熟读律令,将这律令背的滚瓜烂熟,而越多人精通,任何一个案子,若是官员判得过了头,就会很容易被人所质疑和抨击。官员们为了官声,怎么还敢胡乱判案?
只是陈蓉想了想,却又皱眉道:“可问题在于,律令是死的,就如四书五经一样,多少读书人几年下来,就可以背个滚瓜烂熟了,那么岂不是一场考试下来,人人都能默写出大明律,不知多少人会因此而高中?何况,又如何将读书人加以区分出成绩的好坏呢?”
这确实是个难题,叶春秋却是道:“律学,不过是考试的一种而已,又不是只考一个律法,这地方官员,甚至是各部堂的大臣,难道不需要懂一些经济之道?若是两眼一抹黑,对钱粮一窍不通,这做了官,怕也只是个糊涂官罢了。”
“所以,何不如再加一门考试,为经济考呢?里头囊括了算学,包括了修桥铺路所需的花销。”
第一千八百九十二章:这一手真是毒
叶春秋的每一个观点,可谓是说得头头是道。
可是当叶春秋最后说到这个经济考时,陈蓉却是没有多大信心起来,不禁汗颜道:“读书人的性子大多锱铢必较,只怕许多人对这考经济学,要破口大骂了。”
叶春秋却是笑着摇头道:“骂肯定是骂一时的,可读书人要做官,就得考,就得去学习这个啊,一开始,大家在骂,可大家为了前途,还是不得不去考的时候,他们最后岂不是在骂自己吗?所以,只需划出标准,让他们骂一些时候,到后面,想做官的人,该学的还得去学,那些不肯去学的人会骂,可是更多人,却还是会为功名而去学的,他们骂了,显得自己清高,可最终,骂的还是那些学习经济之道的读书人,到时,学了的人,只怕拥护都来不及呢,人啊,总不能骂自己吧?”
张晋不禁失笑,道:“春秋,还是你厉害,这一手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