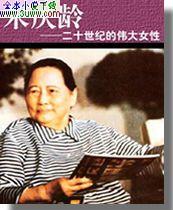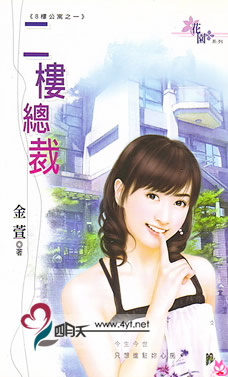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6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她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说,“WTC(吴铁城)让自己担起了当面申斥我的任务。他还不满足……又让H将军(何应钦)的代表……帮他来围攻我。他们不承认事实,只是一个劲地责备我呼吁解除对游击区的封锁。”①
①谢伟思书,见本章注12,第108—109页。
谢伟思把宋庆龄同她的家属及国民党权贵的关系看作是衡量国民党同开明人士之间关系的标尺。这种看法肯定更符合事实,不像近来有人把宋庆龄同她的家属的关系情绪化,似乎他们之间的骨肉之情胜过政治上的分歧。亲人之间的感情当然是存在的,但对宋庆龄来说,原则决定一切。
让我们再来引几段谢伟思的话:
“我不能不得到这样的印象:孙夫人现在的处境极为窘迫和艰难,她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了一个囚徒。这一点她在谈到关于她为解除反共封锁而努力所引起的不快时所说的一句愤愤不平的话语中流露了出来。她说,‘他们所能够做的无非是不让我出去旅行。’”
国民党不但限制她出国旅行,连在国内旅行也有限制。她在1943年4月7日给格雷斯·格雷尼奇的信中说,“我希望能去一趟兰州和西安,但能否成行要看警备司令是否批准。我渴望亲自去看看。”但她到底没有去成。
在谢伟思上面谈到的那次访问以后三个星期,在1944年3月5日,他又去看望她并且发现她更加愤懑: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正好在拜访她。(我一到)他就走了。我表示歉意,她笑着说,这是一次很令人难以忍受的谈话,而且谈得太长了……这位部长的意思是她在一个中国国内问题上,向国外散布不真实的情况和无稽之谈。
“部长来找她还有另外一件事,那就是为了她已同意在孙中山诞辰纪念会上发表广播演说,关于演说的内容要求她接受妥协的方案。这一演说是美国纪念活动的一项内容……是赛珍珠和其他有影响的美国人士向宋庆龄发出邀请的。……她拟的演说稿……在送审中被作了大量删改,因此她表示要取消这次演说……她绝对不能在原则问题上妥协。她原先已同意美方的邀请,如果后来又取消了,中方主管宣传的部门很难交待,所以部长赶来同她谈判,希望双方能够妥协,但没有成功。她毫不对他觉得抱歉。”①
①宋庆龄由重庆致缅甸前线理查德·杨少校,1944年3月11日。
她后来于1944年3月12日为在美国举行的孙中山纪念日所作的广播演说《孙中山与中国的民主》①中,最后一段是这样说的:
①谢伟思书,第109—110页。
“孙中山在反对满清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决不会认为国外朋友对于我们人民的运动的支持是有损国家主权的一种干涉行为。今天我们人民也不会那样想。对于像美国的孤立主义和压制印度独立之类的现象,我们认为有权加以批评,同时我们也承认别人有权分析我们国家中的情势并提出批评。
“有人批评我们有依赖外国的倾向。我要指出,固然所有中国爱国人士都认为我们的抗日军队应该得到一切可能的援助,但是,只有那些采取观望态度,不积极参加我们民族斗争的中国人才会对人民缺乏信心,以致哭哭啼啼表示说,倘使明天外援不来,后天我们就会垮台了。为我们的国家和为我们的前途而战斗的人是要求援助的,可是他们为之而作了这样多牺牲的目标是不受任何条件的影响的。”
现在再接着介绍谢伟思就他同宋庆龄谈话所作的报告:
“谈到最近关于宋子文被捕的谣传,她付之一笑并说他要是被抓起来审判倒是件好事,因为这样可以使气氛澄清。我说总要有个罪名才能起诉……她回答说,随便什么事情都可以被说成是一种罪名。从(她的)态度看来,委员长(蒋介石)一定对宋子文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指控。她接着又说,如果把她同子文关在一起倒很不错。
“她说,(她的姐夫)孔博士很为她担心。他说过,‘你要是老这样说话,他们把你抓起来怎么办?’她回答道,她欢迎他们来抓她。”
她对恶劣环境的挑战不但勇敢而且泰然自若,充分显示出她的精神力量。
谢伟思还报告了另一次有关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谈话。宋庆龄说,戴笠正在把重庆一些防空洞用作秘密监牢,这是一个被关在那里的青年托人偷带出来的条子上透露的。
为了更有效地对日作战,谢伟思同史迪威一样反对封锁中共领导的地区、赞成重庆政府实行改革。在1944年6月20日写的题为《中国的局势:关于美国政策的建议》的报告中,谢伟思提出了在华北地区未来对日作战中“帮助共产党和游击部队或同他们合作的问题”。至于促进重庆的改革,“一个非常有效的行动……将是由白宫对孙逸仙夫人发出邀请’。①
①《为新中国奋斗》,第145—147页。
驻重庆的外国记者是宋庆龄与之建立某种有效联系的另一群人。
美国(时代一生活》杂志记者西奥多·H·怀特1943年亲眼目睹了河南省的大饥荒后回到重庆。他想要让蒋介石知道这些惨状并采取一些行动,但起初没有成功,后来——
“全靠(蒋的)二姨、孙逸仙的圣洁的遗孀的帮助,……她坚持要这个独裁者接见我。
“她最后给我写的一张条子使我对会见坚决起来,她在条子里安排了这一约会。‘……他们对我说,他(蒋)很累……但我坚持说这是一件牵涉到千千万万人生命的事情……’她写道。
“她又说,‘我想对你建议,你在写报道时要像对我谈的时候一样坦率和无所(炫)畏(书)惧(网)。如果对此而倒霉受罪,那也不要泄气,否则局面就不可能有丝毫改变。’”①怀特所写的关于河南饥荒的毫不留情的报道在《生活》杂志刊出后,宋庆龄很快就对这位记者大加赞扬。“我看这样一来他要再来(中国)会有麻烦,”她写道,“但他如果知道他为中国人民办了一件好事,他会感到欣慰的。”②在同一封信中,他以赞扬的口气提到了另一位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一个有才能、有新闻敏感并对中国老百姓有深厚同情的人。“我读了杰克·贝尔登关于三年前缅甸撤退的书,很感兴趣。它至今被认为是关于这一战役的最佳作品。”
①谢伟思书,第155页。
②西奥多·H·怀特着《寻找历史》(英文),第154—155页。
前面提到她通过当时任“联合劳工新闻社”驻重庆记者的本书作者发表《致美国工人们》一文,也属于她同外国新闻界联系这一范畴。
(七)统一战线——以及救灾
在中国社会中,在明晃晃的重庆政治舞台上,宋庆龄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以表明她在建设一个争取更多外援、反对国内压迫的统一战线的工作中的立场。她的一个办法是,只要有可能,就同她在30年代救亡运动中的老同事在一起公开露面。这些人1941年在重庆联合组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它的核心后来成为“中国民主同盟”)。
同她和她的老同事们常在一起的有革命学者、诗人郭沫若。在国共合作进行北伐时,他曾负责北伐军的宣传工作,后流亡日本多年,不作政治活动,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才回国。
国民党某些著名人物采取抗日和反对内战的立场(如冯玉祥将军)或者即使暂时向这个方向转变(如孙科),她都注意到使公众有机会看见她同他们在一起。
她参加对已故爱国进步人士的纪念活动,从不缺席。救国会“七君子”之一邹韬奋在香港沦陷后辗转去苏北新四军工作,1944年7月24卧因病去世,以参加中国共产党作为遗愿。10月1日,由宋庆龄领衔发起的追悼大会在重庆举行。在反动气焰趋于嚣张的时期,她特别注意参与这一类型的活动。她的在场会提高这些活动的声望、扩大影响,还会提供某种安全保障。
两周之后,即10月19日,她又同救国会老人沈钧儒、作家茅盾等人出席鲁迅逝世纪念大会。如同8年前在上海为鲁迅举行送殡仪式时一样,有人企图捣乱,因宋庆龄在场而未敢轻举妄动。她自己这样写道:
“上星期我们为鲁迅开了一个纪念会。那些SS①在我离开之后(因为我有另一个约会)冲进会场,桌椅横飞,出现一场暴乱。”②
①SS可能是Secret Service“特工处”的缩写,也可能借用纳粹党卫队的缩写作为比喻。——译者
②宋庆龄自重庆致缅甸前线理查德·杨少校,1944年5月29日。
在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中,宋庆龄坚持在重庆——尽管受环境的限制——举行一些募款活动,因为这对建立全国性的和国际性的统一战线有好处。王安娜引用她的话说,“我们总是请外国朋友捐款,这不是办法。这里有的是富翁,应该请他们为崇高目的捐献,哪怕是一个人几块钱也好。我们在这里也开展一点工作的话,那我在海外的工作也好做了,可以争取到外国朋友和华侨更多的捐款。”①
①宋庆龄自重庆致纽约格雷斯·格兰尼奇,1944年10月28日。
她和保盟举办的救灾活动不但在救济工作上、而且在政治上都有很大效果。在1943年和1944年的大饥荒中,河南、广东两省受灾人数以百万计——除自然灾害外,还因为国民党官员和军队的横征暴敛以及地主奸商的重利盘剥。这些救灾活动都搞得有声有色并且不取任何费用,同国民党政府只说空话、不做实事以及重庆那些发国难财的阔人对灾情视若无睹适成对比。但由于是孙夫人发出的呼吁,所以甚至这些老财们也不好意思不拿一点出来了。
救灾活动所募集的款项一部分由保盟交给“工合”,为河南灾民组织生产自救。有许多灾民逃往解放区,生产自救在那里开展得最有效,灾民的口粮和劳动生产都安排得很好。
1943年5月中,由宋庆龄主持、“保盟”举办的赈灾国际业余足球比赛在重庆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这个主意是许乃波先想出来的,宋庆龄立即接受。许是一位爱好体育的工程师,在香港时是“保盟”的技术顾问,到重庆又参加了它的常设委员会。他是在英国上学的,同半官方的“中英文化协会”有关系。他为筹办这次义赛举行了一次宴会,邀请几个国家驻重庆的大使出席,席上得到了他们的赞助。在中国官员中,重庆市长贺耀祖将军(也许是因为他那位支持“保盟”的夫人对他做了工作)授权市足球队参加,还命令市政府的军乐队到场演奏助兴。消息公布、请柬发出、赛票售出之后,国民党才匆匆忙忙通知说,只有它所属的机构才可以募集赈灾捐款。保盟没有理它,国民党要强制取消这样的国际比赛,时间上也来不及了。
当宋庆龄到场主持开球式时,许乃波要军乐队演奏中国国歌。“我们只在国家典礼上才演奏”,乐队指挥起先不同意。许坚持说,“孙夫人是国母,到会的还有要人和大使(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苏联和美国)”。军乐队到底还是奏了国歌。①
①王安娜书,第390页。
许乃波还记得,在筹备足球义赛过程中,有一件事情足以再次显示,宋庆龄总是灵活性和原则性两者兼顾。这次义赛的一位重要的外国赞助人是英国大使霍勒斯·薛穆爵士。在那次宴会上,在随便谈话时,薛穆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辩护,他的论据是当时英国人常用的,即: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对任何事情都不能取得一致。宋庆龄马上反驳道,有一件事情他们确实是一致的——英国统治必须结束(印度独立运动领袖包括她的朋友尼赫鲁当时都在狱中)。她所以这样坦率地讲话是因为她始终保持一个基本的观点,即:不能因为战时的同盟关系而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保持缄默。后来,在上面已经提到过的1944年纪念孙中山对美广播演说中,她又明确指出,“压制印度独立”是该受到批评的。
尽管她同薛穆大使有这样唇枪舌剑的交锋,这位大使并未因此而撤回他对足球义赛的支持。大使夫人维奥莱特也没有因此而不志愿参加宋庆龄的救济工作。这都可以证明宋庆龄所受到的人们的尊敬。
这次足球义赛还有一段有国际意义的插曲,那就是由流亡的朝鲜人组成的一支足球队参加了义赛,并且高举着日本吞并朝鲜之前的朝鲜国旗。
据本书作者回忆,有关赛事的安排是很简朴的。观众席是用长木板铺在架子上制成的,只有少数贵宾坐折叠椅,但上面也没有遮阳。就重庆来说,观众算是很多的,许多人没有地方坐,一直站着,其中有人是为了表示对孙夫人和她的事业的热心支持,而不只是为了看球。外国使节成群地来参加,他们从各自的考虑出发,都认为出席这场义赛在政治上是明智的。其中也确有精明内行的足球迷,包括通常较为沉默的苏联大使。他是足球迷这一点过去可能不为人知,现在无疑也为那些收集个人情况者所注意到了。
宋庆龄同每个球队队员握手,代表灾民向他们致谢并发给每人一枚纪念章。
保盟还主办义演,其中有专业剧团的演出。有一个剧团是由进步演员和导演金山领导的。在重庆,从事舞台生涯的人过着艰难的生活。有人在义演过程中看到他们的生活情况后说,“当我看到这些男女演员们睡在一间大厅的地板上、连床铺都没有时,我意识到他们对孙夫人是多么敬爱和信任啊!”①
①许乃波1987年11月8日致本书作者函。
有一场舞蹈义演是由特立尼达出生的戴爱莲组织的。这位中国芭蕾舞创始人之一在香港也曾帮助过保盟。
还有一些不那么正规的音乐会也是为了赈灾举办的。参加演出的是驻重庆的西方国家和苏联的年轻外交人员和军事人员。在音乐会上,有时听众同演出者一起引吭高歌,有苏联歌曲,也有英国约克郡民歌。
这些义赛和义演在战时首都重庆得到中外人士的热烈参加,使人们注意到救济工作是何等迫切,而国民党统治者都并不重视。这些活动使许多人有机会看到宋庆龄并进一步增高了她的声望。同时也使更多人看到保盟仍在积极工作,而这正是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