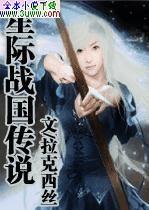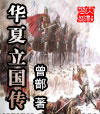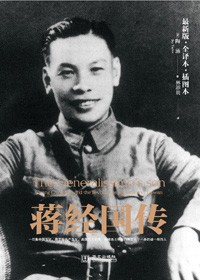蒋经国传-第1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中央训练团”,特别开办“实验绥靖区干部训练班”,训练区长、县长等干部,配合施行。
认真实施,也就和美国在南越办的战略村类似,是以组织对组织的一种手段。
南越这一妙招,没有成功,关键系于:
(1)属于政府方面的干部,赶不上越共方面干部对主义信仰的宗教狂热。
(2)政府军没有力量保护村民的安全。经不起越共的报复打击。
中国的情况,较越南更特殊。地主和农民的利益,彼此矛盾。绝大多数农民相信,跟着共产党走,将结束贫困,获得翻身。
凭这付印象,已命定失败,劳民伤财,空忙一阵。
经国有什么选择呢?明知不可为,亦只有临危受命,鞠躬尽瘁。
计划没有出门,困难来了。行政院重划行政区是第一关,中训团另编预算,订编制,备营房是第二关。
行政院的官僚们,对国事的轻重缓急,漠不关心。仅知道照章办事,奉公守法。一记太极拳打过来,经国已手足失措。他们说:“设立实验区,事关改变现时政区,行政院政务委员无权定夺。须将原案咨请立法院审议通过。”耗时旷日不说,能否顺利通过,还是未定之数。
最后,还是蒋先生想到的变通办法,根据“戡乱总动员令”,交国防部出面办理。但“实验绥靖区”的原定计划,早已走样。
国民党的事,如是拖泥带水,甭说,对敌斗争之不易,对付自己的官僚阶层,就够辛苦了。
“戡建班”第一期毕业的学生,约一千二百余人,编为六个大队,每人发美式手枪一支,子弹两百发,官阶准尉、上尉不等,颇有点御林军的威严。
一九四八年一月,国防部戡建总队'16'成立。总队长胡轨,下辖六个中队,分驻苏北、皖北、豫南、鄂北、鲁南、冀东各地。但都受经国直接主持的“戡建中心小组”指挥。
队员或个别、或小组,参与地方施政,组训民众等工作。有时用他们的上方宝剑,进行搜查、逮捕活动。以戡乱建国的“先锋队”、“政治兵’自居,难免轻视地方干部的尊严,发生越权揽权等情。因而,戡建的功能,未见发挥,内部倾轧的现象,不一而足。
戡建总队之外,尚设戡建小组,负责情报活动,为经国经营情报组织的滥觞。
其奈,俱往矣,随着国军的覆灭,他这支新兵,被俘、被歼的.占十之八九。他们是充州第五大队,于许世友占领济南后,自大队长谈明义以下,无一幸免。少将督导游鲲(曾任蒋主任秘书)同时成擒。
襄阳第四大队全队被歼、包括大队长刘复州在内。
潢州第三大队,因豫南战局吃紧,各奔东西,而自行解体。
淮阴第一大队,未遑开展工作,即和南京的联系切断,后陆续逃回上海。
合肥的第二大队和唐山的第六大队,一九四八年七月调到上海。
武汉“戡建小组”的组长宋特立,携秘密档案投共。
赣南时期,经国曾说过:“年轻人的日子是不夜的,可是年轻人的黄昏来得太早了。”现在,竟成了他自己的忏语,命运就这么捉弄着他。
注释'1'吴嘉静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共谈判与马歇尔使华》,《中报月刊》第41期(香港一九八三年六月》,第98页。'2'曹聚仁著《采访二记》,香港创垦出版社出版'3'曹省三、曹云霞答《蒋经国系史话》,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一九七九年八月出版,第178页。'4'程思远著《李宗仁先生晚年》,第9页,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一九八0年十二月北京。'5'白斌为广西籍立法委员'6'第一次当选国民党中央委员。'7'同'3'。'8'黄维,前国军十二兵团司令,徐蚌会战被俘,一九七五中共释俘时,恢复自由。'9'同'3',第185页。'10'毛泽东著《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29页。这一统计数字,不一定正确,但国军损耗巨大是事实,董显光谓“到了民国三十六年终,中国政府日益增加的危 3ǔωω。cōm险已呈更剧烈的现象”。《蒋总统传》,第488页。'11'电影《南征北战》和《红日》即描写此役经过。战争发生于山东沂蒙山区。'12'参阅《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一九四六年十一二月),一九四七年四月,共军主动放弃延安国军得一空城,不久,胡部被全歼。'13' Russell Randall准将,认为这场战争有五个方面:战场上、财务上、政治上、精神上和心理上。见《中国时报》旧金山版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九日第二版。'14'暗杀闻一多、李公朴,其余如特务恐怖、抓人、判刑、坐牢等。真正的共党分子,极少抓到。'15'同'3'。'16'国防部系统的特种工作队,尚有“人民服务总队”属邓文仪的国防部新闻局,“绥靖总队”属国防部第二厅。
…………
12八一九防线
战争进入第二年(和谈破裂),共军反守为攻,国军精锐,象见到太阳的坚冰,快速融化。
毛泽东“宜将胜勇追穷寇”'1'的战略,就是看准蒋的弱点,不让南京有喘气的机会,由内线进攻,加速蒋氏王朝的崩解。
等到后来,蒋看到事态之严重,承认经济战场上,也遭受挫折,已生命垂危,再无法挽救了。
据董显光说:一九四八年夏间,印刷纸币的费用,已经赶不上货币的兑换价值。'2'从社会经济的实情去了解,假定,以国立大学的教授收入作例:“胜利初期的教授收入,约等于战前的十分之一;如以银元来计算,约等于十五元上下,到了发行金圆券的前夕,我们的收入,只等于银元五、六元左右了。这份薪给,比之战前女工,还差了一半。”'3'这是一位教授的自述。再从当时流行的钞票面额来看,一九四八年的七月十九日,二十五万元的关金大钞开始问世了,法币的发行量已是战前的二十万倍,物价的涨度为战前的三百九十万倍,物价上涨的幅度,如此巨大,可真是“法币的末日”了。
造成这样严重情势的因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内在的,也有外在的。外在的压力,是中共的控制地区,日益扩大,到这年的六月三十日为止,解放军已经控制了二百三十五万平万公里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超过一亿六千八百万。国库收入(田赋)锐减,但军费相反地直线上升。赤字成为天文数字。
国府更大的困扰,每失一地,即产生成千成万的难民,即这些人内心里拥护国民党,恐惧中共的“解放”、“翻身”。据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的统计,此项无家可归的难民人数,共达两千万之巨。政府无法坐视,需予人道救济,因而益增财政上的沉重负荷。
“无粮不聚兵”,早是支援战争的先决条件。但是,中国在战争中,已长期失去生息喘气的机会,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五年,从事剿共战争,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对日抗战。国共内战,又持续数载,民穷财尽,筋疲力竭。
美援是当时南京政府的唯一希望,而美援却不是那么说来即来。华盛顿夹带着附带条件,那就是:国民党先要自助,着手政治革新,推行民主运动,才肯慷慨解囊。
华盛顿的观点,并不全错,但也不全对,它不能用施舍的态度,无条件地送钱送枪送炮,希望每一分钱花下去,有一的钱的功效。然而,客观事实是,国民党已经病入膏育,再猛的药物针剂,短期间,亦无法使它恢复健康,进而生机勃勃。
至于陈伯达所说的“四大豪门”等等,和真实情况,并不全部符合。
谁当财政部长,谁也没有办法,唯有“凭了印刷机,把法币象洪水似的天天泛滥出来”,应付急需。其后果是“一方面冲淡了人民原有币值的购买力,一方面更以最强大的购买者资格,把都市的与农村的物资囊括而去,生活物价飞涨,币值日降。” '5'
渐渐地,灵符失灵,“举国已成法币世界,都市大宗买卖早用黄金美钞计算,农村社会普遍以粮食作价格标准,偏僻地区又已恢复银元往来,物物交换风行各处。”法币在人民心目中,“失去价值尺度的机能,失去流通手段的机能,失去支付手段的机能,失去贮藏手段的机能。”'6'换句话说,国府的财政经济和军事一样,面临崩溃的边缘。
法币既陷在解体的过程中,改革乃变为官民上下一致的呼声,甚至“改得好,当然要改,改不好也要改。一次改不好,可以再改,多少让人民能够喘一口气来。”'7'
改革早在酝酿,下决心见诸行动,却等到一九四八年的八月。
七月下旬,蒋在莫干山,召集他的高级经济幕僚,频频举行会议,京沪报纸盛传,币改如箭在弦。七月的最后一天,蒋突飞上海,在沪举行会议。八月十三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离京前往牯岭,晤蒋会谈,于是订名为经济紧急处分方案的新政策,始拍板定案。
八月十八日,蒋下山返京。第二天,明令公布币改内容。第三天,蒋、翁(文灏)联合招待民意代表及京沪银、钱业,同日宣布政院下设经济管制委员会。二十一日,发表俞鸿钧和蒋经国的新任命。行动迅速和敏捷,显示政府的决心,非打赢这一仗不可。'8'
方案的条文甚多,归纳起来,不外下列四大项目:(1)自八月十九日起,以金圆为本位币,十足准备发行金圆券,限期(十月二十日前)收兑己发行的法币及东北流通券。(2)限期收兑人民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币与外汇,于九月三十日前,兑换金圆券(其后又将限期延至十月三十一日),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持有者严办。(3)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外国的外汇资产,违者制裁。(4)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开支。
紧急处分令,系总统根据宪法临时条款所授的权限,即西方所谓的Mandate,无需经过立法院的立法程序,和美国参议院在东京湾事件后通过的越战授权相同。
南京不惜孤注一掷的决心,从八月二十日《中央日报》的一篇社论可以看出来。文章说:
“社会改革,就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抑制少数人的特权。我们切盼政府以坚毅的努力,制止少数人以过去借国库发行,以为囤积来博取暴利的手段,向金圆券头上打算,要知道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把这个割盲肠的重任交给经国,任上海经济督导员。蒋先生实在没有别的王牌可打,只有太子于满朝文武中,赤胆忠心。而经国自己也颇具自信,咸认“认真实行”,即能“扑灭奸商污吏,肃清腐恶势力,贯彻新经济政策。”'9'
经国的信心,来自……他的潜意识,列宁十月革命以后的困难,不就被布尔什维克的同志们消灭了吗?他很自负地说:“假使将这个政策看做是一种社会革命运动的话,同时又用革命的手段来贯彻这一政策的话,那么,这一政策,我相信一定能达到成功。”'10'
然而,民间舆论,却向他大泼冷水。
上海出版的《经济周报》,带着严重的失望,在社沦中写着:
“不知是故意还是无知,政府的经济措施,却始终认为:无中可以生有,对人民始终没有放弃玩弄那一套无中生有的把戏。”'11'
香港出版的《远东经济评论》断言:“这是临时的镇静剂,可以缓和经济的贫血症,却不会有长久的功效。”接着说:“中国的一般情势是绝望的,蒋和翁的申明,已不再隐匿其严重性。”'12'
美国出版的《华盛顿邮报》更有直率的评论:
“由于内战关系,军队的人数日增,任何方式的币制改革,在此时提出,都将注定失败的命运。而且,除了内战以外,其它足以使这个改革能成功的条件,亦不具备。这些条件是:强有力的政府,有平衡的预算,健全的赋税制度,现在我们所能寄于希望的,莫过于此新出的金圆券,勉可通行一时。
负责拟订这个改革方案的是发明四角号码的王云五财长。据王乐观估计,币改后,政府的总支出,约为三十六亿金圆券,税收在按战前标准调整以后,可得二十五亿,赤字仅及十亿。弥补的办法,可以靠出售国营事业(棉纺厂公债),美援物资,以及增加侨汇。”'13'
经济学家,则大不以为然,“税率按战前标准调整后,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真正征得到手的(两个月是一个很乐观的估计);但支出却不能等待,假使在调整税收所需期间,物价继续增加,开支的数目也必与物价等比增加,一切岂不都成泡影?”'14'
国营事业,经过官营的结果,早是烫手的蕃薯,民间收买的兴趣,微乎又微。而出卖公债的可能性更小,升斗小民,公教人员,有心无力,大商贾对飘摇毋定的局势,缺乏信心,有力无心。
侨汇的增加,有其一定的幅度,无外力可使;而且,统计数字显示的结果,一丸四八年较一九四七年,更为减少。
基于平衡的理想,政府希望今后在节流开源方面着手,具体的措施是增加出口,减少浪费,撙节外汇。这个说法,其实是信口开河。战争一天不停,战争的机器,就无法停止,这些燃料滋补从哪里来?当然,要靠外汇,而撙节又从何说起?
王云五最大的如意算盘,希望美国拿出五亿美金作后援。王特别专程赴华府,但是杜鲁门政府给他吃了闭门羹。
经国带着他“新赣南政冶”的资本,调来了“戡建大队”,向渔管处借调一部的旧干部,在上海中央银行内,设置办公室,就杀气腾腾地,打起老虎来了。
照政府公布的物价管制办法,规定所有货品,必须停留在八月十九日的市价上,即官方称谓的“八一九防线”。管制的目的,打击投机市场,“革上海人的命”。
在经国的统一指挥下,二十三、二十七两天,上海市六个军警单位(金管局、警局、警备部稽查处、宪兵、江湾以及京沪、沪杭两路警察局)全部出动到全市市场、库房、水陆空交通场所,进行搜查。命令“凡违背法令及触犯财经紧急措施条文者,商店吊销执照,负责人送刑庭法办,货物没收。”
七十天的经改,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从“八一九”到十月二日,是第一阶段;十月三日抢购开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