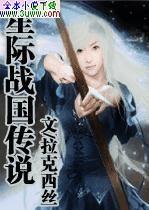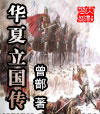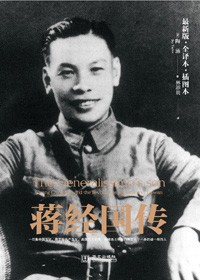蒋经国传-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假使,他模仿瞿秋白,写下他自己的《赤都心影》,比秋白的故事动人多了,拍成电影,凭其曲折离奇的情节,赚人眼泪之外,醒世的意义更大。可惜,缺少西哈努克亲王那样的浪漫气质,基于敏感的政治理由,苏联这一段,成了禁脔,连提都提不得呢!
总结经国对苏联的印象,爱恨交错,划不出一条明显的界线来。他是真正深入基层,和苏联人打成一片的,种过田、做过工,交过小彼得、沙弗亚那样的朋友,体会到苏联的平民还是朴素的、真挚的、善良的。
初期的布尔什维克,和他自己一样,有理想、有抱负,心灵纯洁,狂热献身。二十年代苏联社会朝气
蓬勃,和沙皇执政时期的贪污腐的,形成强烈的对比。社会主义制度,的确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但是,斯大林一连串的整肃斗争,连革命功臣,优秀同志,都以莫须有的罪名,充配、杀头、进集中营,他开始打起问号,革命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在苏联的时间停留愈久,愈怀念故国的山川人物,中国的现状,究竟怎么样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现在,他感到他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苏联不是他的“祖国”,“工人无祖国”,原是国际共产主义者的美丽谎言。
和父亲睽违已十二载,临别前,父亲曾有不少叮咛,想到一九二七年四月为了“四·一二惨案”,对父亲的公开批评指责,倍感不安,将来一旦见面,如何向他解释?去年的声明,会使老人家更光大,所以,他问蒋大使:“你认为我父亲希望我回国吗?”
和蒋方良的婚姻,'7'系由环境所使然,父亲对这位洋媳妇,会怎么想呢?母亲更保守,她看得惯这位蓝眼睛高鼻子的洋鬼子吗?
一九三七年,中日战火迫在眉捷,继何梅协定后,华北的晋冀察绥靖委员会,表面上,由宋哲元控制,日本的统治阴影,已四处弥漫。经国带着妻儿,于三月二十五日踏上征途,出发当天的日记,这样写着:
“今天我要离开莫斯科了,早晨五时就起床,从我的房间望出去,可以看得见克里姆林宫,同我在十二年以前所看见的克里姆林宫,差不多完全一样,不过几个教堂顶上的双头鹰,已经看不见了,现在所能看见的,是由宝石制成的五角星。克里姆林宫是苏联的政治中心,我曾经到过四次:一次是去参观(一九二五年):一次是参加共产国际会议(旁听,一九二六年);一次是参加军事高级学校毕业典礼(一九三O年);一次是参加苏维埃大会。
孙逸仙大学前面的大礼堂,在三年之前已被拆毁,现在在那里正在开始建筑伟大的劳动营。国家大戏院前面的小屋及小花园,已经完全毁灭,现在成了一个极大的停车场,大戏院要比从前威严得多了。国家大戏院右边的低屋及小菜场亦早已拆毁,现在这一区成了莫斯科中心,在这条街上都是高楼大厦—人民总委员会办公处、莫斯科大旅馆、外国人旅行招待所等。莫斯科的地下铁道已经通行,车站装磺的美丽,买在可与皇宫相比。车辆非常舒服,街上的汽车要比十年前增加二十倍。除公共汽车、电车外,还有元轨电车。
红场边的合作社,现在改造为列宁博物馆,范围非常宏大。
莫斯科的商业非常兴旺,新的大商店很多,但是无论什么时候,商店中的人都非常拥挤。今日领护照、买车票,一直忙到开车,下午两点钟,在北火车站搭第二号西伯利亚快车离莫斯科。苏联--再会!”'8'
中苏交通,还是十二年前的老路线,经陆路横穿西伯利亚,到海参崴改乘邮轮去上海。
火车过了伊尔库次克,东方色彩,愈来愈浓。贝加尔湖旁纪念苏武的神龛,凭吊低回,思念故国之情,油然而生。远眺湖景,绿波荡漾,水天一色。车箱穿越湖滨岩石下的山洞,宛延曲折,明暗交替,倍增情趣。
赤塔到海参崴,须绕道阿尔穆省,道经海兰泡,山路崎岖,车辆使劲地爬,穿插在浓雾晨曦间,颇有云山飘渺的意境。
海参崴,市面已较当年繁荣,这是苏联远东的门户。
中国官员的阿谀馅媚,早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的。驻外使领,岂敢怠慢这位荣归的蒋委员长的公子。权世恩总领事,奉到蒋大使的飞电,非但亲迎,且花了两万卢布的巨款,隆重接待。
这一路风光,工人出身的蒋方良,过去耳闻,目见是首一次。经国自己,旧地重返,感受不同,快乐的心境则一。
方良初次离国,新奇刺激,对她生于斯长于斯的苏联,并无依恋,她憧憬着的是一个新天地。
轮船先靠香港,蒋纬国奉命专程南下迎接。'9'一九二五年,在广州分手,他才九岁,现已是二十一岁的小伙子,经国比他大六岁,这年二十七岁。嫂嫂俄国人,大家语言不通,但侄儿侄女,好漂亮的中俄棍血儿。
弟兄俩,久别重逢,有说不完的家常。从纬国嘴里,才知道,蒋先生于一九二七年的十二月,和宋美龄结了婚,阿姆陈洁如,被安排送到美国,停留五年,重返上海。毛夫人姚夫人仍居奉化乡间。
四月中句,一行抵达上海,这里有他的旧居,以及一些美丽童年的痕迹。
上海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改变,黄浦江浑浊的江水,依旧悠悠地流着,江海关楼顶的巨钟,照常钟声悠扬。各国租界林立,帝国主义的势力有增无已。
沪上稍停,即去南京,'10'拜见父亲和美龄女士。传说,蒋生先等了两个星期,才传谕会晤,原因是,对他在《真理报》发表的公开信,颇难鉴谅。后来,还是陈布雷进言缓颊,始子宽恕。
问到儿子的打算,经国表示,愿在政治、工业间,任择其一。
经国提到工业,可以产生两个解释:他曾经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不愿意为自己的出处,使得蒋先生过分为难,此其一;凭他在苏联工厂的实地经验,真心诚意地为祖国的工业建设,尽其绵薄,此其二。
人与人间的关系,环境是最大的主宰。即是亲如父子,也不例外,父王和太子间,一牵涉到权力政治,就好象隔着一层城墙似的。大家都会言不由衷,说话要带过门,互留余地。
经国很技巧地提出他未来的出路。蒋先生功于权术,自然,不会不心领神会。父子这场心战,留下伏笔,但没有结论,蒋先生吩咐,先去奉化,看看阿娘,休息休息再说,来日方长。
经国夫妇,从南京去杭州,特由军委会机要室主任毛庆祥中将陪同,下榻西子湖边的澄庐,挑他生日那天,返乡与毛夫人团聚。
夏明曦刊在香港《大公报》的一篇文章,记载生动细致,值得抄录。
“在溪口,这一天,丰镐房里汇集了众亲百眷,熙熙攘攘,热闹盈门。帐房间里的电话铃声,从早到晚,响个不绝,是杭州来的专线报告。溪口街上,更是人来人往,热闹异常。标语横额,张贴满街;工商界的人做好红条纸旗,置办鞭炮,准备迎接蒋公子还乡。
电话一个接一个,报告说,汽车从杭州出发了,沿着奉新公路驶来。陪同来的是溪口人毛庆祥。
下午二时,人们在‘上山’洋桥那边列队迎候,一辆漂亮的雪佛蓝小汽车远远地从西驶来,由远而近,车中坐着蒋经国、方良、爱伦和毛庆祥四人(连孝璋在内,应为五人)。车近洋桥,便缓缓而驶,人群一拥而上,口号与鞭炮齐鸣,直闹得震天价响。
汽车驶到丰镐房大门口停下,这里,舅父毛懋卿和姑丈宋周运、竺芝珊等人率领一批长辈在门外等候。相见之下.悲喜交集,连忙拥着外甥、外甥媳妇进入大门,直往内走,毛庆祥本来就是溪口毛家人,驾轻就熟,也陪着小主人循着月洞门径自走进去。这丰镐居本是蒋经国的出生之地,幼时奶娘、嬉戏均于此,自然是熟悉的,但现在反主为客,任人安排,一切都感陌生了。原来当他离家时,老家只几间古旧的木结构楼屋,如今经过一翻修缮、扩建,粉壁画柱,面貌大变。这一切,怎么不使这位离家日久的小主人兴‘华堂春暖福无边’之感呢?”'11'
安排和一毛福梅母子见面的那一场,很有点古代章回小说家的笔法,夏明曦说:
“她们决定让母子相会的地点在吃饭的客厅,为了试试儿子的眼力,她们坐着十来个人,让经国自己来认亲娘。
在客厅里,现在坐着的是十来个壮年和老年女人,这就是:毛氏自己、姚氏怡诚、大姑蒋瑞春、小姑蒋瑞莲、姨妈毛意凤、大舅母毛懋卿夫人、小舅母张定根、嫂子孙维梅以及毛氏的结拜姊妹张月娥、陈志坚、任富娥等。大家热情洋溢、兴高采烈,等待经国来认娘。
人们簇拥着蒋经国、方良和爱伦,走向客堂间来,内外挤满了人,当经国等人一入门内,空气顿时紧张起来。
这时的蒋经国一步紧似一步,一眼望见亲娘坐于正中,便急步踏上,抱膝跪下,放声大哭!方良和爱伦也上前跪哭!毛氏早已心酸,经不住儿子的哭,也抱头痛哭!一时哭声震荡室内,好不凄楚!经众人相劝,才止哭欢笑。毛氏对大家说:‘今天我们母子相会,本是喜事,不应该哭,但这是喜哭。’
第三天,丰镐房里桂灯结彩,宾客盈门,喜上加喜。原来蒋经国孝母情重,为讨娘欢喜,遵循澳口乡俗,补办婚仪。
礼堂就是他家的‘报本堂’。他们的婚仪,完全老式:新郎蒋经国,身穿长袍.黑马褂,头戴呢帽:新娘方良凤冠彩裙,一如戏台上的诰命夫人。‘报本堂,里灯烛辉煌,伏猪伏羊,丝竹大鸣。行礼如仪,一拜天地、二祭祖宗、三拜父母。‘礼毕,鞭炮齐放,锣鼓喧天,送入洞房。
溪口风俗,凡是在外完婚之人,回到家里均要‘料理礼水,,即置办酒席请同族吃酒。蒋宅不能免俗。这一席喜酒,足足办了四、五十桌。毛氏嘱咐总管宋涨松(表侄)说:‘凡亲朋众友所送礼仪,一律不收,长辈茶仪受之。’
丰镐房一连热闹了五、六天,待众亲百眷散去,这才静下来,进入正常的生活程序。”'12'
溪口的母子会,那份天伦之乐,曹聚仁论说更活泼传神:
“他的归来,对于毛太夫人是极大安慰,她捞到了一颗水底的月亮,在她失去了天边的太阳之后。这位老太太曾经为了她的丈夫在西安遭遇的大不幸,焚香祈祷上苍,愿以身代。她相信这点虔诚的心愿,上天赐还了她的儿子,她一直茹素念佛,在那老庙里虔修胜业。她对着这位红眉毛、绿眼睛、高鼻梁的媳妇发怔。可是,那个活泼又有趣的孙女,却使她爱不忍释。这位洋媳妇就穿起了旗袍,学着用筷子,慢慢说着宁波话来了。那个夏天,他们这一小圈子,就在炮火连天的大局面中,过着乐陶陶的天伦生活。”'13'
蒋先生让经国回到溪口,有着很多层的作用。溪口非常安静,慢慢地经国可以从容不迫地修心养性,慢慢熟悉周围的环境,由调整而适应。若放在南京,他自己日理万机,焦头烂额,没有时间去照顾儿子,又怕和后母宋美龄合不来,引起误会和不安。而和毛夫人一起居住,可以使经国尽点孝,让她冷寂的心灵,因而有失夫得子的慰藉。
蒋先生心目中的儿子,在苏联期间,已中毒甚深,他自己奉曾国藩为稀世圣贤,恨不得经国也父规子随。经国回忆着:
“我回国以后,父亲要我读《曾文正公家书》和《王阳明全集》,尤其对于前者,特别注重。父亲认为曾文正公对于子弟的训诫,可作模范,要我们体会,并且依照家训去买行,平常我写信去请安,父亲因为事忙,有时来不及详细答复,就指定曾文正公家训的第几篇代替回信,要我细细去阅读。”'14'
经国经过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长时间的陶冶,口头上怎么保证,蒋先生还是不会怎么太放心的。国民党的字典里,虽然找不出“思想改造”这个名词,却并非说,国民党人压根没有使用过。经国没有进汤山中央训练团,但是这个吃力的任务,却是在蒋先生的遥控下进行的。
经国说:“父亲因为我童年就已出国,而在国外时间又太久,怕我对中国固有的道德哲学与建国精神,没有深切的了解,所以,又特别指示我研读国父遗教。”'15'蒋先生的意思:“孙文学说一书,实为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三民主义则为中国哲学的具体表现。”说穿了,蒋先生要洗经国的脑,要把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清除得一干二净。
那份“旅俄报告”,用共产党的术语来说,就是经国的思想总检查。只是程度有差别,能满足一下蒋先生的歇斯底里,也就可以顺利过关了。
帮助经国读书的担子落到徐道邻身上,徐担任过江苏省民政厅长,奉到蒋先生电召,荣拜“太师”。
蒋方良中文一窍不通,总不是办法,需从头学起,请位慈溪籍的女老师,教她学中国语文。
为了讨媳妇的欢心,在剡溪之边,文昌阁之下,特建洋房一幢,(16)供小俩口居住。
另一个陪伴太子读书的,是经国莫斯科的同窗好友高理文。曹聚仁说:
“‘他姓高,个子很矮,湖北人,说话很尖很急。’从莫斯科回国以后,‘跟陈铭枢一伙人(十九路军)交谊很深,福建人民政府的要角。’后来,在赣南时期和上海打虎时期,高是经国的得力助手,可是,‘古来侍君如侍虎。到了台湾,就被永远藏到中信局的冰冻拒里了。’”'17'
奉化舒适安祥的生活,持续经年,中日战争虽于次年七月在河北的芦沟桥点燃,中国被迫进入全面抗战,从事保卫国土的圣战。华东地区尚能苟安一时,直到第二年,去江西赣州,他的隐士生活始告结束。
注释:'1'罗勃…C诺斯著《莫斯科与中共》,香港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一九五六年出版。
'2'距西安三十公里,蒋夜宿骊山,在此被捕。
'3'莫斯科回电指示:“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介石作友善的商谈,促使其赞成抗日,并在有利和平解决的甚础上.自动将蒋释放。”杜桐荪著《谁教斯大林说话的》,《论坛报》第76期。杜说陈立夫曾通过第三国际代表潘汉年致电斯大林,杜肯定斯大林主张放蒋,是陈立夫的“一句话”,乃过分高估陈的影响力了。
'4'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三册,第1245页,香港《明报月刊》出版
'5'蒋廷黻著《出使莫斯科》台北《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