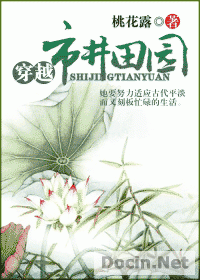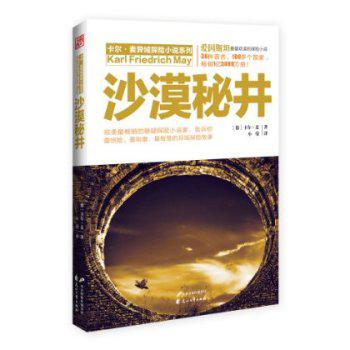梆子井-第1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且说张凤莲整天带着居民们在吴茂山的院子学唱“语录歌”。她起劲地打着拍子,像燕子似的挥着双臂,可是,居民们却怎么也跟不上拍子,你唱你的我唱我的,歌声参差不齐。刚唱了两天,李翠仙就说起奶奶了:“陈寡妇唱歌跟说歌一样,光见嘴动弹不见声音。”于是有一天,邵主任站在了奶奶身边:“你这到底是唱歌呢,还是念网生呢?”奶奶的网生念得很好,前不久邵主任的丈母娘死了,请奶奶去念了一天。她嘴里念念有词,坐在那里就念个没完,至于究竟念些什么,直至今天我也不清楚。“都把声音放大些!”邵主任也打起了拍子,吴茂山的院子响起一片杂乱的歌声:“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条:造反有理!造反有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把这几首歌也试着唱了一下,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歌,充其量不过是嘶嚎,这样的歌也许谁都唱不好。
吴茂山的院子呈方形,这也是居委会常在这里开会的原因。吴茂山住在后院,他的那间上房从前院看只露一个屋顶。而以前呢,这间上房也象我家的上房一样,是上下二层的。听说今天这个样子,是吴茂山儿子的主意:“跷跷者易折,皎皎者易污。房子盖得那么高只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进而招致不必要的麻烦。”由此我想到奶奶的遭遇,可不都是因为房子盖得太高了吗?实际上,奶奶现在还有什么呢,经过这次洗劫,怕只剩下这所房子和一些不成垃圾的破烂了,但是,只要这所房子在,就还会有人打你的主意!
李翠仙还时不时地扒在墙头张望,真不知道她现在还张望什么?孙喜凤见了奶奶总要骂一句:“资本家太太你嚣张啥呢!”而奶奶总是在街上匆匆走过,一言不发也不理她。有一天她竟然在后面说:“装没听见呢,我把声音再放大点儿——资本家太太你嚣张啥呢!”她的声音整条街都能听到,可是奶奶仍然没有听到。奶奶的这个样子和李玉梅有点相象,李玉梅总是这样在巷子里悄悄地走过,脸上甚至也没有丝毫的表情。也许现在,她终于露出欣慰的笑容了?
不知怎么,我常常怕奶奶发生那样的意外:“奶,你走到街上一定要注意呢,见了车你就躲得远远的。”“俺娃,你是越来越懂事了。”奶奶摸着我的头说。我也觉得,我比原先懂事了许多。如果家里不发生这些变故,我还会象以前那样稀里胡涂地活着。现在,我常常静下心来思考:奶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遭遇呢?固然家里房好是一方面,但是家里没人也是一方面。房好又没人,这怎能让人不想呢?如果我家也有一个象吴茂山儿子那样的人,也许状况会有所改观吧?
不久,二舅来了一封信,说他很快要调回来了。二舅在邻省的一座小城工作,是大学毕业分到那里的。虽说在外地,可工作环境和条件还是不错的。现在因为家里无人,他就要调回来了,我和奶奶都为此高兴。“你二舅一回来,巷子也就没人敢欺负咱了。”二舅不象大舅,他遇事沉着冷静,能够看到事情的全过程,而大舅却只看到表面看不到深层次的东西。你比方,他打李翠仙一个耳光的事情,实际上,李翠仙只是一个幕前人物,你打她也许能给她一定的威慑,但是,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吗?怕只能加深她对奶奶的仇恨。象我和奶奶目前这种情况,就如我们住的房子一样,是在夹缝中生存的:首先大环境和大气候对我们是不利的——这点,也许谁也改变不了!但是,如何使小环境小气候变得温和一些,至少张凤莲她们不再象以前那样与我们尖锐地对立了。这,也许就是一个策略的问题了。而这一点,我想二舅是可以做到的,所以我急切地盼望着他回来。
然而这个过程却是如此地漫长。眼看着天渐渐地冷了,六七年的日历也就要翻完,可是二舅的回归却杳无音信。二舅没有消息,街面上却不断有武斗的传闻。这一年来,古城的造反组织已分化为两大派别:一派是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一派是工人造反联合会,简称“工联”。这两个造反组织既不是信仰之争也不是争地盘,他们都标谤自己是造反,诬对方是保皇。虽然毛主席一再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可这两个工人组织却闹得不亦乐乎,从相互谩骂渐渐发展到了武斗。古城的东郊和西郊散布着一些兵工厂,里面的产品也很快被当作了武器,于是,武斗也就上升为真枪实弹的较量,不断传来有人被打死的消息。
奶奶一再地叮嘱我:“你千万不要到街上去,街上太乱,你就呆在院子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活动的范围也相应在增大,这个院子已经不能容纳下我了。听说,西门城楼上就架着机关枪,西门盘道也被铁丝网堵了。奶奶说:“刘振华围城的时候就是这样。”因而,我的活动范围也只能是梆子井了。
而梆子井也相对地显得安静。这期间发生的变化,不过是一些新住户陆续地搬来,而老住户还呆在各自的院子里,新户和老户也能够相安无事地在这块天地间生存,外界的骚动似乎对梆子井影响并不大。但是孩子们之间却在默默地发生着变化——梆子井的孩子们竟然也演化成了两大帮派。一派是以三娃子为首的所谓的“正宗梆子井”派,一派是新住户天财领导的“外来户”派。天财来梆子井之前住在道北一带。那里本是一片贫民区,他们也是城市的边缘人。可是现在,你看,他们竟挤挤挪挪地挤进古城的腹地来了,挤进我们梆子井来了!这本就是我们所不能允许的,而他,竟还要在我们中间作“大”!你凭什么呢?我们在梆子井玩儿的时候你还在铁道边捡破烂呢!如今,才来了几天,就把自己姓什么叫什么全忘记了,就要对梆子井的孩子们发号施令。而要达到这一点,象他这种情况,必须在梆子井默默无闻地呆上一阵儿,然后视你的能力和资历一步步攀升到这个位置。这本是一个社会的通用法则,你天财也不能例外!
但是,他却带着那一帮外来户的孩子们在梆子井横行无忌。梆子井的孩子们如果单个出来,他们不是怒目相向就是拳脚相加,这无疑是日本鬼子到了中国!任何一个有正义感的梆子井人都不能容忍这种现象的发生,于是,我们也就自然地团结在了三娃子周围。三娃子能当我们的“王”,也并非我们的本意。三娃子在梆子井傲气日盛,随着他妈地位的显要,他在孩子们中的地位也不断上升。但是他妈在梆子井又是个什么形象呢?正如喜子所说:“他妈在巷子名声不好,让他当咱们的头,也不是咱的心愿。”然而,“大敌当前”,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况且三娃子根正苗红,正宗的工人阶级子弟。试想,如果让我这个资本家的外孙子当孩子的王,在对付外来的孩子们时我们的威力就会减少许多,这无疑是一个致命的弱点,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还真有点舍三娃子其谁也的形势,况且喜子又甘当“狗头军师”。喜子这个人鬼点子多,但是家里的成份也不是很好,小业主,他爸也不明不白地死了。因而在推选孩子王的时候,他主动让贤给了三娃子,“我不行,我光给咱出主意。”他说:“三娃子当咱的头没啥说的。”而像我这种“地富反坏”的子弟,也自然“没啥说的”。你凭什么竟选孩子王呢?“人贵有自知之明”,你家里是个什么情况,你自己心里最清楚,能让你当个走卒已经不错了。就这样,三娃子既有他妈的权势作靠山,又有喜子这样的人摇鹅毛扇子,还有一群老户的孩子作走卒,一时间竟和天财领导的那些外来户们分庭抗礼,形成了两大营垒!
梆子井的孩子自从有了三娃子这杆大旗,就像一盘散沙有了磁石、漫流的水入了河道一般有了凝聚力。我们紧紧地团结在三娃子周围,天财他们再也不敢小瞧我们了,那种动辄动手的现象绝迹了,甚至连侮辱我们人格的话也听不到了,两大营垒渐渐地趋于了平衡。
与此同时,社会上那两个工人组织也势均力敌。“工总司”的势力范围主要在东郊,“工联”则控制着西郊一带。那些大规模的械斗都发生在郊外,而四门内的市区却成了一个真空地带。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地”内高喊:“你们要保皇,我们却要将造反进行到底!”究竟谁保皇谁造反,就是包青天活转来也未必能分清!
我固然不敢去郊外,但有时也上街看看。这天,我来到西大街,发现“工总司”和“工联”的人正对峙着。“工总司”的人站在东边,个个拿着棍棒,戴着头盔,还有一个精心制作的盾牌。盾牌很大,从正面看,几乎看不到人,盾牌下却露出了棍棒——全是铁的!这种场面颇像古代战场的阵势,这两天我正看《三国演义》,一下子兴趣大增,站在路边袖手旁观了起来。不一会儿,汽水和啤酒瓶子就飞了过来,乒乒乓乓地砸在了盾牌上。“工总司”的人手持盾牌,两条腿坚定不移地前进,嘴里喊着:“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和保皇的工联血战到底!”因而瓶子真正砸到的并不是他们,而是我们这些看热闹的人。小孩儿的头被砸破了,哇哇乱叫,妇女抱着孩子惊慌地穿过大街小巷。商店的橱窗被砸烂了,店员趴在柜台下面,像躲避空袭似的不敢露头。于是汽水和啤酒瓶子又源源不断地运了出来,砸了过去!
我躲在一根电线杆后面,突然,上面的碘钨灯“爆”的一声,象原子弹爆炸似的腾发出一片烟雾,那些玻璃的碎片灌进了我的脖颈。但是眼前的对峙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工总司”的人迎着“弹雨”义无反顾地前进;“工联”的人虽然不断地将酒瓶和砖头扔过来,却步步退却,最后发一声喊,作了鸟兽散,“工总司”的人立刻放下盾牌欢呼了起来。我终于看到了现代武斗抑或古代战争的场面。但是喜子说:“这算个啥吗!明儿你和我到西郊去看看,那才叫真正的武斗!”“我可不敢去,我的胆量只能看这样的场面。”但是他说:“那不是武斗,是个展览。”“什么展览呢?”“打死人展览。”竟然有这样的展览!于是我和喜子去了。
'网:。cc'
第十三章
更新时间:2009…5…12 12:04:49 字数:7550
第十三章
在此之前,也听人说过,西郊打死了多少人,东郊又打死了多少人,但是却从未见过。真不知那些被打死的人是什么样子?听奶奶说,暴死的人一时半会儿是进不了阴间的,阴间的门也不是对所有的死者都敞开着的。只有那些寿终正寝,并且在世上没有做过什么坏事的人,才能一帆风顺地进入冥界的大门。“你好比李玉梅吧”奶奶说:“她现在怕才到奈何桥呢,阎王让她进不进门还难说呢。”这我就有点不懂了,李玉梅虽不是寿终正寝却从未做过坏事,就是那些被打死的人也未必做过坏事,为什么阎王……难道冥界的清规戒律就那么多吗?“你不懂,”奶奶说:“人活着就是图个好死。”我想,也许正因为如此,奶奶才不愿非正常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吧,尽管外界已经不止一次地迫使她那么做!当然,好死不如赖活着,而赖活着又是图了个好死,这其中的辨证关系我不能理解,但是,活着就能经世事,就能看到一些千古奇观。你比方我吧,小小年纪就看到了武斗的场面,现在又要去看“打死人”展览了!
我和喜子出了西门。西门并不是那么容易出的,一个手持棍棒、臂戴红袖章的小伙子拦住了我们:“上哪儿去?”“找俺哥看展览去!”喜子的哥哥在西郊。“小小个娃看啥展览呢,赶快回去!”棍子在喜子的屁股上拍了一下。“看,我是红卫兵!”喜子蓦地掏出个袖章:“小小的就造反直到现在了!”小伙子扑哧一笑,竟放我们出了城。
公共汽车是一辆也没有,工交公司属于“工联”。上个月车开到东郊,竟被“工总司”的人掀翻了,司机被暴打了一顿,售票员是个女的,还被扒光了衣服。说是工联的车只能往西开不能往东开,因为东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现在是西边也不让开了——工交公司已经停业了好长时间。
“没车就没车,咱们走着去!”喜子说:“整天呆在梆子井都快把人憋死了。”说着,他竟深深吸了一口郊外的空气。是的,梆子井牙长个地方,孩子们又无聊得很,整天搞恶作剧。尤其是那些新来的孩子们,见了人就给个中指,嘴里骂一些带河南腔的污言秽语,空气真是憋闷得要死了!而我和喜子又整天跟在三娃子的后面,这并不符合我的性格。总之,出来走走,对我们只有益处没有坏处,况且,郊外的天是多么蓝啊,空气又是多么的清新。虽然墙上贴满了标语,但是那绿油油的菜籽花依然散发出诱人的清香。
喜子的哥哥在一家军工厂,据说是做被服的,可是现在,又是个什么样子呢:几辆卡车堵住了厂门,卡车上全放着棺材。两边站着一些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头上缠着白布,手里拿着棍棒,真不知他们是要埋葬死者呢还是要继续武斗?这种情形不像是出殡,倒像是拉着死者向市民去示威。大门旁的门柱上贴着毛主席的诗词:“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围墙上贴满了黑色的标语:“十二八烈士永垂不朽!”“烈士的鲜血不会白流!”“化悲痛为力量,誓与工总司血战到底!”“要革命就会有牺牲!”等等等等。看来工人阶级内部冲突还不小呢!
一进厂门,一幅巨大的横幅挽幛一直扯到了参观点,内容与外面的大致相同。参观点设在一个腾空的库房里,库房很大,但尸体却胡乱地摆在地上,这与外面的庄严形成鲜明的对比。令人不解的是,大部分尸体都裸露在外,但也有一二具用白布蒙着。裸露的尸体皆面目狰狞,血肉模糊;那些血迹已经发黑变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