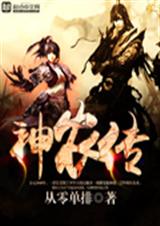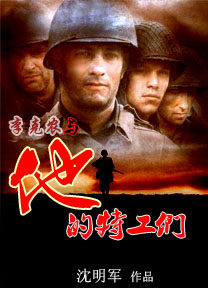李克农传-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结果,两个人在走廊上扭打了起来。李克农的眼镜被打掉在地。闻讯赶来的同志急忙拉开,作了介绍,李克农和陶铸二人正在狼狈不堪之际,一经点破,不由得都“哈哈”大笑起来。
这段时间,李克农工作很顺利,心情也很愉快。因为这时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最好时期,在中共全面抗战的旗帜下,武汉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波澜壮阔,长江局和武汉“八办”一起,积极领导、组织和推动民众爱国运动的发展。
1938年7月7日,为筹集钱物,支援抗战,以实际行动纪念抗日战争爆发一周年,在以郭沫若为厅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的具体组织下,武汉地区掀起了群众性的“献金”热潮。为吸引群众,三厅在武汉三镇设立了五座固定献金台,每座献金台都由一位要人的夫人作台主,另外还有三座流动献金台,设在卡车上,进行流动献金。
中共代表团和武汉“八办”代表到江汉轮渡口献金台参加捐献,这里的台主是国民政府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女士。由于李宗仁在3个月前,指挥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现在又是保卫大武汉的主力部队指挥官,因而,郭女士的出现,更加引人注意。上下轮渡的人群,自动集中到献金台前,纷纷捐钱。中共中央驻武汉代表周恩来献出了自己担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一个月的薪金240元;王明、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等,除代表中共献出1千元外,又各自献上250元。李克农也来了。他首先代表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交上公函一份,并献现金1千元。公函上写着:
顷奉朱总司令自山西来电,嘱将八路军在“七七”抗战建国周年纪念日素食所节省的全部菜费1千元,代献作慰问抗战军人家属及救济被难同胞之用。
接着,李克农把叶剑英、钱之光、李涛、罗炳辉、边章伍和自己一个月的薪金也献了出来。
“八办”的其他工作人员———童小鹏、廖似光、龙飞虎、巴方廷等,也献出自己一个月的薪金。
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群众,以热烈的掌声来表示对这些民族精英的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
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望日见提高,蒋介石则忐忑不安,心有余悸,他命令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严加防范。
戴笠,号雨农,小名春风,1896年出生于浙江省江山县。民国初年,他混迹于上海交易所,结识了蒋介石、戴季陶、陈果夫等人。起初,他们视戴笠为小瘪三,让他干一些跑跑腿、送送茶水之类的杂务。后来,戴季陶打听到他姓戴,又是自己的浙江同乡,便对他多了一份关心。
一次,戴季陶问他读没读过书,以后想干些什么。
戴笠看到蒋、陈等人不似普通人,今后必将会在政坛上有所作为,便答道:“青年人要干,就要像陈英士、徐锡麟一样,干得轰轰烈烈。我受过中学教育,当过团丁当过兵,现在打流(指找不到职业,到处流浪)打到上海来了。”
一席话说得戴季陶对戴笠另眼相看起来,戴笠也相机老于世故地改口称戴季陶为戴叔叔。蒋介石见戴季陶器重戴笠,以后也吩咐戴笠干些事。
戴笠幸遇蒋介石,改变了他一生的经历。而他以后的发迹,也得力于蒋介石的大力提拔。
赴武汉车站智截叛徒
1938年4月上旬的一天,周恩来把李克农叫到办公室,交给他一个重要的任务,去武汉火车站迎接一位神秘人物,而且,必须迎到,不能空手而归。
这位神秘的人物是谁?———张国焘。
张国焘,江西萍乡人,1921年出席过中共“一大”,是建党的12名创始人之一。1930 年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1年回国后,先后担任过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副主席等职,领导红四方面军和国民党军作战有过战功。然而大浪淘沙,泥石俱下,1935年6月红军长征途中,身为红军总政委、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他,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竟然无视中央北上决定,擅自率领红四方面军向川、康地区退却,并在卓木雕非法另立第二“中央”,企图分裂党、分裂红军。在陕北,为挽救张国焘,中共中央仍然任命他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但此时的张国焘,虽然口头上承认了错误,内心却早已和党同床异梦,插翅飞往武汉蒋介石身边去了。
1938年4月4日,正是中华民族思亲祭祖的清明节,为表合作抗战之决心,国共双方约定派代表去陕西中部县(今黄陵县)合祭黄帝陵。国民党政府代表是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而中共代表则是张国焘。
祭陵完毕,张国焘撇下秘书和警卫员张海等人,一头钻进蒋鼎文的小车直奔西安。张海负警卫之责,只得跟着后面西北行营宪兵队的汽车,同往西安。
在西安,张海打听到张国焘已经住进了国民党高级招待所———西京招待所。
两天后,张国焘买好了去武汉的火车票。上午临上车前,张国焘让张海打电话告知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林伯渠。林伯渠闻讯速往车站,对张国焘不经中央批准、擅自行动给予了批评。张国焘煞有介事地说:“我到武汉,是同蒋介石面谈统一战线问题,今天就得去。”
林伯渠劝阻无效,见事已至此,当即指示张海随同前往。回到办事处后,林伯渠马上电告中央,同时又和武汉的周恩来取得联系,告诉张国焘去武汉的车次和时间,要武汉“八办”派人好好“迎接”。
任务交给了李克农。
周恩来告诉他,一定要在武汉车站截住张国焘,然后做工作说服他,希望他留在党内,不要做出叛党的事来。最后周恩来加重语气说道,这也是中央的要求。
李克农受领任务后,深感责任重大,反复考虑万无一失的行动方案。他与吴志坚、童小鹏、邱南章等商量,万一遇上国民党特务阻拦甚至劫持怎么办?对,带上手枪。4月8日上午,武汉大智门火车站。
一列列火车南来北往,上下火车的人流熙熙攘攘。两辆小车驰进火车站,李克农带着总务科长邱南章、童小鹏和吴志坚等四人,从车上走了下来,径往各个出口,等候张国焘“大驾光临”。西安发出的列车来了。他们警觉地打量着每一个下车的旅客。不料,旅客都走光了,张国焘那又白又胖的身影,始终没有出现。“是不是在车上没下来啊?”童小鹏问道。
李克农想了一会儿,说:“好吧,小鹏你在这里盯着,我们三人到列车上看看。”说罢,三人跳上了车。
三双锐利的目光,沿着车厢挨个搜索,终于,在靠后的一节车厢里,找到了张国焘。
张国焘斜躺在座位上,歪着脑袋,一副无精打彩的样子。张海已被特务缴了手枪,坐在对面。两边紧贴着两个国民党便衣特务,鬼鬼祟祟,像是在等人来接应。
邱南章走上前去,很有礼貌地说:“张副主席,你来了,李秘书长带着两辆小车来接你,周副主席请你到办事处去住。”张国焘猛然看见李克农一行,他深知李克农来此的用意,脸一沉,色厉内荏地说:“我不要他请,我来武汉是有事的,我有地方住。”说完,急忙跟着两个特务往车下溜。
李克农见状,不便强迫,因为张国焘职务还在,只得叮嘱邱南章说:“你和吴志坚一定要跟着他,我们先回去向周副主席汇报。”李克农向周恩来汇报后,又迅速找到张国焘。由于李克农的劝阻和邱南章、吴志坚等人的严密监视,张国焘一时间毫无办法。他气急败坏,却又无计可施,只得表示同意由武汉“八办”安排住处。不过,他死活不愿住在办事处内,最后安排住进了太平洋饭店。
张国焘泄密
为防张国焘向国民党泄露中共机密,李克农悄悄地让张海将他的行李搬到了“八办”,很可能,里面装有中央重要机密。果然,张国焘投靠国民党后,还派人到“八办”要过行李,这,当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4月17日,周恩来接到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他找来张国焘,严肃地对他说:“中央的意见有三条:一、改正错误,回党中央工作,我们最希望是这样。二、可以向党请假,休息一段 时间。三、自动声明脱党,否则宣布开除你的党籍。”张国焘听完,面无表情,初衷不改。
当晚11点左右,在国民党军将领胡宗南手下一伙特务的协助下,张国焘仓皇逃离住所。
张国焘就这样背叛了中国共产党。
第二天,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开除张国焘党籍。
张国焘出走后,负责监视的邱南章立即电话告知李克农,并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周恩来冷静地说:“张国焘不思悔改,迟早是会走上这条路的。”张国焘投靠国民党后,被安排进入军统内部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主持工作。特务头子戴笠对张国焘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只盼着张国焘能利用自己过去在共产党里的地位和关系,对中共的组织进行一次大规模的阴谋活动。
张国焘提出要办一个训练班,由他自己亲自培养对付共产党的专门人才,戴笠马上为他挑选人马;张国焘说要在陕甘宁边区设立一些策反站,戴笠马上按照他的计划办理。总之,张国焘要人给人,要钱给钱,一时成了戴笠手中的红人。
哪知一年过去了,张国焘的计划无一兑现:训练班毕业的学生分配无着,只办了两期就停止了;而策反站呢,由于中共严加防范,成绩几乎等于零。张国焘束手无策,戴笠则大发脾气:“这家伙(指张国焘)太不知好歹。他不要以为就这样,可以对付得过去!”这以后,军统原来给张国焘的一些优待也渐渐取消,连以前配给张国焘的一辆专用汽车,也被收回。
一位熟知张国焘的军统人员暗地里为张国焘“鸣冤”:“戴笠骂张国焘不肯为军统卖力,实在是有点冤枉。他连吃饭睡觉都在想办法,实在是因为共产党组织太严,防范太周密,所以做不出特别成绩来。”
张国焘在军统一直过着坐冷板凳的受气生活,时常摇头叹气,心情郁闷不堪。
1948年冬,张国焘逃到台湾,在台北租了一间房住下。由于此时的张国焘已失去了利用价值,国民党既不给他工作,又不给他生活费,甚至连房子也被国民党官员强占。1949年冬,张国焘携妻儿移居香港,化名“凯音”,参加了由顾孟余等人组织的所谓“第三势力”的活动,并投靠美国驻香港领事馆,贩卖一些过时的“中共资料”,以资糊口。
1956年,张国焘托人向中共中央捎话,表示想回大陆。中央转告张国焘,只要他能在报上公开承认错误,就可以回国。但这一要求遭到张国焘拒绝。
60年代,张国焘接受美国肯萨斯大学约请,用四年时间写出了一部90余万字的《我的回忆》,书中对中共历史和中共领袖进行大肆歪曲和诬蔑。肯萨斯大学在其写作期间每月给他二千港元的“研究费”。书稿先在香港《明报月刊》连载,1966年正式出版。这些稿费收入,就成了张国焘晚年主要的生活来源。1968年,张国焘、杨子烈夫妇由香港迁往加拿大多伦多。1977年,80岁的张国焘因患中风,生活不能自理。杨子烈将其送到教会慈善机关办的老人病院。1979年12月3日晚,张国焘因盖的毯子滑掉床下,又无人护理,冻死在床上,魂断异域他乡,时年82岁。
桂林“八办”
1938年8月以后,日寇以30万兵力沿长江两岸大举西进,黄梅、广济、九江、马当相继失守。10月,日寇从水上和陆路三面包围了武汉,武汉三镇危如累卵。
10月21日,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在《新华日报》上登载重要启事:本处奉命迁湘,凡一切信件及临时事宜,请至界限路(今合作路)44号新华日报编辑部接洽,电话号码为24886,尚希各界注意是幸。
这以后,武汉“八办”在周恩来的指挥下,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大搬迁。
10月22日下午,李克农和潘梓年率领“八办”和《新华日报》社的部分工作人员,乘坐租来的轮船“新升隆”号由长江撤离。由于该船吨位小,《新华日报》报馆的印刷设备和纸张把底舱全部塞满,李克农他们一百来号人坐在船上,显得异常拥挤。临行前,岸上忽然拥来几十名无钱买票的难民,送行的周恩来看不过去,也让他们上了船。这一下,这艘小船人满为患,严重超载,行驶相当缓慢。
10月23日,当船行至嘉鱼燕子窝附近时(现属湖北省洪湖县),突然遭到4架日机的袭击,“新升隆”号被炸起火。碰巧李克农和夏之栩等人上岸办事,得以大难不死。当他们返回时,船体已被淹没在水中,江水顿成血色,四周哭喊声震天动地。
“八办”工作人员张海青、赵兴才、徐挺荣等人和《新华日报》社的工作人员共16人遇难。李克农强忍悲痛,一面安抚和救济脱险的群众,一面组织和鼓励幸免于难的同志们,振奋精神,继续前进。
李克农一行辗转长沙、衡阳,于11月中旬到达桂林。李克农到桂林,是奉中共中央的命令,就任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处长一职的。早在1938年8月至9月间,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就作出决定:武汉失陷后,在重庆、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为此,“八办”副官刘恕,偕同党外友好人士熊子民被派往桂林进行筹备。
刘恕到桂林后,先是租用桂北路138号“万祥醋坊”老板黄旷达的一幢两层楼房作为办公用房,以后又在城北灵川县路莫村和金家村,租用了几间农民房屋作为电台、仓库和接待站。
10月25日,周恩来在撤离武汉到长沙的路上,巧遇国民党副总参谋长、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周恩来告诉他,中共将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已派李克农担任主任(即处长),请白允予协助。白崇禧当即答应。这样,国共双方实际上就中共在桂林建立办事处的问题,达成了口头协议。
李克农率领大批人马抵达桂林后,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就正式开始了工作。桂林“八办”对外的名称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桂林办事处”或“第十八集团军桂林通讯处”。
桂林,一向以其秀美的山川、碧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