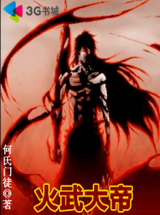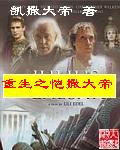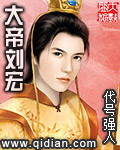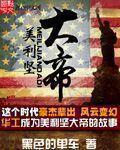永乐大帝-朱棣-第3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以工部尚书的身份巡视山西,结果,在走到泽州时病死 。
查继佐《罪惟录》的记载中,关于建文帝出亡的不同说法就有二十三种之多。因为没有确切证据,作为严肃的史学家,查继佐提出“十六辩”即“十六疑”,对它们一一加以辩驳,全部否定了。
帝子出走何事,而五六十人闻之,后此无一败?疑一。
鬼门可出,水关何必复导?疑二。
金川既启,廷臣惊惧不知所出,在外小臣安敢遽入大内?小臣能入而帝不能出?疑三。
兵势汹汹此何时?而神乐道士惓惓梦中之言,舣舟待命?疑四。
且二十二人信宿王升处也,疑五。
遯野亦多人,而必以为尽与帝周旋,疑六。
亡名者必诬之以名,疑七。
仲彬家吴,吴之人无踪迹取功名者乎?疑八。
得相聚,疑九。
革诰敕亦早,此系逆案,而邑丞之但身临史氏也,疑十。
既疑仲彬匿帝,必大索,能哂而去之,疑十一。
期襄阳胡遂弗后,疑十二。
一再迹云南,必晤帝,疑十三。
帝既目善冠盖,而万里复走仲彬者再,疑十四。
岂不闻胡濙之出,又奚乎天台?疑十五。
间关晤接,无他言,而琐及所献,疑十六。
面对种种疑问,最后,他说:
按出亡之说,传二十有三,岂无一真?惟传二十有三,乃信无一真也。真则一而已矣。即让皇之谥,本自“逊国”二字来。此实录之后,史家不得已,分例“逊国”,以与“靖难”埓。秉笔者不免说谎,数百世安之。却逊与让之义,犹然为出亡作解也。
查继佐的辩驳是在明亡之后。早在明万历年间,即建文逊国传说甚盛时,时人沈德符就有一番辩驳。他说:
建文帝出亡,当时倘令故臣随行,必立见败露。近日此中乃有刻《致身录》者,谓其先世曾为建文功臣。因侍从潜遁为僧,假称师徒遍历海内,且幸其家数度。此时苏嘉二府偪近金陵,何以往来自由,又赓和篇什,徜徉山水,无一讥察者?况胡忠安公(胡濙)之出使也,自丁亥至丙申,遍行天下,凡十年而始报命。观忠安传中云,穷乡下邑,无不必至。胡为常州人,去此地仅三舍,且往来孔道也。岂建文君臣能罗公远隐身法耶?所幸伪撰之人,不晓本朝典制,所称官秩,皆国初所无。且妄创俚谈,自呈败缺。一时不读书、不谙事之人,间为所惑。即名士辈亦有明知其伪,而哀其乞怜,为之序论,真可骇恨!盖此段大谎,又从老僧杨应祥假托之事敷演而成。若流传于世,误后学不小。又《传信录》云,宣宗皇帝乃建文君之子,传至世宗皆建文之后。此语尤可诧。盖宋太祖留柴世宗二子,及元末所传顺帝为宋端王合尊幼子二事,而附会之耳。乃不自揆,僭称“传信”,此与近日造二陵信史者何异?庸妄人自名为信,他人何尝信之?此皆因本朝史氏失职,以至于此。
6.感情代替了史实,政治掩盖了真相
对于明清以来出现那么多关于建文帝的传说,怎么解释呢?就神话或民间传说形成发展的规律而言;借用胡适先生的话:
凡故事的演变如滚雪球;越滚越大;其实禁不起日光的烘照;史家的考证。
关于建文帝传说的发生和演变是符合这一规律的。由于建文帝的下落不明,引起了人们的种种猜测和传说,而传说不断扩大不断丰富,越说越神,越说越圆。
和许多不断演化的传说一样, 关于建文帝下落的追寻,对于许多人来说已经远离了史学或学术,成了一种纯粹的感情牵挂。归纳起来:
(1)明初史家在政治高压和为尊者讳的禁忌之下,既不能批评太祖朱元璋,也不能指责明成祖朱棣,更无法记述事实真相。
(2)明人为伸张其政治抱负,对建文帝其人充满同情和思念,为寄托对建文帝及忠臣义士的怀念,宁可相信传说而不愿深究历史真相。为了宣扬忠君殉节的观念,甚至有意渲染并不存在的传说。
(3)清初史学家,或由于自身的经历或由于政治环境而回避事实真相。以遗民自居者,借建文史事寄托故国之思,反省明亡之痛;降附新朝的亡国二臣,身负骂名,岂敢再指那些宣扬忠节的书为伪书?
(4)旧史家在正统观念指导下,斤斤计较“书法”的长短,为了给统治者开脱,不惜抹杀事实,曲圆其说,比如,宣扬燕王继统出于朱元璋的有意安排,建文逊国是有意让位,朱棣入统受之无愧,等等。
还有,清朝在入关之初,也遇到了同样尴尬的局面。他们赶走李自成,声称为明朝报君父之仇。而崇祯帝自缢后,仍有儿子下落不明。清朝控制了中央政权,但反清势力仍然十分强大。一些反清复明的势力就奉朱三太子为旗帜反抗清朝。所以在当时,清廷力主朱三太子已死,绝不可能在民间躲藏,用此来断绝复明者的希望,以安人心。这同这同建文帝的生死一样,是政治问题。于是,清初的一些书写历史的馆臣体会当政者的意思,便主张建文帝焚死之说,以避免人们影射朱三太子。
7.不是结论的结论
关于建文帝的下落,仍可以用明史前辈王崇武先生的话:“官书曲解历史,野史漫无根据,皆非信史”因此,从明末王世贞、钱谦益以迄清初徐乾学、朱彝尊王鸿绪辈,皆思于此段史事有所考索,而其实甚少发明者,诚以史料缺乏故也。”在现在还没有新的材料发现之前,我们的结论是:
(1)建文帝不论是焚死还是出亡;不妨两存其说。
(2)即使建文帝真的出亡;传说中各种细节也都是不可信的。
下篇 一代雄主
一、靖难之役透视
一个好端端的江山,为什么发生了四年的战争?一个承平天子为什么被赶下了台?除了战争双方的个性不同,能力悬殊,用人各异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原因?不少论者都把靖难之役看做是皇室内的夺权斗争,并没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但在仔细分析靖难前后的史籍之后,不禁对这种说法提出怀疑。尽管由于永乐年间的禁毁,我们所得到的往往只是蛛丝马迹,而将这些蛛丝马迹悉心串联起来之后,我们就发现了一个非常广阔的背景。这不仅使我们能对“靖难”前后的政治变迁做出更深刻的判断,而且也使我们对建文帝和永乐帝的评价更为准确。
那么,就让我们来透视靖难之役。
要透视靖难之役,还应该从建文政治说起。建文君臣所推行的是一套与洪武截然不同的政策,他们变更祖法实行新政的思想是极为明确的。建文皇帝所倚重的大臣兵部尚书齐泰说:“《皇明祖训》不会说话,只是用新法便。” 这显示他们对祖宗旧制的蔑视和实行变法的决心。
我们先来看看建文前后刑法的变化。
建文帝长于深宫,自小接受儒家教育。各书均记载他“仁柔”、“孝友”,这种品格反映在他的政治生活中,则与朱元璋的严刑酷法相反。“太祖春秋高,中外万机,尝付帝(建文)裁决。时尚严覈,帝济以宽大,于刑狱犹多减省,远近忻忻爱戴” 。据说,朱元璋曾经以律授皇太孙,皇太孙“遍考经礼,参之历朝刑法志,改定七十三条,帝览竟,大喜曰:‘吾当乱世,刑不得不重。汝当平世,刑不得不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 。建文所改七十三条,内容如何,今已不可考。有人曾考证建文所改者是例而非律 。不过由严改为宽,大概是确实的。
建文即位,继续实行了宽刑的方针。他说:大明律“较前代律往往加重。盖刑乱国用重典,非百世通行之法也。……律设大法,礼顺人情,齐民以刑不若以礼。其传谕天下有司,务崇礼教,赦疑狱,嘉与万方,共享和平之福。” 这样做的结果是“罪至死者,多全活之。于是刑部、都察院论囚,视往岁减三之二,人皆重于犯法” 。因此,建文二年(1400年)诏曰:“顷以诉状繁,易御史台号都察院,与刑部治庶狱。今赖宗庙神灵,断狱颇简,其更都察院仍汉制御史府,专以纠贪残,举循良,匡政事,宣教化为职省。” 这一机构的改变是刑狱减少的结果。
洪武初,朱元璋曾说:“水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也。盖法严则人知惧,惧则犯者少,故能保全民命。法宽则人慢,慢则犯者众,民命反不能保,故守成者不可轻改祖法。” 因而,洪武时的情况是“用刑太繁” 甚至“无一日无过之人” 。后来,他虽说过“刑罚世轻世重”的话,但他的根本思想并未改变。洪武三十年(1397年),申刑法画一之制,“令子孙守之”,“群臣有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 建文帝衡破旧规,实行宽刑,是需要有些勇气的。建文二年九月,建文帝下令“赦流放官员,录用子孙洪武中以过误逮及得罪者,皆征其子孙录用之” ,“征洪武中功勋废误者子孙录用之” 。因而,在建文朝的官僚队伍中,有不少人是在洪武中遭到贬黜放废的人。这种措施是对洪武政策的实际否定,是一种平反。
我们再来看看田赋。
建文帝在即位诏中表示,要“诞布维新之政”,“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期致雍熙之盛”。 接着他下了一道包括赦死罪、宽刑狱、蠲逋租、赈灾荒的诏书 。每个皇帝上台,都照例要做一番冠冕堂皇的文章,而建文帝的诏书却不完全是例行公事,他确实想有一番作为。这年冬天,他又下诏赐明年田租之半。诏书说:“朕即位以来,大小之狱,务从宽省,独赋税未平,农民受困。其赐明年天下田租之半。” 建文元年正月,又下养老诏,命官赎民鬻子 。同年三月,诏均江浙田赋,人得官户部。诏书说:“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准私租起税,特惩一时之顽民,岂可定则以重困一方?宜悉与减免,照各处起科,亩不得过一斗。田赋既均,苏松人仍任户部。”
江浙苏松地区赋税重于他地,人不得官户部,是朱元璋留下的问题。朱元璋在初取天下时,据说:“愤其城久不下,恶民之附寇(指张士诚),且受困于富室而更为死守。因令取诸豪族租佃簿历付有司,俾如其数为定税。故苏赋特重,惩一时之弊。” “初,太祖宝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而“浙西官、民田,视他方倍蓰,亩税有二三石者” 。后虽稍有减免,但苏松等地的田赋仍远远高于他地。实际受害的当然是普通农民。限制苏松人在户部做官,则是戒于“浙江及苏松二府为财赋之地”,而“户部胥吏,尽浙东巨奸,窟穴其间,那移上下,尽出其手。且精于握算,视长官犹木偶” 。江浙地区是明朝经济的重要支柱,朝廷害怕浙东人掌握财政大权造成威胁。这是一种歧视政策。它不仅给江浙农民带来祸害,而且不利于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人民不堪其苦,就用逃亡和逋欠的方法加以抵制,使重赋往往成为无赋。因而建文帝均江浙田赋,不仅有利于国家,也使百姓得受其惠,确是一件德政。
洪武末,江南僧道“多占腴田,蚕食百姓” 。因此,建文帝对僧道占田也做出了限制。建文三年(1401年)七月,下令“每僧道一人各存田五亩,免其租税,以供香火费,馀田入官,均给平民” ,也无疑是一桩爱民之举。
建文帝受攻击最甚的莫过于变更祖法,更改官制了。
朱元璋为控制中央大权对政治制度做了多次调整。洪武十三年(1380年),他罢中书省,废丞相,升六部秩以分相权,“事皆朝廷总之” 。朱元璋戒谕子孙:“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建文帝不顾祖训严禁,以齐泰为左丞相,黄子澄为右丞相 ,“阃外事一以付泰” 。这在维护旧制,视祖训为神物者看来,自然是大逆不道了。朱棣提出“悉复皇考之旧”,“纲纪政令一出于天子” 。这不仅是为借助于保守势力,使篡权师出有名,也是为了维护专制主义皇权。
改官制,终建文四年一直没有间断。有些官制的改变无关紧要,意义不大,或仅仅改变了名称。但有些改变,则是深有用意的。朱元璋升六部秩,而六部尚书仅二品,这是除宗人府官和公孤傅保以外文臣的最高品级,其目的是压抑大臣,以保证纲纪政令一出于天子,“天子之威福无下移” 。他所需要的是封建帝王的家奴,这些家奴可由皇帝任意处置,从罢黜直到廷杖至死。朱元璋所开创的廷杖,使大臣的身心遭到肆意的摧残和污辱。所谓“血溅玉阶,肉飞金陛”,“君之视臣如狗彘” 。史仲彬、楼琏曾以“安静祖法”为言,反对改官制。建文帝在楼琏的奏疏上批道:“此正所谓知其一未知其二者。六卿果可低于五府耶?祭酒犹在太仆下耶?假令皇祖而在,必当以更定为是。群臣勿复言。” 他不满于六部尚书低于五府官,祭酒反低于皇帝的养马官,至少要他们地位相等。这一方面提高了文臣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显示他无意把权力控制得太死。他倚重大臣,放手让他们去做事,尊重他们的地位,这与朱元璋的极端专制主义是大相径庭的。朱棣在致李景隆书中曾说:“祖训云,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子孙做皇帝时,不许立丞相。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今虽不立丞相,欲将六部官增崇极品,掌天下军马钱粮,总揽庶务,虽不立一丞相,反有六丞相也。天下之人,但知有尚书齐泰等,不知朝廷。” 这段话生动地说明了建文改制的情况和建文帝与朱元璋、朱棣对待大臣的不同态度。
洪武时,王府官的地位更低。他们不过是亲王的家庭教师和办事员。建文帝增设王府官,规定宾友教授进对侍坐称名不称臣,见礼如宾师 。方孝孺说:诸藩“尊崇之极,而骄泰易滋,左右之臣位下势卑,不能矫其失”,“天子慨然为深长之思,增立辅臣,重其职任,俾咸知尊贤取友,以成令德” 。限制宗藩骄泰,提高文臣地位,相辅相成。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