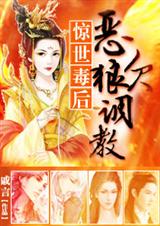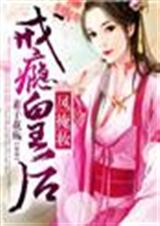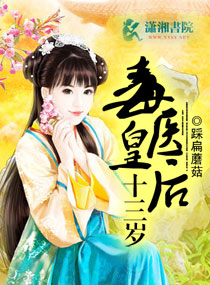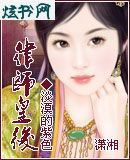中国皇后全传-第7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再次提出要罢免蔡襄,韩琦等人知道其中的原委,便直接切入正题,问:“陛下亲眼见过蔡襄的密奏吗?”赵曙说:“我虽没见过,但在庆宁宫时就已听说了。”韩琦说:“事出暧昧,请再加审察。假若仅仅凭一条谣言就把蔡襄治了罪,那么今后小人就可以更加肆意倾陷,君子就更难立足了。”赵曙坚持说:“造谣者为何不说别人,单单说他蔡襄呢?”终于将蔡襄贬出了朝廷。
曹氏为了警告赵曙不要忘记赵祯和她对他的扶立之功而有意编造的谎言,不但没有在赵曙身上产生如期的效果,反而平白无故地断送了大名人蔡襄的政治前途,这大概是曹氏始料不及的。蔡襄的遭遇表明,在赵曙私心深处,还有一根高度敏感的、紧紧绷着的神经,这就是时刻关注着人们对他继承皇位所持的态度。他认为自己当皇帝完全是天经地义、理所应当的,丝毫不依赖于任何外力的作用,凡是不承认其天经地义的人,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他都不能容忍!任何人不能对他当皇帝稍有异议,哪怕这种异议只是捕风捉影的传闻;任何人没有理由表白自己拥有扶立他的功劳,哪怕这种功劳是钢浇铁铸的事实;任何人不能取代他的地位,代替他行使至高无上的皇权,哪怕这种代替完全是迫不得已临时变通的常规。当曹氏明显地表现出对他的戒备之心,一再告诫他不要忘本的时候,当曹氏泰然自若地垂帘听政,一直不肯主动让出权力还政引退的时候,他便非常本能地表现出了对曹氏的不满。
还在嘉祐八年四月赵曙病情最重的时候,这种不满就已大量流露出来,说了许多矛头直指曹氏的话。六月份以后,他的病情逐步有所好转,但对曹氏的不满却越发强烈了。
他从患病时起就不愿意服药,大臣们闻知,都十分着急,纷纷上书劝他服药,宰相韩琦更是焦虑。六月的一天,韩琦亲手把药碗端到赵曙嘴边,赵曙仰卧榻上,只用嘴唇稍微抿一抿,就伸手推了回去,药水从碗中溅出来,撒在了韩琦官服上。那天曹氏正巧也在这里,连忙找出一件衣服请韩琦换上,韩琦不敢当,曹氏叹息说:“相公真不容易。”又向赵曙说:“你难道就不能勉强喝一点吗?”那知赵曙把头一扭,理都不理她。不但赵曙本人对曹氏表现出了明显的反感,在他的影响下,就连他的儿子们也对曹氏不很尊重了,这使曹氏更加伤心。有天,她当着大臣富弼、胡宿、吴奎的面,一边哭,一边说:“没了丈夫的孤老太婆过日子真难啊!就连顼儿、颢儿这些小孩子都不肯答理我了,受了委屈向谁诉说呢?”赵顼、赵颢即赵曙的长子、次子,赵顼即后来的宋神宗。听到曹氏的话,赵顼的老师韩维立刻教训说:“皇上已失了太后的欢心,你应当极尽孝敬从中弥合才是,否则,你父子都要受祸了。”赵顼生性聪明,恍然大悟。过了几天,曹氏高兴地对宰相们说:“顼儿这几天待我很有礼道,与往昔大不相同,全是卿等善择师傅的结果,应把他们请到中书好好褒奖一番。”赵顼再孝敬也终究难以弥合曹氏与赵曙间日益加大的感情裂痕,曹氏在极度烦恼之中,或许真的产生过废黜赵曙的念头。
十月,宰相韩琦兼任园陵使护送赵祯的灵柩去河南巩县安葬。这时大概曹氏已对赵曙的无礼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便派出一名宦官带着一封文书跑到巩县送给了韩琦。韩琦打开一看,原来上面抄满了赵曙平日所写的谩骂曹氏的歌词和他在宫中的种种过失。韩琦当着宦官的面把文书烧掉,让他捎话给曹氏说:“太后不是经常说皇上疾病未愈,心神不宁吗?既然是疾病所致,那么言语举动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他们都站到了赵曙一边,异口同声地替赵曙辩解,仿佛母子间的矛盾倒成了曹氏气量狭小不能容人造成的,在他们看来,既然赵曙有病,无论他怎样无礼,都是可以原谅的,而曹氏除了一忍再忍,不应有别的什么选择。这种态度虽然使曹氏更加愤愤不平,但也使她清醒地意识到,在朝臣们强大的保皇势力面前,她没有能力、也没有胆量冒天下之大不韪,她所能做的只是抹眼淌泪地发发牢骚,排遣一下心中的郁闷烦恼而已,对赵曙是半个指头也不能动一下的。满腹的委屈同样也郁积在赵曙心中,当韩琦等人来看望他时,他二话不说,劈头就是一句:“太后待我无恩。”韩琦真不愧是职掌调合百味的盐梅宰相,这时立场又反了过来,从容答道:“自古以来,圣明帝王很多,但独称舜为大孝,难道其余帝王都是不孝的吗?若父母慈爱而子孙孝敬,此乃常事,不足道,只有在父母不慈爱的情况下,做子孙的仍不失孝敬,才真正值得称赞,只怕陛下对太后或许有事奉不周之处,天下父母岂有不慈爱的!”赵曙不吭声了,从此之后人们再也没有听见他公开说过曹氏的坏话。
曹氏与赵曙之间,尽管这时已不再像以往那样公开地互相责难了,但内心的芥蒂依然远远没有解开。赵曙在七月初就已基本痊愈,并开始每天临朝坐殿听取中书、枢密奏事。照理说,皇帝恢复了治国的能力。太后就没有必要继续垂帘听政了,可是曹氏一直不肯还政引退。如果说,她当初答应垂帘主要是迫于客观条件,不得已而为之的话,那么这时她赖着不肯还政则主要是因为在政治上、生活上都对赵曙不放心的缘故。她对赵曙越不放心,就越不肯放弃手中的权力,而她越不放权,赵曙对她就越是反感,两人的关系一旦陷入了这样一个怪圈,不但没有和解的希望,反而埋藏着进一步恶化的危险。为了打破这个怪圈,老谋深算的韩琦亲手布下了两个圈套。
公元1064年,即治平元年四月初,代理御史中丞王畴上了一道奏疏,说今春以来,干旱少雨,麦田枯焦,建议赵曙以真宗为榜样,亲自前往寺观祈雨。韩琦等人立即随声附和,齐说应该。赵曙说:“还应与太后商议。”韩琦禀报曹氏,曹氏说:“官家大病初愈,恐怕不宜出宫。”韩琦说:“皇上已经答应出去了。”曹氏说:“素色的仪仗尚未准备就绪,再过些日子吧。”韩琦说:“这是小事,并不难办。”于是下令有司选择出行日期。过了十几天,仍不见动静,知谏院司马光上疏催促,说:“皇上要出宫祈雨之事,早已流闻四方,但至今未见成行,众论狐疑,不知又发生了什么变故。王者四海为家,为民父母,何必拘泥繁文,选择时日,忘万民朝夕之急?”曹氏没有理由再加阻拦,只得放行。赵曙遂出宫祈雨于相国天清寺、醋泉观。韩琦等人之所以抓住祈雨这件事大作文章,并不在于皇帝能否真正求下雨来,而是有其深意的,因为这样一则可以向朝廷内外显示赵曙已完全痊愈,恢复了治国的能力;二则可以巧妙地把玉玺收回到赵曙手上。玉玺是最高权威的象征,谁掌握玉玺谁就拥有最终决策的大权。宋朝规矩,若皇太后垂帘听政,那么符宝玉玺必须归皇太后收藏,皇帝只有在外出行军时,玉玺才可以随驾,回来后仍得交还太后。赵曙出外祈雨,顺理成章地把玉玺拿到了手上,回宫后却不肯交还。他一旦控制了玉玺,也就标志着拥有了发号施令的唯一合法权威,对于曹氏的意见,听与不听皆可随心所欲,曹氏的最终决策之权实际上已被他夺回。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赵曙亲政的关键一步顺利成功,韩琦紧接着布下了第二个圈套,这次的猎物便轮到曹氏了。此时赵曙虽早已御前殿视朝听政,但两府大臣仍像往常一样每天退朝后,到内东门小殿再向曹氏复奏。五月戊申早朝时,韩琦一下子向赵曙奏报了十余件事,赵曙裁决如流,悉皆允当。退朝后,韩琦对曾公亮等人说:“仁宗安葬完毕时,我就该求退,只因皇上御体未平,所以才迁延至今,现今皇上听断已如此不倦,诚乃天下大幸,我准备先禀明太后,请求安置一处地方,告老求退了。希望能得到诸公的赞成。”曾公亮等赶忙说:“朝廷怎能没有您?您千万别提这样的请求。”韩琦阴阴地笑了笑。于是一起来到内东门小殿,复奏赵曙已裁决的十几件事,曹氏每事都称善同意。众人退去后,韩琦单独留下来,把方才向曾公亮等说的那些话又复述了一番。曹氏说:“相公怎可求退?老身才真正应该退居深宫呢,每天在此,实在迫不得已,还是容老身先退吧。”韩琦正等着这句话哩!立即眉飞色舞大谈起来,说前代马氏、邓氏皇后如何如何贤明,尚且不免贪恋权势,今太后若能急流勇退,还政复辟,比马氏、邓氏更是强了许多倍,再拜称贺。接着便抖出了包袱,说台谏官员也有章疏请求太后还政了,不知太后决定在哪一天撤帘?曹氏这时才明白了韩琦口口声声求退的真实意图,原来是在以退为攻,逼着自己让位,真是太诡诈啦!但自己话既然说了出去,反悔是不可能了,她强烈地感到被人愚弄了,虽然气恼却也无可奈何。
曹氏被迫退居深宫,赵曙正式亲政,怪圈打破,避免了两人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危险,赵曙紧接着把曹氏的住所定名为慈寿宫,意思是希望这位慈爱的母后能够永远长寿,并且把曹氏的弟弟已官任宣徵北院使、保平节度使的曹佾,加封为同平章事兼中书令,使他享有“使相”这一极其荣耀的官衔。可是长期形成的感情裂痕仅靠这一二个虚名是不能完全弥合的。事实上,赵曙仍对曹氏心存余恨,就连曹氏所应享受的物质待遇,他都要施加这样那样的限制。在此之前,皇太后若需要什么物品,包括日用器具,只须凭事先加盖了皇帝御用之宝的空白文书直接到诸司库务索要,诸司库务就会立即供应,过后再由三司复奏皇帝就可以了。但如今临到曹氏时,赵曙却偏偏明文规定,必须首先由曹氏宫中的使臣把她需要的物品项目记录下来,送到有关诸司库务,再由这些部门另外书写榜文奏报皇帝,等到皇帝同意,盖上御宝之后,才可供应实物,平白使手续变得繁琐起来。这条规定虽经司马光上书反对,但赵曙一直维持不改。事实证明曹氏以往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凡此种种不能不使她更加愤懑心烦。两人的感情依旧冰冻三尺,碰到一些重大问题时,还会很自然地出现新的裂痕。
赵曙是作为赵祯的过继儿子被立为皇子的,论理只有赵祯和曹氏才是他的皇父母,而对于他的生父淄安朗王赵允让,只能按宗族辈分称皇伯。然而对赵曙来说,真正有感情的还是其亲生父母,他认为自己当了皇帝,就该父因子贵,生父不应仍然处在皇伯和王的地位上。治平二年(1065年)四月,诏令礼官及待制以上的官员讨论应如何尊奉淄王。此诏一下,朝廷之上立刻纷争鼎沸,掀起了一场轰动一时的政治风波。宰执大臣韩琦、欧阳修认为自古无称父为伯之理,赵允让应称“皇考”,持此观点的人我们可称之为“皇考派”;司马光、王珪等人则以“为人后者为人子,不得顾私亲”为理由,认为赵允让只能称“皇伯”,形成了“皇伯派”。两派争论激烈,声震九重。曹氏闻知,也坐不住了,她想:称赵允让为皇考,这不是明摆着要排斥先帝和我独一无二的地位吗?果真这样,那自己更无容身之处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她当即写了一封手书,痛斥韩琦、欧阳修。太后的懿旨毕竟还是有相当分量的,赵曙迫于压力,只得宣布暂停讨论。
当曹氏与赵曙的关系雪上加霜的时候,曹氏与赵顼之间却嫌隙尽释,春风和煦。在受到韩维教训之后,赵顼就经常到慈寿宫看望曹氏,也许只有在这时,慈爱的微笑才会回到曹氏的脸上。一次,赵顼身着全副盔甲,英姿飒爽来到慈寿宫,问曹氏:“娘娘,我穿这副盔甲好不?”曹氏笑着说:“你穿戎装确实好看,可是,假若连你都要披挂上阵,那国家岂不危险了吗?”赵顼乖乖地把盔甲脱下,祖孙俩又有说有笑谈起了别的。
公元1067年,即治平四年正月初八日,赵曙因病逝世,20岁的赵顼继位,是为神宗。孙儿当皇帝,曹氏得到的不仅仅是地位更加崇高,更重要的是心境出现了根本性的好转。初十日,她被尊为太皇太后,居住的慈寿宫也改名为庆寿宫。赵顼仿佛是在用自己的温情去弥补父亲的冷漠似的,对待曹氏极其孝敬,凡是能让曹氏愉悦的事,他无所不做。曹氏对赵顼的慈爱也是无微不至,有时赵顼退朝稍晚,她都要站在寝宫门外等候,甚至亲手端饭给赵顼吃。有一年清明节,赵顼陪曹氏闲聊,偶尔说起好像无人能制做珠子鞍辔了。赵顼虽是言者无意,曹氏却铭记在心,不几天就私下令人绘成图样,从内库中要来一副玉饰鞍辔送到后苑加工,装饰上珠玑,送给了赵顼。赵顼非常感动,立即唤人牵来心爱的坐骑小乌马,在福宁殿前亲试。为了答谢曹氏,他亲手设计了一乘小轿,制做得极其精致小巧,通体用珠玉黄金装饰,进呈给曹氏说:“娘娘试乘此小轿,去凉殿散心。”
于是载着曹氏前往凉殿,他与高太后步行着搀扶左右,曹氏下轿后,感慨万千,动情地说:“官家、太后亲自扶辇,当初我在曹家做女儿时,哪敢想到会有今天的盛事!”满面春风,心里比炎热的天气还要温暖。她去世后,大臣王存献的挽词中说的“珠镕锡御恩犹在,玉辇空扶事已空”,就是指的这两件事。
按照宋朝传统的礼制,外戚家的男子是不能进内宫谒见太后或者皇后的,随着曹氏年事日高,她的弟弟曹佾也成了老人,赵顼多次提出让曹佾进宫与曹氏叙叙亲情,曹氏都不肯答应。一天,曹佾向赵顼奏事,赵顼又提出这一要求,曹氏才勉强应允,赵顼便领着曹佾来到了庆寿宫。陪着坐了一会儿,寒暄几句,赵顼想让他姐弟俩单独在一块好好聊聊,便先站起身来,曹氏却对曹佾说:“这不是你应该逗留的地方。”忙不迭地把他打发出去。曹氏这样做并不是不念弟弟的亲情,而是不想让自己破坏祖宗确立的任何一项规矩。正由于她始终抱定“祖宗之法不可轻改”的政治信条,也就决定了她对赵顼的所作所为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