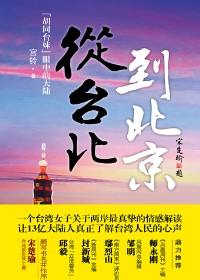从台湾流浪到大西北-第5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当时,我们还自以为在收容所里能被农八师联合加工厂招去工作,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从而结束了在社会上的流浪,解决了工作和吃饭问题,在此找到了一个栖身之地。
过了“经管处”左转向西,我们踏上了一条宽敞平坦的石子路,杨干事跟在我们几个年轻人的后面,姚助理员带着几个年龄较大的如:姜胖子,一撮毛、王空军和李海军(他们二人在“收容所”里都自称是转业战士)等人,走在队伍的最前头。姚助理员边走边向大家介绍说:“石河子是新疆生产建成设兵团最早的建设基地,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经过老一辈军垦战士十余年的艰苦创业,才有了这座新兴的工业城市。”他用手依次指着路南边的单位——由东向西是木工厂、汽二团、机械厂、毛纺厂、供电所,直至西边的十字路口,向北还有联合加工厂、造纸厂、糖厂、棉纺厂等厂子。但是这些单位名字的前面大多冠上了“八一”二字,以示“兵团”军队的建制。
从城东走到城西用了足有一个多小时,石河子市占地面积之大,大到让我们感到吃惊!路边的参天白杨,弯曲黑榆,婆娑细柳接连不断,茂盛成荫使我们为之欣慰。
农八师八一联合加工厂位于石河子市西三路的南段,它的南面便是供电所。
我们在姚助理员和杨干事的带领下,走进一个门头上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业第八师八一联合加工厂”名称具有二十九个字的单位。当初在我刚进入新疆,来到这片既广茅而又荒凉的陌生之地,钱粮(票)将尽,举目无亲,走投无路,几乎沦为乞丐的时候,就是这个具有二十九个字名称的单位收留了我。虽然当时它的本意不是同情我的困境,而是单位需用年轻劳动力我才被招用。在此干搬运工作,劳累筋骨,汗流浃背,吃了许多苦头,度过了我七八年宝贵的青春年华,体会了人生的酸甜苦辣,甚至在此还遭到了少数人的歧视和不公。但毕竟是在我刚流落到新疆,身陷绝境,无法生存的时候,是它收留了我,给了我户口和工作,使我犹如新生,从一个“盲流”(黑人黑户)成了一个自食其力的公民。对此,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是为之感激的!
当时进了大院,姚助理员让我们在一个新盖的礼堂门前的篮球场边林带中休息。然后他到食堂会计室里给我们取来了饭票和菜票,每人发了一个月的饭票和八块钱的菜票(从下个月工资里扣除)。
我们非常高兴,总算找到了一个有人管饭的地方。
此时,食堂已经开饭,我们也像其他工人一样拿着饭票和菜票来到食堂售饭窗口排队买饭,然后端着饭回到篮球场的林带边吃。一些不知情的过路人向我们投来好奇的目光,有的驻足观看,有的指指点点,还有的说我们是从口内跑来的“灾民”。我们一群“盲流”对此全然不管,任其他们说三道四,各人只顾狼吞虎咽地吃饭。
午饭后两点钟,劳资科的姚助理员把我们交给厂库房搬运排的一个中等个子,又黑又胖,甘肃口音很重的张建林排长。他又喊来了四个班长,将我们进行“瓜分”编班,随后带着我们到总务科库房去领被褥及安排住宿的地方。
总务科库房,实际上是锅炉西边的一个只盖了四层框架的楼房,孤单单的像一个还未竣工高耸的炮楼一样,底层大门紧锁,一二楼的窗口全用红砖堵死,三四楼的窗口任其洞开。据说它原是给二车间盖的榨油房,不知为何而停建,后被改作总务科的临时库房。
我们在楼下等了半个小时,只见一个个子不高,身材干瘦,甘肃口音很浓,名叫李云的总务科长来到库房门前,打开大门,爬上四楼从窗洞探出脑袋来高喊:“哦(我)在这瘩(里)念劳资科开的名单发东西,你们在哈(下)面接,一个挨一个地发,不要搞错!”于是就听上面喊到:“柴万友、鲁守义、潘云、蔡晓、韩长宣、顾体忠、张虎、郭瑜……”他按照劳资科开出的名单每念到一个人的名字,便从十几米高的四楼窗口掷出一床网套(棉絮),一条棉毯,一个被面,一个被里和一个装满棉籽壳的枕芯,被念到名字的人在下面慌忙上前伸出双手去接来不及接的便纷纷落地,然后自己捡起。最后李科长在楼上喊:“所需费用从你们以后的工资中扣除。”
发完铺盖,我们每人抱着东西由张排长带着,来到西边相距不远新盖的四车间工房(金工车间),里面空空当当的,还没有开始使用便安置我们住宿。在宽大的工房前后墙两边,用木板搭成两排三、四十米长的通铺,这里就成了我们二十多个及第二天厂里又从“收容所”招来的十几个“盲流”,总共有四十多人的临时工住处。
一时间,这个大工房竟然变成了一个来自天南地北,说话南腔北调,衣着习俗各异的一群“盲流”的宿舍。里面喧哗声,吵闹声接连不断,有人竟然开始玩牌,吞云吐雾地抽起烟来,弄得宿舍里乌烟瘴气。
下午五时许,突然在进门的西侧,一个姓蔡的四川小伙子和一个三十来岁姓韩的河南青年为争一点通铺的位置而吵骂,乃至撕打起来。
“老子操你先人板板啰!”
“我X你娘的”
二人你揪住我的头发,我卡住你的脖子扭打成一团,边打边骂,从铺上滚打到地上仍不松手,而两边又各有老乡在助威呐喊:
“打打打,打死他个龟儿子。”
“他奶奶的,咱给他没个完。”
双方气势汹汹,火药味儿很浓,大有闹个鱼死网破的架式。
此时,大伙怕把事情闹大影响不好,纷纷上前劝阻,才制止了这场纠纷。
事后我对此事很有感触,大家由收容所里来到工厂还不到一天,暂时有了一个栖身之地,还没吃上两顿饱饭就精神十足的为了一点得失而争执不休,甚至要恶言相加大打出手,无疑暴露了人与人“窝里斗”的习性……
到了傍晚,因为下午的一场纠纷闹得大家不快,工房里相对有些平静。我的铺处在北墙西端最里面的一个角落,因距大门较远,出入多有不便,有人不愿在此睡觉,我倒落得一点清静。
晚饭后,多数人到外面去玩或逛商店,我没事坐在临时搭建的铺上看书,没想到厂里保卫科杨桂林干事竟然跑到我们的临时宿舍来看我,于是我赶忙让坐。
他说他是安徽安庆人,1959年初中毕业支边来到新疆,被分配到石河子农八师八一联合加工厂工作,现已有四年了。今天上午他随劳资科姚助理员一起去收容所招人的时候,他看我出身学生年纪轻轻,又是同乡就建议姚将我收下。对此我表示感谢。
他在此坐了不到二十分钟告辞离去。在我送他走出大门外的时候,他还叮咛我在此把工作干好,争取转正。没想到第二年的春天,他竟调到甘肃酒泉新建的农业师去了。
杨干事走后不大一会,下午我刚分到搬运排三班的老乡宋明亮也来看我了。他和杨同为安徽支边青年,安徽蒙城县人,现和我同在一个班,念老乡之情,见我鞋衣破旧,他拿来一件八成新的白衬衣和一双旧球鞋送给我。
我再三谢绝,宋竟有些不快。最后实在是因为我脚上的布鞋已经烂得前面是“五龙”抓地,后面是“鸭蛋”出气的程度了,我便收下了他的一双鞋子,以作上班干活之用。
我流浪到新疆落魄西域,在石河子“收容所”被联合加工厂招用,初来乍到,举目无亲,十分孤单的时候,当天晚上竟有两位老乡诚心诚意地来看我,使我非常感动,大有它乡遇知已,两眼泪汪汪的感觉!
多日流浪,四处颠簸,终于有了一处归宿。当天晚上,我躺在床铺垫得很薄,身下梆硬的木板上,思前想后总是睡不着。旁边在白天相互争吵不休的“盲流”大都进入了梦乡,鼾声如雷,有的还在断断续续地说着梦话。此时我心里仍旧有种小知识分子多愁善感的忧虑,不知道以后的路该怎么走?还会再出现不测吗?这些我不得而知。
更多精彩,更多好书,尽在—http://。cc
第二十五章 找到工作 犹如新生(二)
更新时间2011…8…2 13:27:27 字数:2837
第二节
第二天早晨开始上班,我们几个人来到名为一车间的面粉大楼南边水泥地坪上报到。库房门前已经有一位四十多岁,膀大腰圆,体壮如牛的搬运排三班班长和一个身材不高,二十多岁的副班长在等我们。
一到那里,班长带着甘肃口音和一些新疆“腔”向我们作了自我介绍,他说他叫陈番生,甘肃陇西人,旧社会被抓壮丁来到新疆,一九四九年二十五日起义后成为一名军垦战士。因为过去家里穷没上过学,斗大的字不识一个,是个大老粗,不会讲话请大家不要见笑。
接着他便开始对我们训话:“你们是新来的工人,对厂里的情况还不了解,哦(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联合加工厂是搞粮油加工‘买卖的’,实际上就是一果(个)磨面、榨油的厂子。哦(我)们搬运排便是专门干扛包、装车、卸车等搬运工作的,所以来干搬运工这一行‘买卖的’要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才能完成上级交给哦(我)们的工作任务。北疆地区夏粮七月份开始收割,大量的小麦运到哦(我)厂,紧张繁忙的新粮入库工作就要开始。因为今年的工作量大,厂里缺少劳力,所以才招来你们这批新工人,试用三个月,干得好的可以转正,要不这个‘买卖子’是搞不成的”。但他没有说干得不好的将如何处置。他直言快语将厂里招用我们的动机和目的说了出来,啰啰嗦嗦讲了十几分钟,无非是告诫我们这些新来的“盲流”,一群无缰野马在今后的劳动中要卖力,要听话,服从领导才能由试用工转为一个正式工人。
听了陈班长的讲话,我才…更多精彩全本小说到:(炫)恍(书)然(网)…大悟——就是说我们这些刚被招来的“盲流”,进厂后必须经过三个月的试用期,“劳动管饭”的考验才决定你能否转正,是去是留还是个“谜”?
最后他说这几天的工作是清理库房,打扫地坪,为新粮入库作准备。
我们一连几天都在陈班长的带领下,挥动扫把,使用铁锹,拉着板车装运垃圾,清理库房,打扫地坪。虽然活比较脏,尘土飞扬,粉雾弥漫,但工作比较轻,不是十分劳累。
到了七月中旬,正如陈班长所说,北疆地区兵团农场的麦子开始收割,大部分打下的新粮纷纷拉到加工厂入库。运粮车有汽车、拖拉机、马车,甚至还有地方公社老乡的牛车、毛驴车也运来粮食。他们从库房的卸粮点一辆接一辆的排队,由厂里一直排到厂大门外的马路上。每天至少几十辆,多者上百辆,像一条由头望不到尾的长龙,缓慢地向前移动等候着我们卸车。
当时搬运排有四个班,早先原有的搬运工,加上厂里这次新招来的四十多个“试用工”共计有六七十人。每天分早晚两班倒,即早上六点至中午两点为早班,中午两点至晚上十点为晚班(新疆时间)。每个班再分三五个人的小组,在库房的几个卸粮点上卸粮。在七八月份夏粮进厂的繁忙季节,不管早班或晚班,从上班到下班的八九个小时,除了拉屎、尿尿和中间吃一顿饭外,几乎都在干活。即使如此,也不会见排队的粮车有所中断……
搬运工作非常简单,就是每人两个肩膀扛着一个脑袋,赤手空拳的上阵。上班时到卸粮点上,手搬、肩扛靠人的力气干活,或是打开停靠在卸粮铁制漏斗旁的车门,爬上汽车搬动麻袋,解开包口,两手抓住袋角,猛力提起麻袋将粮食倒入斗中,再由输粮机皮带将粮食过进仓库,这是一种人力加半机械的卸粮办法。当时一个班最多时要卸几十辆车,卸粮二三百吨。在七八月份炎热的夏天,露天作业,头顶烈日,汗流浃背,口干舌燥,身上被晒得会脱几层皮,有时手抓麻袋,指头被磨破,不得不用胶布包着干活。
上班干活再苦再累也要咬牙坚持,唯恐干的不好得不到领导上的认可,而丢掉饭碗。因为我们多数人过去在社会上游荡,既无工作又无饭吃,现在进了工厂不仅“劳动管饭”,而且还给你安置了一个住处,这总比在外面流浪着强。同时厂里又作出了试用三个月给于“转正”的承诺,当时对我们这些“盲流”来说,如同饥饿获食,雪中送炭,这是一件多么诱惑人心的事情!
机会难得,失不再来,所以大家非常珍惜。平时处事谨慎,上班拼命地干活,即使累得筋疲力尽也不会有人吐露半句怨言。
在夏粮进厂工作中,身强力壮的姜“胖子”、王“空军”、李“海军”他们还可以对付。而两个来自“天府之国”的“盲流”和一个来自靠近四川、青海,外号叫“小炉匠”的甘肃“盲流”,他们身高不足一米六,体重不到五十公斤,干起活来就显得格外地吃力,不堪重负。他们那特有的短小得可爱的身躯,背起装满小麦高有一米,重达一百零二公斤,上写“中粮”的麻袋,整个身体被压三分之二,人们在后面只能看到他们的两条小腿在颤抖,步履蹒跚艰难地爬上粮堆……
我介于前面两者之间,身材中等,体质单薄,干起活来样子也不比他们好到哪里。尽管我力不从心,但仍要拼命地去做,绝不能落伍,目的是“劳动”不仅可以“管饭”,而且还为了厂里能给于“转正”。
紧张而又繁重的卸粮工作,干上一天已经把人累得筋疲力尽,下班回到宿舍腰疼腿酸,身上就像散了架一样。晚上躺到铺上胳膊发麻,手指冒火,继而变为全身延续性的酸楚,以至于难以翻身,良久不能入睡,但次日依然要打起精神去上班。即使在干活中我的右腿被车箱框砸伤,右脚被钉子扎破,鲜血直流疼痛难忍,到卫生所医生进行处理,并给开了几天病假,而我只休息了两天就一瘸一拐地又去干活,以表示我轻伤不下火线的决心。我要卧薪尝胆,任劳任怨,不惜劳其筋骨之苦,争取三个月后成为厂里的一名正式职工,在此谋求一个栖身之地。否则,我已是山穷水尽,再也没有闯荡江湖的本钱了!
在此期间,我们搬运排不仅要卸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