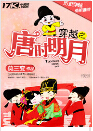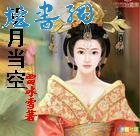宋时明月-第1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集。
“噢,那么,接下来你俩又成回跟屁虫了?”
“跟屁虫”,这个词很怪,两倭人脑袋转了好几个弯才体会出这句话的含义。还是由不三回答了赵兴的话:“不,学士出了新书,敝国上下都在翘首企盼,我俩必须把这本新书尽快送回国内,所以我们这是来告辞的。”
就这么走了?——出版费、稿费这些全不提?拍拍屁股就打算走?未免太欺负人了。
赵兴眼珠不被人察觉的转着,脸上带着逼真的忧虑,叹着气,说:“唉,学士苦啊——吃了上顿没下顿,兜里只剩俩窝窝头……嗯,你们回国时,有没有兴趣顺点货物?”
赵兴前一句话令两倭人感触的都要哭了,赵兴后半句话却让他们如万丈高楼失了脚——怎么?我们才酝酿好了悲哀,他怎么问起不想干的事?
两倭人还是很真诚地回答:“有的……我俩出外一年多,花费全靠家主支付,这次回去,一定要带点礼物,感谢主人的栽培。”
两老实人!
赵兴感慨过后,马上又问:“我的意思是说,你们俩有没有兴趣,给自己带点私货?”
两倭人相互看了一眼,不三、不四齐齐叩首,严肃地回答:“此身上下,皆主人所赐,诚不敢有私。”
赵兴对这两块榆木简直无话可说。他忍了半天气,又继续说:“好吧……我打算让你们带些私货,回去后,你们帮我把货卖了,凑齐路费再回天朝,也顺便这货款带回来,这笔钱,我打算让学士改善一下生活。”
第一部 华丽的前奏曲
第1018章 此心安处是吾乡
听说是为学士的生活费着想,两倭人感动啊,马上答应赵兴。
剩下的事是商议如何赚钱了。
其实,赵兴现在并不富裕。宋代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程族的产出只是让他们的生活稍稍富足而已,如果不是周涛那笔钱垫底,赵兴能拿出来的本钱真不多。
与之相应的是,这时代倭国与宋代的贸易已经很完善,所有能赚钱的行业都有拿执照的牙人把持,他们的投资额令赵兴想都不敢想象。
不过赵兴是什么人?
既然自己本钱小,那就用先进思维欺负古人……赵兴的目光扫过苏东坡的房子,这时,雪堂里响起了笛声,一个清脆的嗓音正在唱着苏轼的新词,声音里充满快乐与满足。
赵兴眼睛一亮——名人,我有这么一个时代牛人,那钱还不长着翅膀,劈里啪啦的往怀里掉。
什么是文化,印书是文化,印盘子难道不是文化?
别人印书我印盘子。找苏东坡提两句诗,用喷涂的方法把诗喷到瓷盘上,然后烧出来……本钱小,盘子的质量就无需追求,反正这盘子制作出来是让人摆着看的,而不是盛菜的,所以程家坳的陶窑完全可以满足生产条件。那种烧陶温度,稍高一点就成了劣质瓷盘。
盘子虽然劣质,但上面有了苏东坡的词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就上升成一种文化雅器,如果再加上苏东坡的亲笔手迹,那些倭人还不抢着买?
赵兴想到这儿,立刻冲进了房子。
一进门,他看到苏东坡正小心地问歌罢的王巩侍妾柔奴:“广南风士,应该很不好吧?”
自进屋以来,柔奴脸上一直带着微笑而王巩也带着满意的微笑看着柔奴——是那种有他(她)万事足的微笑!
这是什么样的微笑?
王巩因受“乌台诗案”牵连,被贬谪到地处岭南荒僻之地的宾州,他一个儿子死在宾州,一个儿子死在老家,而王巩自己也差点病死。
在见到王巩前,苏轼心中难过愧疚,以为王巩心里一定对他有所怨恨,不敢写信去问候他。可没想到,王巩不但没有怨恨他,反而面带微笑,载笑而归。
王巩受贬时,唯有京师歌妓柔奴毅然随行。她跟着王巩翻过大庾岭,在炎热的岭南一待多年,现在她回来了,无怨无悔,还能微笑,而且容光焕发。让苏轼很好奇。
对苏轼的问题,柔奴看看王巩,抿嘴淡笑而答:“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赵兴脑中轰然炸响。
“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
来到这个世界,赵兴老有一种漂泊感。面前的一切都给他一种不真实感,他一直希望自己是在做梦,什么时候梦醒了,世界便恢复了正常……
然而,这句话却如当头棒喝,令他的脑袋嗡嗡响个不停。
这时,苏东坡的话像是隔了一层玻璃,听起来很遥远,只听隐隐约约传来喊声:“拿笔来,且让我赋词一首。”
苏东坡不止赋了一首词——他赋了五首。
这人真是才华横溢,属于满的随时都要溢出的那种。等赵兴醒过神来,苏轼还在写。他随手抓起桌上第一张诗稿,那上面写的是那首名传千古的诗词:“常羡人间琢玉郎,
天教分付点酥娘。
自作清歌传皓齿,
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年愈少,
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
试问岭南应不好?
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柔奴又名“点酥”,苏东坡这是在夸奖这对乐观夫妇的恬然喜乐。
赵兴闯进来的时候,只粗粗向王巩拱了拱手。现在他不顾礼节的翻弄苏东坡的诗作,倒没引起屋里人的厌烦,因为他满脸的狂热很好的解释了他的失态。
不过,他说的话却让人纳闷——他在低声唠叨:“太大,太大!”
这话什么意思?
屋里人都觉得奇怪。
“太大”似乎不是一句赞赏词。难道是在说“太伟大”了?可这时代还没有“伟大”这个词。
赵兴下面的行动却又令人绝倒——他扯过桌上的空白纸,折叠几下,撕成巴掌大小的小纸片,而后眼巴巴的央求苏轼:“学士,写这上面,用小楷。”
王巩几乎笑喷出来,苏东坡的诗兴全被赵兴败坏了,他懊恼的狠狠的瞪着赵兴,但赵兴却未察觉苏东坡的愤怒,嘴里一叠声的央求。
还能怎么样?苏东坡是个不善于拒绝朋友的人,赵兴第一次开口求他,不过是写几个字而已,这要求他能拒绝吗?
无奈的将几首诗誊在几张巴掌大的纸片上,赵兴尤不甘心,继续说:“再来,写那首‘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首词代表苏东坡人生观的成熟。后来人们更是把词里包含的思想上升到哲学高度,称它为“想得开”哲学。到明清时代,这种哲学思想演化成四个字——难得糊涂。
苏轼从仕途巅峰谪居到黄州,他尝尽了世态炎凉,最后,他尤能保持乐观开朗的性格,归功于“想得开”三个字。而他的另一位弟子秦观,就因为想不开,在贬谪路上忧愤而死。
苏东坡一写完,赵兴带着满脸狂喜,拿着诗稿夺门而出。剩下苏东坡尴尬的向王巩解释:“定国,我这个门生……”
王巩平静无波的笑着。其实,他早看出来赵兴压根不能算苏东坡的门生。他虽然对苏东坡执弟子,苏东坡也坦然受之,但两人之间的称呼很有意思,苏东坡到是按惯例称呼他门生的“字”,但赵兴却用“学士”,而不是“老师”、“恩师”来称呼苏东坡。
“倒也是性情中人”,王巩笑着回答。
当晚,王巩与苏东坡彻夜尽谈。因为苏东坡房子小,无法安置,王巩便索性租来一艘小舟泊在江边,与苏东坡在小舟里彻夜尽谈。
第二天中午,苏东坡与王巩是被吵醒的,等他们爬出小舟,发现院落里多了四十多个壮汉。这些壮汉却由十名孩子领着,分组在院里忙碌——或平整场地,或和泥。江边还停着一艘大舟,十几个厢丁正从船上卸砖卸木材。
领头的孩子当中,苏东坡只认识程夏与程爽,他们两位似乎是孩子头,手里拿着厚厚一叠纸,指挥着院里的壮汉忙碌。王夫人等三个妇人远远站在雪堂门口,苏东坡的孩子很好奇,直围着那群壮汉转。
苏东坡叫过程夏问:“你老师呢?”
程夏叉手回答:“师公,老师昨晚领着两名倭人走了,说是打算送倭人到明州,将他们送上船。”
苏东坡看了看嘈杂的院子,很不满地说:“这是干什么?没看见我有客人吗?”
程夏答:“师公,这是老师的吩咐。老师说:冬天快到了,先生的房子小,既无法待客,也无法让师姨奶待产,所以吩咐我们尽快把房子建起来。师公若是嫌这嘈杂——我程家大院已经备好了酒菜,师公且去那里歇息两日。”
歇息两日?两天能盖好一栋房子?
苏轼的目光扫过那些忙碌的壮汉,发现他们手上很有些奇怪的工具。他本想好好探究一下,但客人在一边,午饭时间又到了,只好懊恼地领着客人前往城里的程家大院。
果然只需两天,程夏不是自夸。
程族拥有丰富的盖房经验,而黄州这片,即使到现代,流行的大多是单砖房,这样薄的墙壁在分工协作下砌得很快,第一天砌起四面墙壁。到半夜,挑灯夜战的工人已完成了封顶。等到第二天,则开始进入安门窗等内部装修活儿。
************************************
黄海,无风无浪。海面上孤独的飘着一艘宋船。
这艘宋船船头是方形的,形状像是缩小版的南海一号。
宋船的船头是空的,一层层木版像叠积木一样层层搭起一个上翘的迎风面,海浪就在悬空的船头下不停拍打。
船头甲板上站着五六个人,他们分成两派,一派人当中站着个子高大的赵兴。赵兴是身上各插着三把刀的两名日本武士,正是跟在苏东坡身边跑前跑后的两名倭人。再远处,船舷边,是扶着船舷,吐得有气无力的程爽。
与他们相对的是几名水手,当中一位船长模样的壮汉还在大声嚷嚷:“不行,我就说了,冬天我们应该走南阳,夏天才往倭国走,你们晚来了三个月,却非要往那个地方走,瞧,我们已经走了三天,大海茫茫,什么也没见着。”
赵兴背着手,神态很悠闲,他身后两名倭人则摆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凶狠的问:“赵官人说了要往北走,现在才三天,你说怎么办?”
两名倭人一边说话,一边将腰中的倭刀抽出半截,仿佛一言不和就准备动手。
这两倭人在宋国境内一副温良敦厚的模样,一出海则恢复了本来面目,不仅别上了腰刀,而且别了不只一把。
这时候的倭刀还保留着唐横刀的模样,刀身较直,类似一把单刃剑。这种单刃剑也就是现代人常说的“斩马剑”,它的全称叫做“尚方斩马剑”,在京剧里把它简称为“尚方宝剑”,如果写成错别字,那就是“上方剑”。
现在它只有一个名字,叫做“唐刀”,这是日本人起的名字,后来它叫做“日本武士剑”,如果刀身加一点弯度,那就是“日本武士刀”了。
刀上别两把以上的剑,这才是真正的武士做法,而腰中只别一把刀,那种刀叫做“仪刀(剑)”,亦即摆样子的武器。因为按照现在考古学统计,一场真正的战斗,一名战士平均要损坏1。3把武器。因为生死关头,你必须在珍惜武器与珍惜生命之间作出一个选择,如果你想保命,你就必须带上两把以上的武器。
这三柄刀各有名称,最长的名叫“太刀”,意思就是大一点的刀,大一点就是“太”。这把刀是用来破阵的,刀身约为人身高的70%。第二把刀叫做“打刀”,刀身长度为手臂的1。2至1。4。最短的那柄刀,在汉代叫做“手戟”,宋代叫“解手刀”,日本人叫“肋差”——是用来自杀的。
《水浒传》中,宋江杀阎婆惜就是用解手刀,宋人用这把短刀是用来处理公文函件的封皮,已失去了战斗的意义。
倭人的叫嚣并没有起得应有效果,那个船老大也算是走南闯北的人,他身后站的两名手持篙棍的水手,自己也学着赵兴的姿态,赤手空拳。他冲两个倭人一咧嘴,吐出一口浓痰说:“倭鬼,没跟你说话,大郎还没开口,矮子跳腾什么?”
“大郎”是宋代江湖术语,类似现代称呼“老大”。而海船的船主或者货主则称“纲首”。宋律“甲令: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以巨商为纲首、副纲首、杂事。”所以,赵兴这时的官称是纲首,“大郎”则是江湖称呼。
赵兴不慌不忙,眺望着头顶上的太阳,说:“我听说,你们有辨别方向的办法,前几天天阴有雨,我们都无法确定方向,现在把你我的方法都拿出来,我们再确认一下——我坚持认为,最多明天早晨,我们就能看见陆地。”
赵兴他们是从明州出发的,按明州船舶厮的记录,从明州到日本只有五天航程。该记录是这样描述该条航线的:朝太阳升起的东方航行一天,拐向北斗星方向,航行三日,可见耽罗……
这种技术是极其粗略的。而各位行船的船老大也都有自己的航海秘密。比如,现在船老大就在用自己的方法确定北方,在《梦溪笔谈》中也有记录,沈括记录了三种用磁石确定方向的办法,宋代最常用的是将磁针丢在水盆中指南,而最准确的是悬吊法。
现在船老大用的就是悬吊法,宋人通常不用这种方法。他拿出一块磁石,用磁石擦了擦一枚特制的大铁针,然后用一根绳绑住铁针的中间,将铁针悬吊起来,再招呼众人围成一个圈子,挡住了海风,而后指着针头方向说:“那里是北方。”
赵兴背着手,淡淡的笑着:“没那么麻烦,瞧我的:面朝太阳,看着自己的影子,用右脚朝影子方向迈出一步,两脚分开一指左右,面朝的方向就是北,就这么简单。”
这种方法其实只在北半球实用,南半球的方向确认,正好相反,但赵兴对此却没有解释。
船老大难以置信的按此方法反复确认,他的态度恭敬起来:“原来大郎也是常跑海的老手,这方法好……你说明天我们就能见到陆地,你确认?大郎,这可不是开玩笑,大海茫茫,我们的淡水已经用尽,明日不见陆地,那……”
第一部 华丽的前奏曲
第1019章 唐人的风采
冬季出海,风势不顺。这个季节正是日本船向中国开的时候。赵兴他们逆风出海,为了利用风势,船走的不是通常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