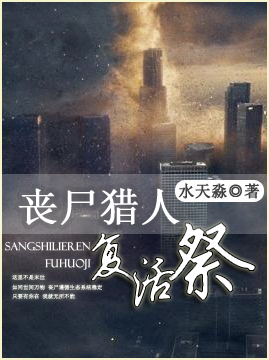复活-第5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们一刻不停的叫嚷声。隔壁是单身犯人的牢房。这间牢房更加拥挤,连门口和过道里都站满一群群喧闹的犯人。他们穿着湿衣服,正在分配什么东西,或者解决什么问题。押解兵向聂赫留朵夫解释说,监狱里有个开赌场的犯人,专门借钱给别的犯人,谁一时还不出就用纸牌剪成纸片作借据,此刻犯人头正根据纸片从伙食费中扣下钱来还给赌场老板。那些站得近的犯人看见军士和一个老爷,就住了口,恶狠狠地打量着他们。在分钱的人中间,聂赫留朵夫发现他认识的苦役犯费多罗夫。费多罗夫身边总带着一个皮肤白净、面孔浮肿、眉头紧皱、模样可怜的小伙子。另外,他还看见一个麻脸、烂鼻、面目可憎的流浪汉。据说这人在原始森林里杀死了同伴,吃了他的肉。流浪汉一个肩膀上披着湿囚袍,站在过道里,嘲弄而大胆地瞧着聂赫留朵夫,没有给他让路。聂赫留朵夫就从他身旁绕过去。
尽管聂赫留朵夫对这种景象十分熟悉,尽管在过去三个月中,他常常看到这四百名刑事犯处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大热天,他们在灰砂飞扬的大道上拖着脚镣行进,或者在大路旁休息,逢到天气暖和的日子,还看到男女犯人在旅站院子里公开通奸的可怕景象,虽然如此,他每次来到他们中间,象现在这样发现他们的目光集中在他身上,还是觉得羞愧和负疚。尤其难堪的是,除了这种羞愧和负疚感之分,还会产生克制不住的嫌恶和恐惧。他知道,就他们的处境来说也是无可奈何的,但他还是无法清除对他们的嫌恶。
“他们过得可舒服了,这些寄生虫”聂赫留朵夫向政治犯牢门走去,听见背后有人说,“这些鬼东西有什么好苦恼的,反正不会肚子疼,”一个沙哑的声音说,还夹着不堪入耳的骂人话。
人群中响起一阵不友善的嘲弄的哄笑。
十
护送聂赫留朵夫的军士经过单身犯牢房时对聂赫留朵夫说,他将在点名前来接他,然后转身走了。军士刚走开,就有一个男犯提起镣铐上的铁链,光着脚,快步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浑身发出一股浓重的汗酸臭,偷偷地对他说:“老爷,您出头管一下吧。那小子上了当。人家把他灌醉了。今天交接犯人的时候,他竟冒名顶替,说自己是卡尔玛诺夫。您出头管一下吧,我们可不能管,不然会被打死的,”那个男犯说,神色慌张地向四周看了一下,立刻从聂赫留朵夫身边溜走。
事情是这样的:一个叫卡尔玛诺夫的苦役犯,怂恿一个相貌同他相似的终身流放犯同他互换姓名,这样苦役犯就可以改为流放,而流放犯却要代替他去服苦役。
这件事聂赫留朵夫已经知道,因为那个犯人上礼拜就把这个骗局告诉了他。聂赫留朵夫点点头表示明白,并将尽力去办,然后头也不回地往前走去。
聂赫留朵夫在叶卡捷琳堡就认识这个犯人了,他当时请聂赫留朵夫替他说情,准许他去服苦役,把妻子一起带去。聂赫留朵夫对他的要求感到惊奇。这人中等身材,生有一个最普通的农民脸型,三十岁光景,因蓄意谋财害命而被判服苦役。他名叫玛卡尔。他犯罪的经过很奇怪。他对聂赫留朵夫说,这罪不是他玛卡尔犯的,而是他魔鬼犯的。他说,有个过路人找到他父亲,愿意出两个卢布要他父亲用雪橇把他送到四十俄里外的村子去。父亲就吩咐玛卡尔把他送去。玛卡尔套好雪橇,穿上衣服,就同那过路人一起喝茶。过路人一面喝茶,一面告诉他要回家成亲,随身带着在莫斯科挣到的五百卢布。玛卡尔听了这话,就走到院子里,找了一把斧子藏在雪橇草垫下。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带斧子,”他讲道,“只听得有个声音对我说:”带上斧子。‘我就把斧子带上。我们坐上雪橇出发。一路走去,什么事也没有。我也把那斧子给忘了。直到离村子不远,只剩下六俄里路,我们的雪橇离开村道,走上大路,往山坡上爬去。我就从雪橇上下来,跟在后面,这时他又低声对我说:“你还在犹豫什么呀?你一到山上,大路上就有人,前头就是村子。他就会带着钱走掉。要干,现在就得动手,还等什么呀?’我弯下腰,装作整理一下雪橇上铺着的草,那斧子仿佛自动跳到我手里。他回过头来对我一看,说:”你要干什么?‘我抡起斧子,想把他一家伙劈死,可他这人挺机灵,霍地跳下雪橇,一把抓住我的手,说:“混蛋,你想干什么?……’他把我推倒在雪地上,我也不还手,听他摆布。他用腰带捆住我的双手,把我扔在雪橇上。他就把我送到区警察局。我就坐了牢,后来开庭审判。我们的村社替我说好话,说我是个好人,从来没有做过坏事。我的东家也替我说好话。可是我们没有钱请律师,我就被判了四年苦役。”
现在,就是这样一个人要搭救同乡。他明明知道,这事有生命危险,但他还是把犯人中的秘密告诉了聂赫留朵夫,万一人家知道这事是他干的,准会把他活活勒死。
十一
政治犯住两个小房间,门外是一截同外界隔离的过道。聂赫留朵夫走进这部分过道,看见的第一个人就是西蒙松。西蒙松身穿短上衣,手里拿着一块松木,蹲在炉子跟前。炉门被热气吸进去,不断颤动。
西蒙松一看见聂赫留朵夫,没有站起来,只从两道浓眉下抬起眼睛,并同他握手。
“您来了,我很高兴,我正要跟您见面呢,”他凝视着聂赫留朵夫的眼睛,现出意味深长的样子说。
“什么事啊?”聂赫留朵夫问。
“回头告诉您。现在我走不开。”
西蒙松继续生炉子,应用他那套尽量减少热能损耗的原理。
聂赫留朵夫刚要从一扇门里进去,玛丝洛娃却从另一扇门里出来。她手拿扫帚,弯着腰,正在把一大堆垃圾往炉子那边扫。玛丝洛娃身穿白色短上衣,裙子下摆掖在腰里,脚穿长统袜,头上为了挡灰,齐眉包着一块白头巾。她一看见聂赫留朵夫,就挺直腰,脸涨得通红,神态活泼,放下扫帚,在裙子上擦擦手,笔直站在他面前。
“您在收拾房间吗?”聂赫留朵夫一面说,一面同她握手。
“是啊,这是我的老行当,”她说着微微一笑。“这儿脏得简直不象话。我们打扫了又打扫,还是弄不干净。怎么样,我那条毛毯干了吗?”她问西蒙松。
“差不多干了,”西蒙松说,用一种使聂赫留朵夫惊讶的异样目光瞧着她。
“哦,那我回头来拿,我那件皮袄也要拿来烤烤干。我们的人都在这里面,”她对聂赫留朵夫说,指指靠近的门,自己却往另一个门走去。
聂赫留朵夫推开门,走进一个不大的牢房。牢房里,板铺上点着一盏小小的铁皮灯,光线微弱。牢房里很阴冷,空中弥漫着灰尘、潮气和烟草味。铁皮灯只照亮一小圈地方,板铺处在阴影中,墙上跳动着影子。
在这个不大的牢房里,除了两个掌管伙食的男犯出去取开水和食物外,所有的人都在。聂赫留朵夫的老相识薇拉也在这里。她更加又瘦又黄,睁着一双惊惶不安的大眼睛,额上暴起一根很粗的青筋,头发剪得很短,身穿一件灰短袄。她坐在一张摊开的报纸前面,报纸上撒满烟草。她正紧张地把烟草往纸筒里装。
这里还有一个聂赫留朵夫觉得极其可爱的女政治犯——艾米丽雅。她负责掌管内务,给他的印象是,即使处境极其艰苦,也具有女性持家的本领,并且富有魅力。这会儿她坐在灯旁,卷起衣袖,用她那双晒得黑黑的灵巧而好看的手擦干大小杯子,把它们放在板铺的手巾上。艾米丽雅年轻,并不漂亮,但聪明而温和,笑起来显得快乐、活泼和迷人。现在她就用这样的笑容迎接聂赫留朵夫。
“我们还以为您已经回俄罗斯,不再来了呢,”她说。
这里还有谢基尼娜。她坐在较远的阴暗角落里,正在为一个淡黄头发的小女孩做着什么事。那女孩用悦耳的童音咿咿呀呀地说个不停。
“您来了,真是太好了。见到玛丝洛娃啦?”谢基尼娜问聂赫留朵夫。“您瞧,我们这儿来了个多好的小客人哪。”她指指小女孩说。
克雷里卓夫也在这里。他盘腿坐在远处角落里的板铺上,脚穿毡靴,脸容消瘦苍白,弯着腰,双手揣在皮袄袖管里,浑身发抖,用他那双害热病的眼睛瞅着聂赫留朵夫。聂赫留朵夫正想到他跟前去,忽然看见房门右边坐着一个淡棕色鬈发的男犯。这男犯戴着眼镜,身穿橡胶上衣,一面整理口袋里的东西,一面跟相貌俊美、脸带笑容的格拉别茨谈话。这个人就是赫赫有名的革命者诺伏德伏罗夫。聂赫留朵夫连忙同他招呼。聂赫留朵夫所以特别忙着跟他招呼,因为在这批政治犯中,他就不喜欢这个人。诺伏德伏罗夫闪动浅蓝色眼睛,透过眼镜瞅着聂赫留朵夫,接着皱起眉头,伸出一只瘦长的手来同他握。
“怎么样,旅行愉快吗?”他说,显然带着嘲弄的口气。
“是啊,有趣的事可不少,”聂赫留朵夫回答,装作没有听出他的嘲弄,把它当作亲切的表示。他说完,就往克雷里卓夫那边走去。
聂赫留朵夫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但心里对诺伏德伏罗夫却远不是没有芥蒂的。诺伏德伏罗夫说的话,以及他招人不快的意图,破坏了聂赫留朵夫的情绪。他感到沮丧和气恼。
“您身体怎么样?”他握着克雷里卓夫冰凉的哆嗦的手说。
“没什么,就是身子暖不过来,衣服都湿透了,”克雷里卓夫说着,慌忙把手揣到皮袄袖管里。“这里也冷得要死。您瞧,窗子都破了。”他指指铁栅外面玻璃窗上的两个窟窿。
“您怎么一直不来?”
“他们不让我进来,长官严得很。今天一个还算和气。”
“哼,好一个还算和气的长官”克雷里卓夫说。“您问问谢基尼娜,他今天早晨干了什么事。”
谢基尼娜没有站起来,讲了今天早晨从旅站出发前那个小女孩的事。
“照我看来,必须提出集体抗议,”薇拉断然说,同时胆怯而迟疑地瞧瞧这个人,又瞧瞧那个人。“西蒙松提过抗议了,但这还不够。”
“还提什么抗议?”克雷里卓夫恼怒地皱着眉头说。显然,薇拉的装腔作势和神经质早就使他反感了。“您是来找玛丝洛娃的吧?”他对聂赫留朵夫说。“她一直在干活,打扫。我们男的这一间她打扫好了,现在打扫女的那一间去了。就是跳蚤扫不掉,咬得人不得安生。谢基尼娜在那边干什么呀?”他扬扬头示意谢基尼娜那个角落,问。
“她在给养女梳头呢,”艾米丽雅说。
“她不会把虱子弄到我们身上来吧?”克雷里卓夫问。
“不会,不会,我很留神。现在她可干净了,”谢基尼娜说。“您把她带去吧,”她对艾米丽雅说,“我去帮帮玛丝洛娃。
给她送块毛毯去。“
艾米丽雅接过女孩,带着母性的慈爱把她两条胖嘟嘟的光胳膊贴在自己胸口,让她坐在膝盖上,又给她一小块糖。
谢基尼娜出去了,那两个取开水和食物的男人紧接着回到牢房里。
十二
进来的两个人当中有一个是青年,个儿不高,身体干瘦,穿一件有挂面的皮袄,脚登一双高统皮靴。他步伐轻快地走进来,手里提着两壶热气腾腾的开水,胳肢窝里夹着一块用头巾包着的面包。
“哦,原来是我们的公爵来了,”他说着将茶壶放在茶杯中间,把面包交给玛丝洛娃①。“我们买到些好东西,”他说着脱掉皮袄,把它从大家头顶上扔到板铺角上。“玛尔凯买了牛奶和鸡蛋,今天简直可以开舞会了。艾米丽雅总是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他笑眯眯地瞧着艾米丽雅说。
“来,现在你来沏茶吧,”他对她说。
①从上下文看,这里应是艾米丽雅。毛德英译本作艾米丽雅看来是对的。
这人的外表、动作、腔调和眼神都洋溢着生气和欢乐。进来的另一个人,个儿也不高,瘦骨棱棱,灰白的脸上颧骨很高,生有一双距离很宽的好看的淡绿色眼睛和两片薄薄的嘴唇。他同前面那个人正好相反,神态忧郁,精神萎靡。他身上穿着一件旧的棉大衣,靴子外面套着套鞋,手里提着两个瓦罐和两只树皮篮。他把东西放在艾米丽雅面前,对聂赫留朵夫只点了点头,但眼睛一直瞅着他。然后勉强向他伸出一只汗湿的手,慢吞吞地把食物从篮子里取出来放好。
这两个政治犯都是平民出身:第一个是农民纳巴托夫,第二个是工人玛尔凯。玛尔凯参加革命活动时已是个三十五岁的中年人;纳巴托夫却是十八岁时参加的。纳巴托夫先是在乡村小学读书,因成绩优良进了中学,并靠当家庭教师维持生活,中学毕业时得金质奖章,但他没有进大学,还在念七年级的时候就决心到他出身的平民中间去,去教育被遗忘的弟兄。他真的这样做了:先到一个乡里当文书,不久就因向农民朗读小册子和在农民中间创办生产消费合作社而被捕。第一次他坐了八个月牢,出狱后暗中仍受到监视。他一出狱,就到另一个省的一个乡里,在那里当了教员,仍旧搞那些活动。他再次被捕。这次他被关了一年零两个月,在狱中更加强了革命信念。
他第二次出狱后,被流放到彼尔姆省。他从那里逃跑了。他又一次被捕,又坐了七个月牢,然后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他在那里又因拒绝向新沙皇宣誓效忠,被判流放雅库茨克区。因此他成年后有一半日子倒是在监狱和流放中度过的。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丝毫没有使他变得暴躁,也没有损耗他的精力,反而使他更加精神焕发。他喜爱活动,胃口奇好,永远精力旺盛,生气勃勃,干这干那,忙个不停。不论做什么事,他从不后悔,也不海阔天空地胡思乱想,而总是把全部智慧、机灵和经验用在现实生活中。他出了监狱,总是为自己确定的目标奋斗,也就是教育和团结以农村平民为主的劳动者。一旦坐了牢,他仍旧精力旺盛、脚踏实地地同外界保持联系,并且就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