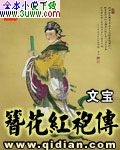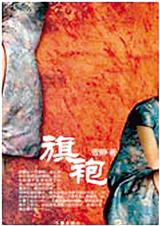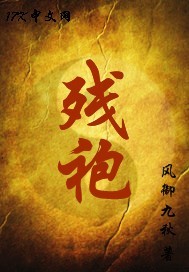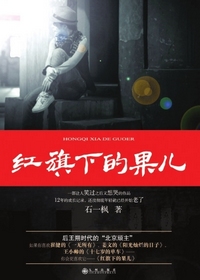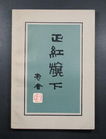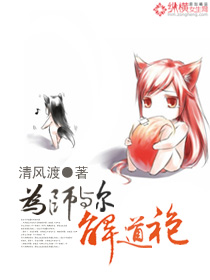红旗袍-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辆车。在火腿店等车的时候他又打了几个电话,询问那桩房地产案的情况。从这些电话中得到的信息,使他愈加下定决心不去蹚这浑水。
没过多久,局里的司机小周就来接他了。这家伙是侦探小说爱好者,很崇拜陈超,自称“陈探长的跟班”,估计早就把他要去拜访卞教授的事传遍全局了。陈超心想,这样也好。他开始为即将与卞教授进行的会谈打起了腹稿。
卞龙华的家是一套三室一厅的公寓。这是一座新建的公寓楼,位于黄金地段。很少有学者会住在这样的地方。为陈超开门的是卞龙华本人。这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中等身材,满头银发。他看起来饱经风霜,但依然面色红润,精神矍铄。五十年代,年轻的他曾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年的他又因“历史反革命问题”遭到迫害;而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又被称为“老学究”。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文学研究成了卞龙华最后的精神庇护所。
陈超递上火腿,说:“卞教授,一点薄礼,不成敬意,还请笑纳。”他试图找个地方把手里的东西放下,可看来看去,觉得实在不便用这油乎乎的东西玷污那些名贵的家具。
“谢谢你,陈队长,”卞龙华说道,“我们院长已经和我谈过你的情况。考虑到你的工作负担,我们决定你不必像其他学生那样坐班上课,不过论文你还是要按时交的。”
“非常感谢你们的理解,我肯定会按时交上论文的。”
这时,一名年轻女子轻轻走进客厅。她看起来也就三十出头,身穿黑色旗袍,脚蹬一双高跟凉鞋。她接过陈超手中的火腿,放在茶几上。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最能干的女儿凤凤,”卞龙华说道,“她在一家中美合资企业当CEO。”
“是最不孝的女儿吧?”凤凤笑道,“当年我没学中国文学,而是跑去学了商业管理。陈队长,感谢您选择我父亲作为您的导师,能有您这样大名鼎鼎的学生真是我父亲的荣幸呢。”
“不不不,能有机会师从卞教授是我的荣幸。”
“陈队长,你在警局干得好好的,怎么会想到来学中国古典文学呢?”凤凤一脸困惑地问。
“文学是一门与世无争的学问,”一旁的卞龙华插话道,他脸上带着一丝自嘲的微笑,“这丫头不听我的话,买下了这间公寓。买了就买了吧,我们现在住在一起,算是‘一国两制’吧。”
陈超明白,旁人对他这次的选择都颇有质疑,但他试着不去想这些。
“就像是一条从没走过的路,总想去尝试一下,”陈超说道。“想有机会干点别的,也权当是满足下虚荣心吧。”
凤凤说:“我有一个请求,我爸爸有糖尿病,血压又高,所以不能每天都去学校上班。您能来这儿听课吗?”
“没问题,只要卞教授方便就可以。”
这时,卞龙华说道:“记得高适的那句诗吗?‘百无一用是书生’啊!你看,我这糟老头子也就会这么点儿雕虫小技咯。”
“文章千古事。”陈超用杜甫的诗句回应道。
“嗯,你的确对文学有一股热情。唉,俗话说,同病相怜啊。当然,你恐怕也得为自己的‘消渴之疾’想想呢。我可听说你是个浪漫诗人。”卞龙华说道。
消渴之疾是糖尿病的别称,陈超听说过这个词。糖尿病患者通常会口渴、疲惫。卞龙华此话一语双关,既指自己所患的糖尿病,也指他对文学的求知若渴。可这与陈超是个“浪漫诗人”有何关系?
当他下楼回到车里时,发现司机小周正捧着一本香港发行的《花花公子》杂志,垂涎欲滴地打量着上面的裸体模特。陈超顿时豁然开朗,中国古语中的“消渴之疾”,也许可以拿来形容年轻人无可救药的浪漫激情呢。
但他又不能确定。自己也许在哪儿读到过这个词,只是各种八竿子打不着的信息充斥于脑海之中,让他一时想不清楚。坐进警车之后,陈超发现自己又恢复了警察的思维方式,并且正试图以这种方式解读卞教授的用词。看着后视镜中自己纠结的面容,他不禁摇了摇头。
不过他此刻的感觉还是不错的。学一下古典文学,总能给生活带来一些变化。
二
上海市公安局。于光明警官正坐在办公室里沉思。这其实还不能算他的办公室,至少现在还不是。作为特案组代理组长,陈超不在的这段时间里,他将暂时在这里办公。
事实上,尽管他早就在组里掌握实权,却没几个人把他当回事。即便是在陈超忙于各种会议和翻译工作的时候,也是如此。所以,他总感觉自己像是生活在陈超的阴影里。
陈超报名去学文学的决定令他颇感不解,局里同事们对此也是议论纷纷。按照刑侦队'1'队长'2'廖国昌的说法,陈超这是试着在声名鹊起之后保持低调,以读书为掩护远离众人目光焦点。在小周看来,陈超一直就想考个硕士甚至博士的学位,这对他将来的职业生涯至关重要,因为在新的党员干部提拔任用机制中,拥有高学历就拥有巨大先机。而返聘老干部张政委对此却有不同看法,他认为陈超的目的是出国留学,以便与远在美国的那位当狱警的红颜知己长相厮守。但这与那位传奇探长的诸多轶事一样,没人能辨明真假。
'1'原文为“homicide squad”也可译为重案组,是与陈超的特案组平行的部门。
'2'此处的“队长”,也可称为“组长”,但中国公安机关中无此称谓,故也称“队长”。
于光明对上述说法都不怎么赞同,或许这其中还有其他不为人知的秘密。陈超已就一桩房地产案向他询问过相关信息,却没有说明询问的原因。这不符合陈超平日与他交流案情时的风格。
不过在这样一个繁忙的早晨,已经没时间容他去细想这些了。党委李书记要他去廖队长办公室开会。
廖国昌是个四十出头的壮实汉子,鹰钩鼻、浓眉大眼,面容严肃。看到于光明走进办公室,他皱了皱眉,显得有些不悦。
在局里,一般只有那些有着重大政治影响的案件才会交给由陈超和于光明领导的特案组。廖国昌表现出的不悦,表明案件肯定不是简单的凶杀案。
“于光明同志,想必你对‘红旗袍杀人案’已经有所耳闻了吧。”与其说李书记是在提问,不如说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是的,这案子真是耸人听闻啊。”于光明答道。
一周之前,在淮海路一座花坛里发现一具姑娘的尸体。死者身穿红色旗袍。由于案发现场地处繁华商业区,在媒体的渲染之下,此案被公众称为“红旗袍杀人案”。案发之后当地曾出现交通阻塞现象,无数群众前来围观,还有无数记者和摄影师,夹在拥挤的人群中,作着各种报道。
一时间,报刊上充斥着各种推测。如果没有什么特定原因,哪个杀人犯会傻到把这般穿着的死者弃尸于如此繁华之地?一位记者发现,案发现场花坛所在的街道对面,正是上海音乐学院。还有人说这是一起政治案件,是对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丑恶价值取向的抗争。因为旗袍曾被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标志,如今却重新风靡上海。有家小报说得更悬,说此案幕后策划乃是时尚界某巨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媒体对于本案的热络报道,一些服装店旋即在橱窗里挂起了各色新款旗袍。
于光明感到此案迷雾重重。根据最初的尸检报告,死者臂部和腿部的伤痕显示在其窒息而死之前遭受过性侵犯。但死者身上和体内均未检出精液痕迹,且尸体被清洗过。死者在旗袍之下未穿着任何衣物,这于常理解释不通。弃尸地点位于人来人往的公共场所,几乎不会有杀人犯选择在这种地方弃尸。
按照局里一般的办案经验,本案凶手应该是在行凶后为死者穿上衣服,以便于运输。但由于行动仓促,他忘了给死者穿上内衣,或者说他认为没必要这么做。也许死者在遭遇致命袭击之前所穿的就是这件旗袍。弃尸地点也许并没有什么特别含义,可能就是凶手比较鲁莽,随便找了这么个地方丢下尸体而已。
于光明不怎么相信这种“偶然理论”,但他觉得这案子跟自己的特案组应该关系不大。他可不想越俎代庖。
“真是耸人听闻啊。”他重复着这句话,他觉得有必要这么重复一下,因为李书记和廖国昌都没吭声。“这案发现场有点儿意思。”
还是没人吭声。李书记轻轻地咳嗽起来,他的眼袋在这诡异的寂静气氛中显得愈加突出。说起来,李书记就快六十岁了,他的眼皮浮肿得很厉害,眉毛也早已变成灰色。
“调查有什么突破吗?”于光明向一旁的廖国昌问道。
“突破?”李书记插话道,“今天早晨又发现一具身穿红旗袍的女尸。”
“又一个?在哪儿?”
“南京路上。人民广场一号门的阅报栏前。”
“真是令人发指,那可是市中心,”于光明说道,“这是赤裸裸的挑衅啊!”
廖国昌说:“我们比对了两名受害人,二者存在一些相似之处。特别是她们所穿的旗袍,面料和款式完全一样。”
“这下那些记者们可又活跃起来了。”李书记一边说,一边用手指了指办公桌上堆着的那沓刚送来的报纸。
于光明拿起一份《解放日报》,上面发表了一张彩色照片,一个身穿红旗袍的姑娘倒在阅报栏前。
“上海第一起连环变态杀人案,”廖国昌大声读着报纸上的内容,“‘红旗袍’一词如今已变得家喻户晓,各种揣测四起,整个城市都笼罩在不安之中……”
“记者都疯了,”李书记打断了他,“啥图片和报道都发出来,真是唯恐天下不乱啊。”
他的这种挫败感是可以理解的。上海一直以高效率的政府工作和相对突出的低犯罪率著称。其实,之前在这座城市并非从未发生过连环杀人案,只是得益于高效的媒体管控,那些案件从未见诸报端罢了。一旦这样的案件被媒体曝光,就会暴露出警方的工作不力。所以通常国有报纸对于此类案件都是尽量避而不谈的。然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报界也都坚守着自己的底线——即新闻工作者必须揭露丑恶事件,在这种情况下,媒体管控就未必奏效了。
“如今书店里、电视机上都充斥着西方那些灯红酒绿的玩意儿,有些东西还是咱们的陈大探长翻译的呢!”廖国昌说道,“报纸专栏上都开始玩起福尔摩斯式的推理游戏了。看看《文汇报》,正预测下一起命案的发生时间呢。‘周五将会出现另一具身穿红旗袍的女尸。’”
于光明接话道:“这是常识,连环杀人案的凶手通常会以相似的手法作案。只要不被抓到,他就会一直这么干下去。陈队长翻译过一些关于连环杀手的东西,我觉得咱们应该听听他的看法。”
“去他妈的连环杀手!”李书记貌似被这个词激怒了,“你跟你的领导谈过了吗?我想还没有吧。他现在忙着写论文呢。”
陈超与李书记素来不合。于光明深知这一点,所以他选择了沉默。
“担心啥啊,难道说死了张屠户咱就得吃混毛猪吗?”廖国昌话里带着几分挖苦。
李书记显得特别激动:“这些杀人犯简直是在抽公安局的嘴巴!他们就好像是在炫耀‘我又干了,你们警察能奈我何’?他们正在千方百计地破坏我们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通过在人民群众中制造恐慌的方式威胁社会稳定!我们应当把调查重点集中在那些对政府心有怨言的人身上。”
看起来他的逻辑还停留在全民手捧《毛主席语录》的时代。于光明心想,照你这种逻辑,“阶级敌人”可多了去了。李书记向来以在刑事侦查上滥用政治理论而著称。这位局党组织一把手,貌似把自己也当成刑警队的一把手了。
“凶手肯定有个第一犯罪现场,很可能就在他家里。他的邻居也许听到了些什么呢。”廖国昌说。
“没错,通知所有居委会,特别是靠近两处案发现场的那些。毛主席说过,我们要依靠人民,”这时李书记拿出领导的威严指示道,“现在,为了尽快破案,廖队长、于警官,我授权你俩牵头组织一个专案组!”
直到李书记走出办公室之后,两位警官才开始正式讨论案情。
于光明先开了腔:“我对案情不甚了解,特别是对第一个受害人一无所知。”
“这是第一个死者的资料。”说着,廖国昌递过一个鼓鼓的文件夹,“目前我们还在收集第二个死者的信息。”
于光明拿起第一个死者的放大照片。乌黑的头发遮住了这个姑娘的一半面庞,她身材姣好,旗袍将她的曲线勾勒得玲珑有致。
廖国昌介绍道:“从胳膊和腿部的伤痕来看,她貌似遭受过某种性侵犯,但在其阴道内没有检出任何精液和非正常分泌物。法医已经排除凶手使用安全套的可能性,因为没有检出任何安全套润滑粉的成分。不管凶手对这姑娘做了什么,起码他给僵硬尸体穿上旗袍的时候很仓促很粗心。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旗袍上有撕扯痕迹,纽扣也没系好。”
“我们可以确定这旗袍根本不属于死者吧?第二个受害人不也穿着同样的旗袍吗?”于光明提出疑问。
“没错,这旗袍不是死者本人的。”
于光明仔细查看着照片上旗袍开衩被撕破的部分以及那些未系的纽扣。如果凶手不辞劳苦地提前准备好这样精美而时尚的旗袍,他会如此仓促地把它穿在死者身上吗?何况同样的事也许还发生了两次。
“第二个死者的旗袍开衩部分也被同样地撕破了吗?”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廖国昌不情愿地点了点头,确实不像因仓促而撕坏的。
“你啥时候对外发布第一个死者相关信息的?”
“发现尸体三四天之后吧。这个姑娘名叫田陌,二十出头,在邻近广西路和金陵路的海鸥饭店工作。她和瘫痪的父亲相依为命。听邻居们说她是个善良勤劳的姑娘。她没有男朋友,熟悉她的人也都不相信她能有什么仇家。”
“看上去凶手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