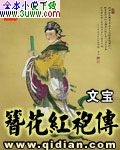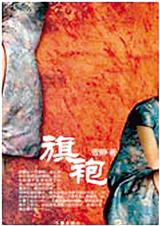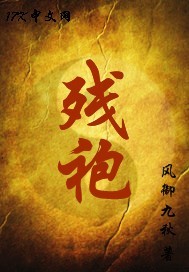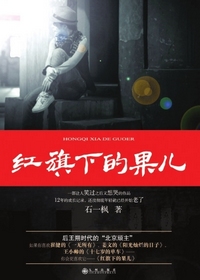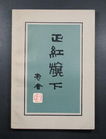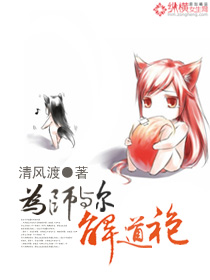红旗袍-第2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看来她非常爱自己的儿子。”陈超说道。
“我觉得也是。谁看了那张照片都会被感动的。”
“孔先生告诉过您那位模特儿的名字吗?”
“应该是告诉过我,不过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照片的拍摄过程您了解多少细节?比如说,旗袍的选择之类的。”
“这个,我老伴儿比较欣赏东方式的美丽,而旗袍可以展示那女人最美的一面。不过那肯定是她自己的旗袍,那么高级的旗袍我老伴儿可买不起。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照片上那件旗袍是谁选的。”孔姨摇了摇头。
“照片是在哪儿拍的呢?”
“那女人住在一栋豪华的公馆里,估计是在她家院子里拍的吧。我老伴儿在那里拍了一整天,用了五六卷胶片呢。接下来一个星期他都像只鼹鼠一样窝在暗房里冲洗照片。他太投入了,有一天晚上把所有照片拿回家来,问我哪张好。”
“所以是您帮您老伴儿选出了最好的一张?”
“嗯,可那张照片得奖没多久,我老伴儿就开始变得忧心忡忡的。一开始他没告诉我原因。我读过报纸之后才知道那照片引起争议了,有些人说照片里暗含‘政治信息’。”
“呵呵,什么东西都可能被涂上一层政治色彩。”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老伴儿因为那张照片被整得很惨。毛主席说有人借文学作品对党进行攻击,于是那些红卫兵们就说我老伴儿借照片对党含沙射影。跟别的‘牛鬼蛇神’一样,我老伴儿也被挂上牌子游街示众……”
“许多人都经历过这些,我父亲也是,挂着牌子游街……”陈超若有所思地说道。
“这还不算完呢,还有人逼我老伴儿说出照片上那女子的身份。这让他非常愤怒。”
“谁逼迫的孔先生?他对他们说什么了吗?”
“我记得当时整我老伴儿的是一伙造反派吧。他最后还是招了,因为那些人的手段太狠毒了。再说,在他看来,给摄影作品当模特儿也不是啥罪过,起码没有任何裸体和淫秽的内容。”
“孔老先生知不知道后来那模特儿怎么样了?”
“不,至少一开始他不知道。过了一年多之后他才听说那女人死了。这不是他的错,当年死了很多人。更不要说那个女人出生在那种家庭,还当了‘资产阶级’摄影模特儿。但是这件事却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压在我老伴儿的心里。”
“其实孔老先生没必要那么自责,那些造反派也可能在别处得知那模特儿的身份。”陈超说道。也许老摄影师很在乎那位模特儿吧。考虑到此时谈论这个没什么意义,于是他换了话题:“刚才您说孔老先生当时拍了五六卷胶片,其余照片保存下来了吗?”
“保存下来了。他这么做是冒很大风险的,当时连我都不知道它们藏在哪儿。不过他去世以后我无意中发现了那些胶片,还有一个笔记本。他给这些照片起的名字是‘红旗袍集’。我实在不忍心扔掉它们,因为我知道它们对我老伴儿来说意义非凡。”
说完,孔姨从一个箱子里拿出一大一小两个信封,大的里面装着一个笔记本,小的里面装着一沓照片。
“就是这个,陈警官。”说罢,她把两个信封递给了陈超。
“太感谢您了,孔姨。”陈超接过东西,站起身来,“看过之后我一定如数奉还。”
“没事,我拿着也没用,”孔姨说道,“不过别忘了你在庙里对佛祖发下的宏愿啊!”
“我不会忘记的。”
真是意外收获。陈超在弄堂外上了一辆出租车,在车里开始阅读那个笔记本。那是一本工作记录。按照上面的说法,孔建军当时是在一场音乐会上邂逅了那位模特儿,当时他就被“音乐高潮处她无与伦比的美丽”折服。后来一位少先队员模样的小男孩儿跑上舞台向她献花。那小男孩儿就是她的儿子,母子二人在舞台上亲密拥抱。音乐会后的一个星期,孔建军一直在劝说她当自己的摄影模特儿。这个过程并不轻松,因为这位女子对名利都不感兴趣。最后他好不容易说服她带着儿子拍一组照片。拍摄地点是她家后花园。
陈超快速浏览着这本记录着各种拍摄参数的工作笔记,发现那位模特儿的工作单位是上海音乐学院。笔记上还写着她的办公室电话。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孔建军在笔记中只提及了一次她的名字——梅老师。
合上笔记本,他开始查看那些照片。
眼前的照片数量很多。如当年那位摄影师一般,陈超也有些入迷了。
回过神来,他对出租车司机说道:“师傅,调头去上海音乐学院吧。”
二十三
陈超对音乐学院的探访一开始并不顺利。
学院现任党委书记赵奇光接待态度倒是不错,但他对梅老师几乎一无所知。查过校史资料后,他告诉陈超,这位梅老师和她的丈夫明老师当时都在学院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明老师自杀了,而梅老师死于一场意外。至于梅老师作为模特儿拍摄的那张照片,赵书记表示完全不了解。
“我是五六年前才调到学院的,”赵书记解释道,“大家都不愿提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事情。”
“是啊,都要朝前看的。”
“你可以去问问那些老人,他们或许认识梅老师,应该知道些什么。”赵书记在纸上写下一串人名,递给陈超,“祝你好运。”
不过认识梅老师的人如今应该都退休甚至过世了吧。拿着纸条看了一会儿,陈超决定先去拜访器乐系的刘正权教授。
“没错,这的确是梅老师!”刘教授看着照片说道,“不过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张照片啊。”
“您能给我讲讲她的事吗?”陈超问道。
“梅老师当年可以称得上是校花了。只可惜她死的时候还那么年轻。”
“她是怎么死的?”
“我也记不清了。当时她才三十四五岁,儿子才十岁。太悲剧了。”
“她儿子后来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刘教授说道,“当时我们在不同的院系,你得去问别人了。”
“那您给我推荐个人吧。”
“那个,你去找向子龙吧。他已经退休了,住在闵行区。这是他的地址。据我所知他钱包里一直放着一张梅老师的照片。”
看来这位向子龙当年曾仰慕梅老师,要不然这些年也不会一直把她的照片放在自己的钱包里。
离开刘教授家,陈超看了看表。他得抓紧去闵行区找向子龙,时间已经不多了。
那里曾经是一片工业区,距离市中心很远,所幸如今通了地铁。陈超打车赶到地铁站,然后坐了二十分钟地铁赶到闵行区,一路小跑出站,又拦下一辆出租车直奔向子龙的住处。
不一会儿他便来到一片居民区,走进了一栋居民楼。来到二层的一户人家门前,他敲了敲门。一阵沉默之后,屋里的人有些迟疑地打开了那扇仿木门。陈超掏出自己的名片,递给这个趿着拖鞋披着棉袍的瘦高男人。那人看了一眼,满是皱纹的脸上露出惊讶的神情。
“没错,我就是向子龙。阁下是中国作协的人?”
陈超才发现自己递给他的是一张中国作协的名片。情急之下他掏错了名片。
“不好意思,我把名片搞混了。我叫陈超,是上海市公安局的。不过我的确也是中国作协的成员。”
“哦,陈队长。我好像听说过您,”向子龙说着,将陈超让进家中,“不过不知道阁下今日上门有何贵干?是以诗人的身份还是以警察的身份呢?”
说着,他给陈超倒了一杯茶,给自己的杯中也续了一些水。他走路时一瘸一拐的。
“向教授,您的脚扭伤了吗?”
“不是,我三岁那年得了小儿麻痹症。”
“不好意思今日贸然登门找您是为了调查一件大案,需要向您了解一些事情。”陈超在茶几边一个塑料折叠椅上坐了下来。茶几看起来是定制的,比常见的长出一截。环视四周,他看到墙上有一个巨大的书架。除了这两样,房间里就没什么别的大件家具了。“是关于梅老师的事,她是您的同事吧?”
“梅老师?没错,她的确曾是我的同事,可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你们问这些干什么?”
“您别误会,我们要调查的案件并不牵涉到梅老师。但一些关于她的事情对我们的调查有帮助。您提供的信息我们都将严格保密。”
“您该不会是以她为题材写诗什么的吧?”
“您为什么这么问?”
“几年前曾经有人向我打听过梅老师的事,我当时拒绝了他。”
“那是个什么人?您还记得他的姓名吗?”陈超问道。
“我也忘了他叫什么了。不过我记得当时他给我看过身份证的。他自称是一位作家。估计是蒙我呢。”
“您能给我详细描述一下那个人吗?”
“好像三十出头吧,要么就是三十四五岁。很有教养,但说的话有点莫名其妙。我就记得这些。”向子龙喝了一口茶,“整个城市都沉浸在一种集体怀旧的氛围里,关于那些曾经是显赫家族的故事特别流行,就像那部《上海的红颜薄命》。我凭什么让别人拿着她的故事去换取名利?”
“向教授,您做得没错。那所谓的作家企图拿着梅老师的遭遇去牟利,的确令人无法接受。”
“是啊,她当年受的屈辱够多了!”
向子龙显得有些激动。作为一名仰慕过梅老师的异性追求者,他此刻的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屈辱”一词证明,他了解一些内情。
“向教授,我向您保证,我绝对不是为了编故事骗钱才来拜访您的。”陈超说道。
“但是您说是关于一件案子……”向子龙还是有些迟疑。
“目前,我不方便详细说案子的事,可以告诉您的是,凶手已经杀了很多人,如果我们不抓住他,他还会杀死更多的人。”说着,陈超拿出那本杂志和其他照片,递给向子龙,“您可能看过这本杂志吧?”
“哦,还有这些照片,”向子龙急切地翻看着照片,脸色苍白。他走到书架前,拿出一本相同的《中国画报》,“杂志我这也有一本,这些年我一直都留着它。”
向子龙保存的这本杂志中间夹着一个系有红丝带的书签,翻开正是梅老师照片所在的那一页。书签很新,上面印着东方明珠电视塔。这座电视塔是九十年代才建成的上海的地标建筑。
“都这么多年了,关于这张照片一定有许多故事吧?”陈超问道。
“是啊,说来话长。‘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你多大?”
“还在上小学。”
“那您知道‘文化大革命’爆发的背景吗?”
“当然。不过,您还是从头说起吧,向教授。”
“在我看来,一切从六十年代初就开始了。当时我刚被分配到音乐学院,而梅老师己经在那儿工作两年了。她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是学校里最出色的女教师。陈队长你别误会我的意思。对于我来说她更像是个良师益友。当时在学校里不能演奏那些古典名曲,只能吹吹打打一些简单的革命歌曲。我为此感到非常苦恼。如果没有她的鼓励,我也许就放弃音乐之路了。”
“正如您所说,梅老师当年在学校里是最出色的女人。那么肯定有很多人仰慕她,甚至追求她。您听到过这样的传闻吗?”
“您什么意思?”向子龙盯着陈超问道。
“向教授,我并不是要对梅老师不敬,请别误会。为了调查,我需要了解各种情况。”陈超赶忙解释道。
“没有,我从未听到过这样的传闻。像她那种出身的女人得夹着尾巴做人,一旦闹出绯闻就意味着灾难。当年那种政治气氛你们这些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那个时候,全国都没有一首真正的浪漫情歌。”
“那是因为当时毛主席希望人民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革命和建设之中吧……我听说她丈夫也在音乐学院工作,是吗?”
“是的,她丈夫叫明德仁,也是学院的老师。他没啥特别的。他们二人的婚姻在我看来就是父母包办的。明老师父亲曾经是个大财阀,而梅老师的父亲是个努力讨生活的小律师。当年的明府在上海滩也是显赫一时的豪宅了。”
“嗯,对于那座豪宅我也有耳闻。他们的婚姻生活有什么问题吗?”陈超不明白向子龙为什么要提到包办婚姻。
“我不太清楚。不过大家都说明德仁配不上梅老师。”
“好吧,”陈超意识到,在向子龙眼里,没人配得上梅老师,“那么,您是怎么知道这张照片的?梅老师向您提起过吗?还是说给您看过这本杂志?”
“都不是。当时我们在同一间办公室,有一次我偶然听到她与那位摄影师讲电话了。所以我买了一本那期杂志。”
“照片上她穿了一件旗袍。您后来见过她穿那件旗袍吗?”
“没见过,而且拍那照片之前我也没见她过穿。她有许多件旗袍,演出的时候常穿。但从来没穿过照片上那件。”
“梅老师是因为那张照片惹上麻烦的吗?”
“我也不知道,反正照片发表没多久‘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她公公去世了,丈夫也自杀了,罪名是反党反革命。而她也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被赶出豪宅,住进‘牛棚’——一间小阁楼里。而明府被一些‘革命群众’占据了。当时梅老师遭受了最屈辱的迫害。”
“她就是因为这个死去的吗?”
“关于她死去的那些情况,”向子龙喝了一口茶,仿佛在回忆着什么,“我的回忆可能有靠不住的地方,毕竟过去这么多年了。”
“我理解,毕竟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不过您不用纠结于细节是否准确。您所说的一切我都会去二次核实的,”陈超也喝了一口茶,“看看这张照片吧,真应了那句话,红颜薄命啊。我们应该为她做点儿什么。”
这句话让老教授一惊。
“你是说真的?”向子龙说道,“是啊,你们警察也应该为她做点儿什么了。”
陈超点了点头。他怕打断老教授回忆的思路,就没说什么。
“年轻人,你应该听说过当年那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大专院校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