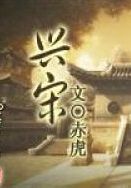兴宋-第29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都跑了。
孙里长说的语言很晦涩难懂,他代表全镇仅剩的老头向时穿献上三牲,而后递上一壶酒,似乎说了一番颂扬话,可是时穿一句听不懂——太平镇据说是晋代王谢孙三族某旁支定居的地方,后来战火纷飞,逐渐有了外姓,但太平镇的语言一直保持晋代风格,这种语言被认为是古汉语中的一种,现代被称为“太平语”。
“昔日王谢庭前燕,飞入平常百姓家……”时穿身边没有一个太平语的翻译,只好不懂装懂的吟诵一句,立刻跳转话题:“本官比较欣赏‘蓝田乡约’,赞成乡人自治,所以太平镇的民事本官不想过问(想过问也听不懂你们说什么),本官是来剿匪了,民事上不插手。”
时穿听不懂对方的话,不代表对方听不懂时穿的话。孙镇长脸上立刻露出喜色,又躬身赞颂几句,时穿反正听不懂,自顾自问:“谢眺楼犹在吗?李太白的《谢朓楼饯别》我还记得,‘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以及‘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什么?你说的我听不懂,赶紧找个会官话的举人秀才来?”
提前抵达的徐宁赶紧上前解释:“大人,那方腊抓住读书人喜欢剥皮熬油,当地的读书人因此恐惧,都逃至宣州城躲避战火,此处只余下几个蒙童稍稍懂点官话……咱不如先进镇子安歇,大人有话进镇再说。”
孙里长也赶紧邀请,时穿稍稍打量了一下孙里长,马上问:“宣州太平镇以孙姓为大是吧,我记得有首诗为《寄题宣州太平县众乐亭为孙莘老作》,那众乐亭还在吗?”
孙里长回答了一句,时穿点点头,回复说:“镇子我就不进了,我直接驻扎在镇外,镇前这条河通长江吧,让我们的水军过来,从长江转运粮食补给——告诉孙里长,我军要扎硬寨,需要订购大量砖石木材,太平镇谁家有砖石窑厂,让他通知一下窑厂立刻开工,人手不够赶紧去四处雇用,我要得急。”
此处是皖南的十万大山区域,方腊从杭州撤退后,就是躲入十万大山中苟延残喘。此地刚经过战火,正是人心惶惶的时候,想要安定人心,最后的办法就是给他们一个工作,一个足以养家糊口的工作。
孙镇长又说了几句,时穿一指徐宁:“里长,今后我军有徐统制负责与你沟通,你有事跟他说,现在,我需要百余亩抛荒的土地以便构筑军营,这土地在不在水边无所谓,最好给我一个单独山头。”
徐宁赶紧插话:“大人,我们在此地恐怕也停留不了多久,没准建设好营寨,咱们也该开拔了,故此下官以为,简单的硬寨足够了。”
“待不了多久?你恐怕想错了!”时穿也不解释:“我怎么吩咐你怎么做。”
徐宁是知道时穿对于居住环境有多么挑剔。他原本以为为了防范山里匪徒的偷袭,时穿顶多扎一个由木桩壕沟围成的“硬寨”,但如今时穿又要购买砖石又要用大量梁木,这分明是建设家园的劲头嘛,一个野外硬寨,至于吗?
然而,这支团练武装是由时穿装备,花销由时穿支付,人钱多没地方花,他徐宁能怎么办?
转脸望向林冲,林冲微微摇头,示意徐宁不要再说什么,而孙立则直接转过脸去,回避了徐宁的目光。至于孙镇长……这厮已经满脸兴奋,与身边的乡老说个不停。
当晚,一番忙碌过后,徐宁总算将营中事务安置完毕,军营扎在离太平镇五里的一个小山坡上,因为是第一天扎营,没有竖立起营墙,只是在山坡下挖了三道深深地壕沟,等林冲出来设置岗哨后,徐宁借机问:“我听说大人在与刘镇分手时,曾谈到童贯想闲置咱们。如今大人在这里扎硬寨,还一副大兴土木的模样,难道,咱们真被闲置了?”
林冲淡然地说:“大人扎硬寨,其实不光是为了被闲置的问题……当然,咱们肯定是被闲置了,至于童贯能闲置咱们多久……嘿嘿,这不用你来操心,大人不是肯吃亏的人,我瞧他心中已经有了主意。如今建这个硬寨,那是另有原因。”
徐宁摇摇头:“不明白,在这群山之中扎一个砖石硬寨,不是白花钱吗?这笔钱留下赏赐诸军不是更好?”
林冲笑了:“时大人做买卖,什么时候吃过亏?这硬寨啊,我也是刚想明白……”
第419章 太平镇的太平相
清晨,当薄雾犹笼罩在山峦上,群山之间便响起一声响亮的军号,接下来,这几日小镇百姓惯常看到的一幕再度上演——要不了片刻,就会以一群赤膊汉子,喊着口号排着队跑出来,绕着山梁跑步。
自从太平镇这个两万人口的小山镇里突然来了近三万士兵后,这一幕天天上映。通常这些汉子唱着歌跑完步后,会回到山脚下开始操练,偶尔,隔三岔五也放放雷火铳一类的响器,据说这种雷火铳不是驱鬼驱邪的法器,居然是一种武器……当然,这支军队摆弄这些响器的时候,或者摆出整齐队列走队形的时候,总能吸引不少大姑娘小媳妇围观。
这群军汉们初来到镇上时,曾让镇中父老大为惊恐,许多平常百姓都把家中稍具姿色的妇女藏起来,唯恐遭到兵祸——据说,摩尼教那里不管俊丑,只要是女人就抢。然而,这群军汉来的第二天,镇中孙氏当家族长,那位朝廷任命的保甲长——里长孙大人,开始吆喝族中老幼犒赏军队,当时,镇上唯有与孙家关系密切的李姓、苟姓谢姓王姓响应了孙姓族长的号召,其余人本着“兵过如蓖,匪过如梳”的祖训,疏远了这群军汉……紧接着,那些不去的人都后悔了。
据说管理这支军队的是一位主簿。这位主簿大人面见几位宗长后,立刻公布了朝廷赈济方案,当日劳军的几位宗长被任命全权负责此事,随后这位主簿下了一份大订单——雇用劳役与采购砖瓦石梁的订单。主薄大人需求量很大,据说要在镇外建立一座军营……当然,这份订单先到先得,到了那些犒赏军队的家族手里!
太平镇在群山之中,离景德镇不远,当地有不少窑厂。砖瓦这东西又不值钱,无非是下点苦力气做泥胚,去山里砍柴烧窑——若没那份技术,大不了去山里采石,附近就是十万大山,山坡上随意拣选几块石梁扛到军营里也能卖钱。乱世里力气不值钱,粮食才精贵。于是,镇民们经过初始的将信将疑,在几位胆大者试着与军汉们接触,并如期得到报酬之后,所有人都疯狂了,那些当初没有参加劳军的家族,在家族里很受了一通埋怨,责备他们眼光太浅——最初参与犒赏军队的的几个家族真赚了大钱。
据说,随同当初那份巨额订单的,是一份水泥窑修建方法,几个家族得到这份图纸后,马上在山里的矿点附近建立了大大小小的水泥窑,而后开始向军队出售水泥……接下来,这些家族发现,他们自己也需要水泥。随着军队营房的逐渐建立,许多泥瓦匠在工地上转了一圈之后,立刻学会使用这种新式建筑材料,这玩意没有多少技术含量。
镇里人跟军队打交道多了,知道这支军队军机确实严明,于是,五里外的军营成了小孩姑娘媳妇玩耍的必去之处。山里人娱乐项目匮乏,一场大戏常常能津津乐道好几年的,更何况那军营里天天在唱戏。
四月天,山里天气不凉不热,正是舒爽的好日子。每天清晨,随着军号响起,那些与军队打交道的汉子们也想听到号令一样,立刻扛起锄头背篓赶往军营,这时候,家中的女人孩子常常要求随行,汉子们这个时候常常也不拒绝——这支军队的购买力实在旺盛,镇上百姓无论拿出多少鸡蛋禽肉,他们都能一扫而空。所以每天早晨,汉子去军营打工挣钱,娘子带上家里产的鸡蛋以及绣品,去军营外摆个摊,也给家里添了进项。
所以,这支军队抵达十余天后,镇子里已经与这支军队的节奏保持一致了,每天军号吹响时,阵中不知有多少人在悉悉索索的起床穿衣,当军队跑出军营的时候,无数男女也扛着各种工具与农产品向军营赶,他们常常在山里上与跑步的军队插肩而过,这时候,镇民们总是用军汉听不懂的“太平话”,向熟识的军汉打招呼。虽然军汉们在队列里不能说话,却也能得到点头回礼——这种熟识常常让镇民回去炫耀好几天。
接下来,当军汉跑步回来,下苦力的汉子们也进入军营,开始一天的操劳——这些下苦力的汉子多是被军队雇用盖房子的,大工做不了,挖土和泥背砖卸运物资的活儿,都是他们的。军营里给的工钱厚,中午还管顿饭,这顿饭常常有肉,山里耕地不多,左右待在家里无事,跟着军汉混几顿肉食,也是美食。
至于随同镇民一起来的姑娘媳妇,她们常常被禁止进入军营。可这也没什么——她们可以在军营门口摆摊。随着这支军营驻扎于此,渐渐的,附近四里八乡的山民都把他们当做一道风景过来相看。连他们每日出号起床都觉得新鲜,很多人天不亮打着火把赶路,就为等在军营门口看士兵们集合排队,出营跑步……当然,由于军营内需要的劳工数量大,这些人见识过之后,常常转托熟人或者亲戚,也去军营里混口饭吃。
于是,这几日但有亲戚来镇上玩耍,镇民们总喜欢领着他们去军营门口看风景,这时候镇民心中不乏炫耀的心理。
汇集的人多了,就有草市出现。每日上午这段时间,军汉们都要操练因而不能出营,但聚集在门口的看客总要吃饭喝水买点零食吧,时不时的,军营内的大厨鲁胖子也会来到门口,扫荡村民带来的农产品以及山货,三万人的队伍,人数比镇民还多,他们的胃口之大,每天都能扫空所有的货物。
上午过后,大戏开演了——先是军营开午饭,只见无数炊事车一字排开,士兵们挨个排队领午餐,队伍整齐而有序。每到这时候,总有几位好事者大声介绍:这群海州兵吃的可不一般,顿顿有肉,据说每天是一斤肉的配给。这且不说,他们连烧酒都分发,只要是夜里站岗放哨的人,都能领到二两烧酒……
接下来,好事者肯定要炫耀海州兵夜里执勤多么严格,听到响动就放雷火铳,那雷火铳多么厉害,百步之内取项上人头如探囊取物,邻村的那谁谁,夜里不停警告擅入军营,立刻被轰去了半边脑袋……当然,你要真较真询问那被轰去半边脑袋的人具体名姓,好事者往往说不出——但全体镇民都跟你急,他们坚持认为有这种事,只是具体名姓嘛,一千个人说的一千个样子。
午饭过后,军营中常常冲出一队凶恶的蕃兵,这群蕃兵或者向南或者向北,一路奔驰。这个时候,好事者常常向从未见过高头大马的人炫耀说:这是晋西蕃兵,他们是出去剿匪的,这群人骑的马还不算高大,海州兵自己有支不大的骑兵,他们骑的战马那才叫高大呢,这些战马奔驰如电……总之,有他们存在,太平镇才真是太平。
这番话常常迎来一片应和声,或有人谈起旌德与宣州城附近的剿匪,据说哪里的官军很凶恶,一旦听到村中有人通匪,官军来了常常鸡犬不留,对比他们,这群海州兵真是良善……等等。
说这番话的同时,良善的海州兵开始自由活动了,荷包丰满的海州兵三三两两结伴去镇上玩耍,当然,因为语言不通,大多数海州兵还是喜欢待在军营里,上演“诸军百戏”。朝廷规定的“诸军百戏”内容有蹴鞠,划龙舟等等,宋初的时候,马球也是一种百戏内容,但因为战马宝贵,所以虽有倡导,基本无人实行。
海州兵的“百戏”内容更富娱乐性,其中有披甲上阵类似现代橄榄球运动的“夺鞠”,还有类似棒球运动的“捶丸”,前者碰撞剧烈,很受晋西蕃兵喜爱,于是下午这段时间,常常是两军打擂台,各派数队人马比赛——这才是等候营外的围观者苦苦期盼的。
太平镇在群山之中,海州兵占据一个山头,可周围山梁不少,站上去围观,虽然看不清具体人脸,可是攻防情况却看的很清楚,因此对于大多数缺乏娱乐的平民来说,这时的海洲军营就是小剧场。每到下午这个时刻,镇中与海州兵关系密切的家族,常常打上遮阳伞、带齐大队姑娘丫鬟仆人,进入军营中观赏比赛。而与军队关系生疏的,或者普普通通的百姓,在占据附近一个山头,饮着小酒吃着零食,也能欣赏到一场大戏。
山坡上看戏有一个好吃,常常是比赛一开始,好事者就跳出来介绍比赛规则,对阵双方情况……当然,以宋人的赌性,也少不了有人组织赌局下注赌胜负。
大约是所谓的“仓廪实,知礼节”,那些在镇上闲逛的海州兵很少做出触犯乡规民约的事情,这些人出了军营,常常穿着很考究的军服,军服上闪亮的铜扣,宽大而嵌满铜钉的武装带、军衔军功章绶带等等,让他们显得神俊威武,就是冲着这身漂亮军服,镇上有不少小伙子悄悄动了心思,上去用笨拙的官话与士兵搭讪,询问如何从军的问题——所以海州兵去了镇上,从不缺乏领路者。而当地镇民的官话水平,也在这短短数月内飞速渐长,这意外收获让时穿始料未及。
打听久了,镇上的年轻人常常感到失望——海州兵从不在异地招兵,这是一支团练武装,必须本乡本土才成。
然而,与海州兵搭讪的镇民却并不是一无所获,海州兵常常见闻广博,谈起海外风物,说起万里扬波,以及各种新奇玩意,一套接一套的令人只恨少长了一只耳朵……这些内容足够山民们在后半生里,反复给儿孙辈们念叨了。
双方接触多了,镇民们逐渐知道海州兵虽然来了三万人,但其实正式的战兵不足一万人,其余的人则是给战兵服务的辅兵,以及沿途招纳的民夫——虽然这些人也在拼命以海州团练自居,但这个时候,镇民已经会分辨战兵军服与辅兵、民夫的区别。后者常常没有制式军装,偶尔某些人跟随部队久了,会得到一两套军队换洗衣服,但常常没有肩章臂章以及军衔标志。
不过,这些战兵也不完全归属一支部队,据说海州团练本部只有五千兵力,另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