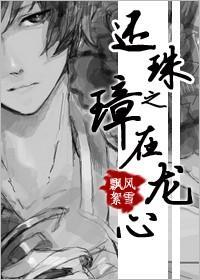朱元璋-第1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宋濂说:“我看你是给老虎捋胡须呀。”
刘基不听宋濂的,他真的派人送了一本给朱元璋。朱元璋十分惊讶,楚方玉能在被囚的最后时日里有如此平静的心态,写出这样一本犀利而又文采飞扬的杂记来,果真是才女,尽管里面是骂朱元璋的,他却恼不起来,心底有一种拂不去的悔意,堂堂大明开国皇帝,连这样一个女子都容不下吗?
他害怕这本文存,这是胜过千军万马的兵器,千军万马只能斩关夺城,开拓疆土,这本文存却会流传百世,让后人都看不起朱元璋。
朱元璋料定这是刘基出资刻的书,也许还有宋濂,他必须要他们交出所刻的书,还有刻书的活字版。
然而刘基在信上写得再明白不过了,“从书商手中偶得楚方玉文存,可谓奇文”,言下之意他并不是始作俑者,朱元璋不相信也无奈。
这本《珍珠翡翠白玉汤文存》像一块难以下咽的鸡骨头一样卡在了朱元璋的喉咙里,咽不下,吐不出,整日里烦躁不安。
这天中午,达兰来见朱元璋。
朱元璋不在。达兰悄悄进来,看到了放在龙案上的一本书,《珍珠翡翠白玉汤文存》。她拿起来看看,感动地想,宋夫子真仗义呀,这么快就印出来了。她又看到一份奏疏,正是刘基弹劾胡惟庸的。题目是:劾胡惟庸结党害公疏。她心里一动,又有了吸引利用胡惟庸的东西了。
刚看了几页,云奇来了,问:“娘娘有事?”
云奇像是无意又像有意地把龙案上的书本、奏折、御笔批答全整理到了一起,达兰无法要求再看。
“皇上呢?我有要事。”达兰说。
云奇说皇上在华盖殿,日本和高丽的使臣来进贡,皇上正在训话。
达兰讪讪地往外走:“那我回头再来。”
接待日本使者回来,朱元璋叫云奇把《珍珠翡翠白玉汤文存》拿去厨房烧掉,却又临时改变了主意,又要了回来,忍不住还要在灯下细读。去掉朱元璋看了并不舒服这一层,玩味楚方玉那雍容华贵、行云流水的文字,真是个享受。
静悄悄的夜,灯下只有朱元璋一个人在看《珍珠翡翠白玉汤文存》,看得出他很沉重,很伤感,也很生气,常常摔下书本,在地上踱几步,又忍不住捡起来再读。
马秀英悄然进来了。朱元璋发现了她,急忙把书藏起。马秀英说:“陛下不必藏,这本书我也有。它既然刊刻印行天下,哪能只供皇上一个人看呢?”
朱元璋说:“是什么人替楚方玉刻的?谁传出去的文稿?这人真是太可恨了。”
马秀英说:“这怕是无头案了。”
朱元璋说:“我猜,这刊印的事又是刘基所为。”
马秀英说:“又想再抓起他来?”
朱元璋说:“查无实据呀。好在,楚方玉没有太过分,不过也把朕奚落得够难堪了,这口气难消,朕已下令搜查民间,凡私藏、私刻此书者,一律问斩。”
马秀英说:“有些事,我是从书里才知道的,皇上并没对我说过。楚方玉所说的不假,是吗?”她指的当然是威逼她的事。
朱元璋默然良久,沉重地点了点头。
马秀英宽慰他,不要自寻烦恼了。古往今来,再英明的君主也非完人。销毁此书之令可下,千万别再罗织成文字狱,如不当回事,此书未必流传太广,如把这书当成大逆不道的事严办,反倒会弄得世人皆知,人人争看。秦始皇焚书,焚净了吗?
朱元璋承认她说得对,哑巴吃黄连,装聋作哑,听其自然,也许更好。
在刘伯温上奏疏狠狠弹劾胡惟庸一本的次日晚上,当达兰借故溜出城去,与胡惟庸在他的外宅里幽会时,把她看到的奏疏一半的内容告诉了胡惟庸。
胡惟庸如吞了个苍蝇一样难受,那天尽管不必防备有人惊扰,他却阳痿不举,达兰好不后悔,就该云雨过后再告诉他,没想到这事会影响了房事。
送走了达兰,胡惟庸立刻派心腹把几个亲信召到外宅来密商对策。胡惟庸最恼恨的是刘基已经绑赴法场了,却节外生枝,叫皇上那混蛋老丈人给搅了局。现在可好,打虎不成反被虎伤,看来刘基是要与他胡惟庸周旋到底了。
陈宁说也难怪,他这是报谈洋坟地案的一箭之仇呢。
胡惟庸说,他写了那么长的奏疏,对他很不利,皇上本来就对他权太重而不放心。这次连陈宁也捎上了,不能不防。
“可恨这刘基,如此可恶,”吴云说,“最好是永远封住他的口。”这是暗示。
“永远封住?”胡惟庸说,“那只有让他死了,上次他在法场上都逃过了一劫,他命真大。”
“机会还有。”陈宁进一步暗示,他病了,这几天一直在请郎中吃药。
吴云眉飞色舞,认定是天赐良机!何不趁机在药里投毒,让他一命呜呼?
胡惟庸摇头认为不可。他刚刚上了个折子参我,立刻暴卒,我不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吗?
陈宁沉吟半晌,认为有一个办法可行。叫御医开一服可置人死地又不马上见效的药,三个月或半年后发作,就永远没人怀疑了。
吴云拍手叫绝,说这真是妙计。不过也怀疑有这样的慢功夫毒药吗?从来没听说过。况且要找到听话又严守机密的御医才行,这又谈何容易!
胡惟庸说:“这倒不难,让我再仔细想想。”这等于胡惟庸已决心撞个鱼死网破了。
胡惟庸想起太医院里有一个熟人,叫麻奉工,官居太医丞,三年前他私卖御医院的几味贵重药品,东窗事发,差点丢官罢差,他给胡惟庸送了一扇价格不菲的水晶四扇屏风,胡惟庸出面替他摆平了,官居原职,因此麻奉工对胡惟庸感激涕零,四时节令,他都要配些滋补的药送给胡丞相。
麻奉工这天在太医院当值,没想到丞相会亲自迈进大门,通常是叫底下的人传令就是了。
胡惟庸大摇大摆地坐在那里,问太医丞麻奉工,太医院现在是几品啊?正五品吧?
太医丞麻奉工道:“是。太医令为正五品,我这太医丞就是六品了,御医七品。”
“太低了点。”胡惟庸既表同情又许愿,日后给你们升为四品,并且说他早想好了,由麻奉工当太医令。
太医丞受宠若惊,忙说那可就仰仗丞相了,又说他们这些人其实是提着脑袋干活,治好王公大臣的病,应该;治坏了,得拿命来顶。
“倒也没那么悬乎。”胡惟庸四下看看,问他有没有这样的方子,投下去并不马上见效,几个月后才死人。
麻奉工吓了一跳,问:“丞相这是何意?”
胡惟庸一笑,只问你有没有?
“有是有的。”他说,医生行医,悬壶济世,本是活命救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不敢与闻。
胡惟庸叫他只管配方下药,至于后果,与他无关;又很神秘地告诉他,这是皇上密令,要置此人于死地。
麻奉工道:“这我就不懂了。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皇上赐死的事,本朝也不少见,何必非用这样见不得人的手段呢?”
胡惟庸吓唬他,可要小心,给皇上办差,谁敢说见不得人?
麻奉工道:“丞相还是找别人吧,我胆子小。”
胡惟庸拂袖而起:“好啊,你别后悔就行。”
在他往外走的时候,麻奉工又害怕了,不干,不又得罪了丞相吗?但他仍想问问,要让他死的是个什么人啊?
“当然是犯上忤逆的乱臣贼子。”胡惟庸一字一顿地说:“刘基!”
麻奉工吓得一抖。但他知道刘基在午门外险些被杀头的事。
胡惟庸说,上次都推到午门外,马上要行刑了,却不想皇上那老糊涂了的岳父跑来敲了登闻鼓,叫皇上下不来台,不给岳父个面子不好看,你以为刘基真的不该死呀?这回你放心了吧?
麻奉工这倒深信不疑了,他只得说:“好吧。”声音和蚊子哼哼差不多。
第八十二章
皇帝审案,太子推翻,朱元璋急于让他走出宋老夫子的阴影。老虎如果不用它的利爪尖牙,猫也会欺负他的。上元节与民同乐,却乐出了血腥一条街。
既然朱元璋试图把太子朱标从宋夫子的阴影里拉出来,就不是说说而已,他要太子在他活着在位的时候就跟着他历练,学他的雷厉风行和治国方略,以猛临民。但毕竟不十分放心,这如同雏鹰捕食,也不能过早放单飞。譬如让朱标断案,多是御史或刑部尚书作陪,又都是复审的案子。
今天让朱标审的,又是朱元璋已审过并定了刑的,在陪同御史袁凯看来,这是走走形式,叫太子体会一下父皇的精明果断和公允。太子并不以为然,他审得十分用心,几乎是从头来过,连人证物证也一样不能少。
一个年轻犯人跪在朱标面前,御史袁凯敬陪末座。朱标打量这个文弱书生,朱标问他叫什么?犯的什么罪?
犯人答:“我叫冯宛,我没罪,有罪的是我父亲。”
袁凯介绍案情,他父亲是青州县令,因草菅人命罪判了死刑。
朱标一边翻案卷一边觉得奇怪:“一人犯罪一人当,你父亲死罪,与你何干?怎么把你也抓来了?”
袁凯说他是自投罗网的。
犯人冯宛陈述说:“我想替父死,我父亲茹苦含辛抚养我们弟兄七人,实属不易,我想替死,可皇上说我拿大明律开玩笑,也把我关了起来。”
朱标又一次想确认,他父亲果然有罪吗?
“有罪。”冯宛答,“我不求翻供,只求代死。”
袁凯见太子有点动心,忙悄声提醒朱标,恐怕有诈,不然皇上不能连他都抓。
朱标忽然喝令:“那好,成全他,把他推出去砍了。”
这令袁凯吃了一惊,但冯宛并无惧色,反而恭恭敬敬给太子磕了个头,说:“看来太子殿下是个大孝之人,能体会在下一片孝心。谢了。”
爬起来后,冯宛面不改色地去赴死。
冯宛已被武士拖走了,朱标又喊:“回来!”
武士又把冯宛推上殿来,朱标说:“你本是一片孝心,这样杀了你于心不忍。这样吧,免你父亲一死,改判他到塞外戍边。”
冯宛并不满意,他跪下说,那和处死了是一样的,即使不埋骨荒漠,也是回不来了。所以冯宛仍愿一死,免了父亲的罪,望殿下成全。
朱标说:“你得寸进尺。太可恶了!那好,还是成全你,拉下去砍了吧。”
冯宛再次道谢,依然从容而出,这令朱标又惊奇又佩服,朱标再次把他叫了回来:“拉回来!”
朱标对袁凯说,两次试探,证明他的孝心是真的,不然早屁滚尿流了,这样的人不可不成全。
袁凯深感不妥,忙提醒他要慎重,这些案子全是圣上亲自审后定了案的,发来殿下复审,一两件有异议尚可,但殿下几乎件件从轻发落了,仁慈固然对,皇上那儿怕无法交代。
朱标说他自有道理。他对冯宛说:“冯宛你听着,念你一片至孝心怀,成全你,免你父亲一死,只罢他的官。你下去吧。”
冯宛泪流满面地磕头说:“谢谢太子。”
朱标意犹未尽,说:“我为你屈法,因为你孝,我希望孝心能成为民本、国本。”
冯宛千恩万谢地下去了,御史袁凯可犯了难,太子可以为所欲为,自己怎么办?皇上首先会把板子打在他屁股上啊。
果然不出所料。
朱元璋看完了太子重审的案卷,重重地往案上一放,脸上冰冷可怕,垂手站在一旁的御史袁凯十分惶惑。朱元璋说:“太子没审过案,你也没审过吗?朕审过的所有的案子他几乎都推翻了,有的全翻,像这个冯宛;有的减罪一等,你为什么不说话?”
袁凯苦笑着说:“臣有过失。”
朱元璋又笑了:“也不能怪罪你。你有什么过失?他会听你的吗?”
袁凯这才松了一口气。
朱元璋以探询的口气问袁凯,朕审结的案子,和太子的大相径庭,问他看谁对?
袁凯说:“陛下法正,太子仁慈。”
“你老奸巨猾!”朱元璋说,“这也有把柄叫朕抓住,你这不等于说朕不仁慈吗?”
袁凯登时又吓得魂不附体,好在这一次朱元璋不是那么认真追究,他虽不满意儿子的宽纵无边,却对他的重“孝”很感欣慰。
这次审案风波没有想象得那么严重,朱元璋没有大发雷霆,而且没有推翻朱标复审的判决,冯宛的事一阵风传出去了,成为一段佳话,这令朱标很得意。
朱标与太子妃常娥在御花园里漫步时,也是一脸得意。常娥问:“你因为什么事情差一点把父皇惹火了?”
朱标说,这叫道不同不相为谋,父皇主张严法治国,我则信奉仁德化民。对犯人,父皇历来是严刑重法,他发来十几件案子叫我重审,他怪我都给改轻了,说是纵容,等于庇护。
常娥道:“你也太过。皇上都审过了,要你推倒重来?皇上是试试你,考考你,教一教你日后怎么治国,你倒好,认真了,竟把皇上审结的案子全部推翻。”
“要我审,就这样。”朱标说,“不用我,就算了。”
“这叫什么话!”常娥说,“皇上总有百年、龙驭宾天的时候啊,你那时也能这么甩手吗?”
朱标说:“从前父皇怪宋濂把我教坏了,这次有点彻底失望了,也许我真不合适当太子,父亲总是说四弟燕王比我有魄力。”
常娥让他也学学嘛,不能让父皇灰心。
“对我灰心不说,连累御史袁凯也跟着倒了霉。”朱标说他被皇上训了一顿,怕皇上拿他出气,本来皇上没想怎么着他,回去后就疯了,抓狗屎往脸上抹。
常娥说:“这么不担事呀?真疯了?”
朱标说:“也许是装的,反正疯了;疯了也好,躲过了一劫。”
第二天朱元璋又交下来一个通敌案,非同小可。犯官是镇守海防明州卫指挥同知林贤。这几年倭寇屡次犯边,在福建泉州、漳州一带登陆,烧杀抢掠,令朱元璋十分恼火,便加强了沿海的防护力量。却不料有人告发,明州卫指挥同知林贤通敌卖国,居然拿了日本人五百两黄金的贿赂,为倭寇提供情报。
这还得了!朱元璋初时不信,但派去查办的御史连赃金都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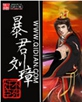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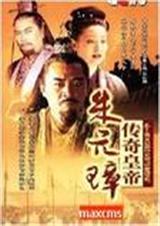
![[综琼瑶]璋显龙心封面](http://www.8btxt.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