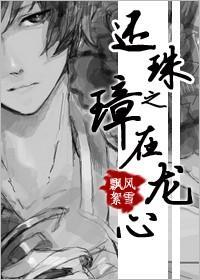朱元璋-第9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朱标马上告诉他出处,这是孟子的话。
朱元璋最讨厌孟子,朱标偏偏拾孟子牙慧,便立刻板起了面孔:“他说的,不足为凭。”停了一下又问,最近宋濂都教他什么了?
朱标说,仁孝为上,重礼教轻刑法。一个君主,用仁爱之心去驭天下,则四海臣服,天下歌舞升平。
朱元璋哭笑不得提醒太子别忘了,仁政并不能使坏人感化过来,仁政只对善良的人有用。韩非子主张二柄,也就是两样法器,一是刑,一是德,杀戮为刑,庆赏为德,不要说老百姓,就连那些大臣都一样害怕刑罚。
朱标不以为然,他说先生以为,重刑只能收一时之效,重德才会长治久安。
“又是先生说。”朱元璋哭笑不得地心里暗自动了这样的念头,也许该给他换一位老师了,将来把太子教育成宋老夫子那样的人,怎么管理天下?
朱标却十分尊崇他的师傅,自认为若能把宋先生的品格、学识和为人学到手,那可是天大的喜事,但太难了。说这话时,眼中充满了崇拜的神采,这更令朱元璋忧心忡忡。
朱标察觉了,问:“父皇好像不大喜欢他?”
朱元璋所答非所问,叫宋濂专心带人去修元史不好吗?
朱标固执地要跟先生学,他的文章好,淡泊、宁静,不造作,文如其人。他从来不求什么,他才是五品官,他说父皇对他其实太吝啬了点。
朱元璋对宋濂说不出是褒是贬,他清高,给他官他不当。当了翰林院学士了,连朝都不上。
皇上父子正为宋濂的为人、品格、见解、学识争执不休时,宋濂迈着夫子的方步来给太子授业了。
朱标说他最喜欢先生为别人写的墓志铭和序、跋。真是好文章,读起来如甘泉沁入心扉。其实朱元璋也有同感,但不能支持太子。
朱元璋强调当皇帝不靠文章。
朱标提到他人品也好,从不讲别人坏话,从不说谎。
“这倒是。”朱元璋也有另外的看法,从不讲别人坏话,也有明哲自保的用意呀,人无完人,不要因为是太子师,便一俊遮百丑了。
这时宋濂进来了,一怔,说:“没想到皇上在这儿。”他行了礼后,朱元璋单刀直入地问:“这几天,先生不去早朝,午朝也不见影,怎么回事?”
宋濂说,他不惯于官场礼仪,他这官本来也无实职,皇上何必苛求。
朱元璋很不高兴地说:“上朝,是人臣起码的规矩,这还叫苛求?”
朱标为他的座师开脱说,礼贤馆的先生是国宾,不能与卿大夫等同。
朱元璋开玩笑地说:“今后不好办了,朕才说一句,就有人替先生辩解了。”几个人都乐了。
朱元璋转而严肃地问:“昨天晚上先生干什么去了?去进学街喝酒了吗?”
宋濂心里一动。章溢家住在进学街,他昨天晚上也果真在他那里做客。他心里暗想,朱元璋精明心细到如此地步,是国家之福,也未尝不是士大夫之忧啊。
宋濂说:“章溢过生日,到他那去喝了三杯。皇上连这小事也知道?”但他马上又笑了,“幸而我从不说谎,皇上连大臣家的泔水都有本事弄出来呀。”
朱元璋笑了,说:“过几天朕再为太子配一位师傅,先生编《元史》,有些顾不过来。”这是他对太子釜底抽薪的第一步。
宋濂淡然地说:“怎么样都行啊。”
第七十章
李善长的致仕与众不同,同时履新,这是体面的结局吗?女传胪给皇上开的一副药,皇上看来是剧毒。吊在辘轳上的爱情本来就是三玄的。
李善长一直处于惶惶然的噩梦中。李彬事件使他日渐失宠,杨宪出事,虽未直接牵扯到他,但首辅有逃不脱失察之过。向汤和借用三百兵丁做工匠的事,以及那桶出自他家阴沟的臭泔水,叫他喘不过气来。
他只能消极地等待,有一天皇上会厌烦地摆摆手,让他回家去抱孙子。
朱元璋早该下决心处置李善长了,敲打他、冷淡他,也算一种暗示,他希望给李善长一个体面的结局,由他自己叩请告老致仕。可这个李善长居然硬扛着,死猪不怕开水烫。
朱元璋刚刚写完“李善长”三个字的纸条挂在屏风上,胡惟庸到了:“皇上叫我?”
这已是掌灯时分了,太监正在殿里殿外点起明烛来。胡惟庸用眼一溜,就看到了那张字条,但他不动声色。他早摸透了朱元璋的心思。
朱元璋像是对胡惟庸说,又像自言自语,这人老了一定昏聩吗?不然怎么会有老耄昏聩这个词呢?
胡惟庸说,有的人老,是从躯体上老,有的人是从心上老,前者不能算老,心态老朽了,才是昏聩了。他的呼应含而不露,意思却到了。
朱元璋又问他昏聩和利令智昏有何不同?这当然也是明知故问。
胡惟庸说,利令智昏是坏人,昏聩不是。他料想朱元璋是在往李善长身上引。
果然,朱元璋说,李善长大兴土木,又包庇李彬,与杨宪勾勾搭搭,向汤和借兵肥私,是昏聩还是利令智昏?这问得太具体了,叫胡惟庸很为难,但他不能给朱元璋一个落井下石的印象。谁都知道,李善长朝不保夕,在相位上呆不了几天了;最有可能接替他,也最为李善长鼎力推荐的杨宪又是那么个下场,胡惟庸的晋升几乎是人人都看明白的了。越是这种时候越该谨慎,不能给朱元璋一个急不可耐的印象,更不能使人感到他胡惟庸不择手段。反倒是应当说恩人李善长几句好话。胡惟庸了解朱元璋的脾气,他决不会为几句不咸不淡的好话的所左右而改变决心,这好话也就无伤大雅,也无损他的升迁了。
胡惟庸说,丞相当然不是利令智昏,连昏聩也不是,是被人蒙蔽,一时糊涂。
“你到底向着你的恩师。”朱元璋便明言了,他确实老了。朱元璋想暗示胡惟庸,要让李善长自己提出来告老还乡。
胡惟庸说,李丞相不同于别人,是开国元勋,功勋卓著,即使真的老朽了,摆在那里也好看。这个“摆”字用得极有学问,朱元璋听了很舒服。
朱元璋决心已下,如果有人自恃有功,为所欲为,那朕会毫不犹豫地让他回家抱孙子去。
胡惟庸眼里闪过亮点,却一闪即逝。他用忧虑的口气说,他走了,杨宪处死了,朝中还真找不出能代他为相的人了呢。
朱元璋脱口而出,叫他和汪广洋干。
胡惟庸夸张地瞪大眼睛,半晌才跪下去说:“皇上请三思。论资历、论才干,臣都不配,百官攻击我倒无所谓,到时候会说皇上不会选贤任能,有辱皇上名声。”
朱元璋说:“朕只要做了,就不后悔。你起来,朕告诉你,朕早有重用你的意思,有人说你虽精明干练,却叫人看不透。也有人说你口是心非,包藏祸心,你自己怎么说?”
朱元璋喜欢这样当面提出不好回答的问题。
胡惟庸说得十分得体,既不自夸,也不辩解,他说自己整天在皇上跟前伺候,皇上最能看透他。臣自己说什么都没有用的。
“也不一定。”朱元璋说他连自己的养子朱文正都没有看透,更不要说别人了。他用人,敢用,也敢罢。他警告胡惟庸,一旦坐了相位,有可能成为众矢之的,也可能大权在握忘乎所以,希望他是赵普,而不是赵高。望他好自为之。
这等于是单独对胡惟庸下了谕旨,接替李善长的相位已是板上钉钉了,多年的努力、多年的宿愿、多年的抱负,总算开花结果了。他既要在皇上面前掩饰住狂喜而不至于失态,一方面又要尽善尽美地表达出对皇上的感激和忠诚,最好的办法是流泪。他的泪腺还真帮他忙,顿时泪满双颊地跪在了朱元璋面前。
胡惟庸说:“陛下方才的教诲之言,我会铭记终生的。”
这时有值殿官递上一份奏疏,原来大将军蓝玉奏报,他已率兵攻占拉河,在那里屯兵驻防后,想回京面奏。
朱元璋接奏报在手,对胡惟庸笑道:“哪里是来面奏,是想媳妇了,也难怪,这些将领,这么多年屁股几乎没离开过马背。有些人还说朕重武轻文,没有武将驰骋天下,江山能打下来吗?今后可把轮休当成制度,让武将轮流回来休假,或者长期驻守在边塞的,可带妻小。
胡惟庸称颂这个办法可安武将之心,也尽人情,他愿领旨去办。
李善长还是识趣的,一经得到朱元璋的暗示,立刻连夜上了一道表,称自己年迈体衰,精力不济,继续为相监国,会误了社稷,故再三恳请告老还乡。
朱元璋在早朝的时候,叫值殿官当众宣读了李善长的辞官表。朱元璋说李善长功在社稷,不准他致仕,再三慰勉挽留。
李善长不傻,他周围的人也都帮他谋划。朱元璋的挽留不过是虚应故事、官样文章,是在表现他的不忘勋臣的恩宠,是在示恩,也是给这位开国老臣留够了面子,李善长岂可当真?
于是李善长又接连上了两道泣血顿首、诚惶诚恐的辞官表。朱元璋终于忍痛割爱,赐他荣归故里了。
这一天是李善长带着家口回老家濠州的日子。
长江边上一溜十几条大船整装待发,帆也升起来了。
陈宁、詹徽、陆仲亨、郭兴、费聚、吴桢等官员都来为李善长送行。李善长站在码头上,众官为他敬酒。
李善长眼含着泪,说:“老朽真不敢当,本来想悄悄走的,却还是惊动了各位。”
李善长心里有一种无以名状的失落感。皇上明知他今日启程返乡,却毫无表示,他本人不来,至少要委派一个钦差隆重地送上一程啊!最终皇上还是没给足他面子,也叫这些朋友同僚们看着冷清,这是他心里酸楚的原因。
郭兴说:“丞相劳苦功高,平时待我们如兄长,你今日荣归故里,岂能不送?”
费聚说:“你才五十七,怎么就不叫干了?”语中有不平之意。
陆仲亨用力踩了他脚一下。
李善长说自己老了,糊涂了,办了些让皇上不放心的事,此次归乡,当老守田园了,望各位好好尽职尽责,为皇上出力。
陈宁说:“说不定哪一天,皇上又会想起丞相的好处,一纸诏书召您回来呢。”
李善长苦笑说:“不可能了,覆水难收啊,覆水难收。”他把手里杯中酒全倒进口中,正要告辞登船,有人喊:“皇上来了!”
李善长一惊,举目望去,果见大路上黄罗大伞、卤簿仪仗浩浩荡荡而来。真的是朱元璋来送行了?他顿时感到少有的满足和荣耀,甚至对方才心中的抱怨都有自愧之感。
朱元璋的大驾惊动了来送行的百官,都跟在李善长身后向朱元璋拥过来。
当朱元璋走下帝辇时,见李善长、李存义和送行官员俱跪于地上,便招呼说:“都起来,你们跟着跪什么,你们和朕一样,是来送行的呀。”
众人起来后,朱元璋对身后的汪广洋、胡惟庸说:“我和胡丞相、汪丞相是来送李善长履任,而非归隐。”
大家都有点愕然,你看我,我看你,难道又不让他致仕了吗?
汪广洋说:“李丞相将是中都的监修官。”原来是这么个官儿。
此前朱元璋已颁诏在濠州兴建中都宫城,他要把自己的故乡也修成与金陵一模一样的宫城,使故乡披上皇家的圣洁之光,成为陪都。他今天送行时宣布李善长执掌中都修建之事,并说屈尊百室先生为社稷再出一把力,算是老骥伏枥吧。
这虽不是什么大差事,不可能与丞相相比,毕竟可以说李善长没有完全回家养老,皇上总算给他找了个营生干,也就心满意足了。朱元璋又说也有让他休息一阵的意思,说不定哪一天,你还得回来为朕出力呀!
这话虽不可认真,听起来却极舒服。
胡惟庸捧上了大印。李善长接任后,说:“谢谢皇上大恩,这叫李善长备加惶恐,只有鞠躬尽瘁为国尽力了。”
朱元璋把他拉到一旁,亲热地说:“还有件事要借丞相大名呢。”
李善长说:“皇上请明示。”
朱元璋说他从前就相中了常遇春的女儿,想聘为朱标的太子妃,没想到常遇春会猝死,就没来得及下定。朱元璋想请李善长充当这个媒人。
李善长心情大为改观,他笑着说这是皇上看得起他,岂有不愿之理。他此行正好去常遇春老家,就按御旨下定。
几个太监在云奇带领下抬上了两口红箱子,朱元璋说:“这是聘礼,请带上。”
对于李善长来说,今天是不快的日子,却意外地得到了补偿。
转眼间会试、殿试结束了,举世瞩目的召见新科进士庆典在华盖殿隆重举行。从朱元璋起,大臣们全穿上了大典的吉服,华盖殿里外张灯结彩,细乐奏鸣,钟鼓之声悠扬,南京城如同过节一样洋溢着喜悦气氛。
刘基恭恭敬敬地送上了名单及考卷,说:“启禀陛下,下面要上殿来的是会试中二甲的第一名传胪。”
朱元璋拿起那张差不多有一丈长、三尺半宽的宣纸卷子,先看糊名处,不禁念出声来:“楚方?又是他?”
刘基说,正是那个给皇上呈上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举子,他的才学不古板,立论又振聋发聩。
朱元璋看了看卷子不禁大加称赞,楚方果然才学出众,这文章写得不落俗套,朱元璋说他历来不喜欢因袭。他传谕,宣他上殿。
刘基亲自站在丹墀上喊:“宣会试二甲一名传胪楚方上殿!”这喊声一递一声地传出去,喊声余音久久不散,一时钟鼓和乐大作。
少顷,明眸皓齿无比端庄的楚方玉款款上殿来,她的风度吸引了殿下群臣所有的目光。
在众人瞩目下,楚方玉站到了朱元璋面前。
朱元璋满心欢喜,竟破例地开了句玩笑:“传胪今天不是来献珍珠翡翠白玉汤的吧?”
楚方玉笑笑说,珍珠翡翠白玉汤不过是果腹之物。今天想在圣上跟前说的是一味药。
“一味药?”朱元璋不解,众人也都不知所以。
“治国如同医病,”楚方玉说,“开对了药方,可治病救人;出治国良策,可免灾祸,富国强民,这也是方子。”原来她开的是治国之方。
朱元璋说:“有理。”他又看了看卷子,“你叫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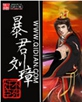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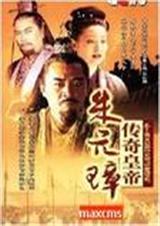
![[综琼瑶]璋显龙心封面](http://www.8btxt.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