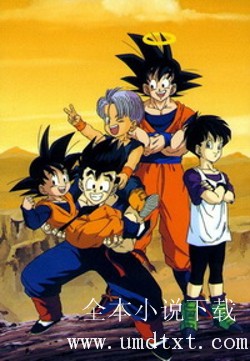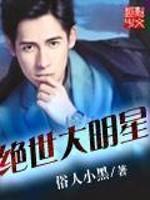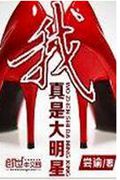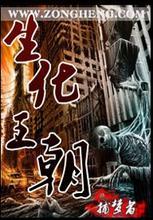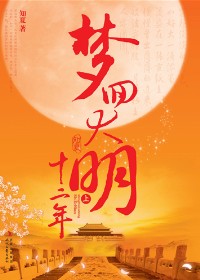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第3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教民榜文》中他规定,一些次要的司法事务,例如家务、骂架和斗殴等纠纷都可由老人和里甲来审断。官员们不许干预诉讼过程,也不许接管判决事宜。如果地方当局干预了关于老人的案件,其他老人可以直接奏报给皇帝,那么,官员们可能自动地被牵连进这名受审老人罪行中去。当然,人命大案等还应报告政府来审理。
第五节 “激进主义”的“幼稚病”
在全帝国范围内掀起这样疾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朱元璋自然有他的想法。在一则命令中,朱元璋宣布了他村长式的设想:“如果天下百姓都听我的,认认真真照这个命令办,那么不出一年,天下的贪官污吏都变成好官了。为什么?因为良民时刻监督,坏人不敢胡作非为,所以各级官员都不得不做好官、做好人。”
在另一个地方,他这样说:“呜呼!所在城市乡村耆民智人等,肯依朕言,必举此行,即岁天下太平矣。”
这当然是典型的“如果……就”的逻辑。依靠社会底层来监督官员,这样思路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朱元璋没有认真考虑把这种监督机制化,常态化,而希望仅仅用一次群众运动来解决所有问题。
“激进主义”在中国这个“中庸”大国里有着十分深厚的土壤。“激进主义”是一种“幼稚病”。就像热恋中的青年男女相信只要有爱情,两个人身上其他的一切不谐调都不成问题一样,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者也相信,道德激情可以击败一切不义,只要在政治操作中倾力贯注和绝对恪守道德原则,实际政治中的任何困难都不难克服。看事过易、意气用事、态度偏激、思想狂热、喜爱暴力是它的特点。它拖累着中国政治一直不能脱离中古式“伦理政治”范畴而进化成“世俗理性政治”。
“理性”并不是朱元璋先天素质中的缺项,他在战争中头脑之清醒,次序之清楚,充分证明了他理智的强大。然而,越到晚年,他的政治思维中“激进主义”的狂想就越来越成为了主旋律。
毕竟,朱元璋是人而不是神。在群雄并起的强大压力之下,他能强迫自己每分每秒都恪守理性的指挥,在重重困难中苦心孤诣寻找那条唯一的生路。登上帝位后,虽然他一再提醒自己要“小心”、“谨慎”,然而由于外面的压力都已消失,天性中那长期压抑着的“急躁”、“竣切”还是不可避免地浮出水面。而屠戮功臣、牢狱百姓之顺利之容易之几乎没有遇到反抗,又大大强化了他的自信心和浮躁感。
坐踞极尊、四周毫无约束,这种地位对人性的腐蚀朱元璋也不可能避免。于是,一方面,他仍然能兢兢业业、宵衣旰食,强迫自己忘我工作,另一方面,他却没有能力再把那个强大而盲目的“本我”压制回“理性”的控制之下,反而越来越为“本我”而控制。性格中天生的“狂暴”与乡村视野中天然形成的“泛道德主义”倾向与“权力万能”幻象合流,造成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现象:皇帝坐在九重之上,伸出手来在最低的草根阶层里放了一把火,异想天开地希望用局部的“无政府主义”这把烈火来彻底烧毁官僚主义的土壤。
第六节 史上最大的惩贪浪潮
诏书发布下去了,天下却没有出现朱元璋想象中的“群起响应”的局面。
毕竟,自有国家以来,中国老百姓就一直匍匐在官员脚下。面对皇帝的“造反”号召,他们一时不知所措。虽然皇帝一再发布“呜呼!君子目朕之言,勿坐视纵容奸恶愚民”的殷切呼唤,他们还是将信将疑,愣在当地不敢动。
朱元璋火了,他自然有他的办法。洪武十九年,他严厉惩罚了镇江市的一些市民,原因是他们没有按他的要求,积极捉拿坏官韦栋,而听任他在镇江胡作非为,直到这个坏官被皇帝亲自发现。皇帝发布诏书说,因为这些市民不听他的话,所以“将坊甲邻里尽行责罚搬石砌城”。皇帝得意洋洋地说:“有罚款把家罚得精光的,有的家破人亡,有的不及去搬石就被我处死!”
这就是朱元璋的动员方式。
他知道,这种方式在这片土地上当然最有效。同时,对那些壮着胆子,捉拿官员的“吃螃蟹者”,他立刻大加奖励。常熟县百姓陈寿六串同自己的弟弟和外甥,把县里的恶劣吏员顾英捉住,送到南京,朱元璋大为高兴:
在《如诰擒恶受赏第十》中他说:
前者《大诰》一出,民有从吾命者。常熟县陈寿六为县吏顾英所害,非止害己,害民甚众。其陈寿六串弟与甥三人擒其吏,执《大诰》
赴京面奏。朕嘉其能,赏钞二十锭,三人衣各二件。更敕都察院榜谕市村,其陈寿六与免杂泛差役三年,敢有罗织生事扰害者,族诛。若陈寿六因而倚侍,凌辱乡里者,罪亦不放。设有捏词诬陷陈寿六者,亦族诛。陈寿六倘有过失,不许擅勾,以状来闻,然后京师差人宣至,朕亲问其由。其陈寿六其不伟欤?
在这动员加恐吓之下,朱元璋兴起的捉贪运动终于在各地兴起。懦弱的老百姓居然敢对官员下手,这有中国以来人民所不敢想象的翻天覆地的现象终于出现了。在通往南京的路上,经常出现一群衣衫褴褛的百姓押解着贪官污吏行走的情景。也有贪官逃回家里,被亲戚捉住,送到京师,朱元璋得意地说:
为《大诰》一出,邻里亲戚有所畏惧。其苏、松、嘉、湖、浙东、江东、江西,有父母亲送子至官者。有妻舅、母舅、伯、叔、兄、弟送至京者多矣。
于是,大明天下出现了这样的情景:一直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员们要对百姓下跪求饶了:
北平布政司永平府滦州乐亭县主簿汪铎等设计害民,妄起夫丁,民有避难者,受财出脱之,每一丁要绢五匹,被高年有德耆民赵罕辰等三十四名帮缚赴京。行间,有的当人、说事人、管事人何波等十名,翻然改图,格前非心,一同辅助耆老赵罕辰等四十四名,将害民工房吏张进等八名帮缚起行。
去县四十里,其县官主簿汪铎等追赶求免,谓耆老言:“我十四岁读书,灯窗之劳至此,你可免我此番,休坏我前程。”呜呼愚哉!孰父母生此无藉不才之徒,官于是县,是县民瞻,今既不才,为民所觉,乞怜哀免于耆民,纵然得免,何面目以居是任?呜呼!兴言至此,虽非本人,凡听读者亦皆赧焉。贤人君子,可不为之戒乎?(《三编·县官求免于民第十七》)县里的主簿,相当于今天的县委办公室主任,科级实权干部,平日在地方上怎么耀武扬威就可想而知了。而今被群众揪出来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立刻露出了一副可怜样,苦苦哀求:这个科级干部,是我从十四岁读书考学辛苦换来的,乡亲父老可怜可怜我吧,不要让我断送了大好前程!
真是平日只见民求官,怎想还有官求民!在朱皇帝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被封建统治颠倒过去的世界又颠倒回来了!
第七节 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从洪武十八年到洪武二十八年,皇帝与百姓密切配合,严厉打击贪污腐化。那个时候,几乎无日不杀人。有些衙门,因为官吏被杀太多,没有人办公,朱元璋不得不实行“戴死罪、徒流办事”,“戴斩、绞、徒、流刑在职”的办法,叫判刑后的犯罪官吏,带着镣铐回到公堂办公。
他不仅动用刑狱,严加惩处,而且还法外加刑。罪行严重的,处以墨面文身、挑筋、挑膝盖、剁指、断手、刖(yuè)足、刷洗、称竿、抽肠、阉割为奴、斩趾枷令、常号枷令、枭首、凌迟、全家抄没发配远方为奴、族诛等各种非刑。
在洪武时代做官,真的是一件极为危险的勾当。据说,皇帝每天上朝,如果把玉带高高地贴在胸前,这一天杀的人就少一些;如果把玉带低低地按在肚皮下面,这一天准得大杀一批,官员就吓得面如土色。在这种恐怖气氛中,不论大官小官,个个胆战心惊,不知什么时候就有大祸临头。传说当时的京官,每天清早入朝,必与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回家便举家庆贺,庆幸又活过了一天。
原来是天底下最热爱做官的读书人们此时也视仕途为畏途。他们“以溷(hǔn)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多不乐仕进”。有的家里有好学之子,怕被郡县所知,弄去当官,反而叫他们休学种地。有的为了避免被强征出仕,至自残肢体。
不少人在时过境迁之后,回想起洪武朝的情景,还心有余悸。如当时监察部副部长左佥都御史严德珉,在洪武朝因病要求辞职,朱元璋怀疑他是装病,将他黥面发配到广西南丹。后来遇赦放还,活到宣德朝,回忆起当年的经历,说先时国法甚严,做官的常保不住脑袋,这顶破帽不好戴啊!说完还北面拱手,连称:“圣恩!圣恩!”
能得到“圣恩”的人太少了。连不少受过朱元璋多次表彰的清官,也因为牵连到“空印案”之类毫无必要制造的大冤案中送了命。济宁知府方克勤是有名的清官,一件布袍穿了十年也没有换新的,因为牵连到了“空印案”里,被朱毫不留情地杀死。户部尚书滕德懋(mào)被人举报为贪污,朱元璋迅即把他处死,之后剖开滕的肚子,想看看这个贪官肚子里都有些什么。孰料剖开之后,发现里面全都是粗粮草菜,只好悻悻地长叹一声:“原来是个大清官啊!”
朱元璋清楚地知道自己杀的人里有许多无辜之人,然而他的原则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他要的是一个纯而又纯的与贪污绝缘的官僚队伍,要的是不惜任何代价实现这样一个在别的王朝没能实现的人间奇迹,而不是什么公平正义。如果能达到这个目标,多少人冤死,在朱元璋是无所谓的。
第八节 越反越腐的反腐怪圈
虽然力度如此之大,然而朱元璋期望的纯而又纯的状况终于没有出现。
在朱的政策下,想在官场全身而退几乎就不可能,所以有些人,认为反正动辄得咎,不如趁早捞一把算了,反而加紧贪污搜刮的活动。他们“当未仕之时,则修身畏慎,动遵律法。一入于官,则以禁网严密,朝不谋夕,遂弃廉耻,或事掊克,以修屯田工役之资”,享受一天是一天,于是贪污事件仍然层出不穷,弄得朱元璋连声哀叹:“似这等愚下之徒,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
连朱元璋寄以最大希望的村民自治也很快破产了。因为有了权力,可以处理一般的案件,老人也很快腐败起来。他们毫不自重,以权谋私,甚至贪图酒食贿赂,“公道不昭,贞邪莫辨,妄张威福,颠倒是非”。
至于擒拿犯法吏员一举,负面作用也很快反映出来。群众运动的火候是最难掌握的。不久,就有许多地方官为了政治利益,威胁利诱百姓们保举自己,打击他人,更有许多地方群众为了抗税不交而把正常工作的税收官员捉拿到京。这类事情远比真正捉到的贪官要多,弄得朱元璋一个劲地呜呼不已。
朱元璋自己多次承认他的思想教育工作收效甚微。他在谈及《大诰》前两编施行情况时说道,“迩来凶顽之人,不善之心独未向化”,“奸顽之徒难治,扶此彼坏,扶彼此坏。观此奸顽,虽神明亦将何如!”观洪武二十一年至三十一年所颁布的榜文,也可看到朱元璋的目标没有实现,让他不满的现象比比皆是:“县州府行省官吏在职役者,往往倒持仁义,增词陷良”,“凌虐良善,贪图贿赂”;“奸顽小人,恃其富豪,欺压良善,强捉平民用为奴仆,虽尝累加惩戒,奸顽终化不省”;“无藉之徒,不务本等生理,往往犯奸做贼。若不律外处治,难以禁止”。
皇帝晚年,对自己的暴力惩贪曾经有过困惑和动摇。洪武二十三年,他对刑部官员说:“愚民犯法,如啖饮食,嗜之不知止。设法防之,犯者益众,惟推恕行仁,或能感化?”
虽然朱元璋屡次重申,“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后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即以奸臣论无赦”,还是改变不了他曾经希望世世代代指导人民的《大诰》很快被弃如敝履的现实。虽然没有哪个后世皇帝敢明确宣布废除《大诰》,但在朱死后,再也没有发挥过实际作用。到明代中叶,《大诰》
已经鲜为人知。曾经发行上千万册的这本宝书,到明末在民间几乎一本也没有了。这也许是朱元璋从来没有想到的。
更让朱元璋没有想到的是,虽然他在世时,贪污腐化现象得到了一时的抑制,然而却积蓄了巨大的反弹能量。在他死后,腐败又迅速发展起来,大明最终以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王朝之一被列入历史。明朝之亡,即缘于此。
第十三章 死亡名单:疯狂屠杀功臣的始末与细节
第一节 开国六公二十八侯
洪武三年,徐达大败明王朝最后一个劲敌扩廓帖木儿,元顺帝也病死于蒙古草原,明朝天下大定,朱元璋长长出了口气。这一年十一月,他在奉天殿举行盛大仪式,大封开国功臣。一口气封了六公、二十八侯。
六公全是淮西人:韩国公李善长(他虽然原籍歙县,但后来徙居滁阳,在渡江前已经投奔朱元璋,所以也被视为淮西老臣),魏国公徐达,郑国公常茂(常遇春之子),曹国公李文忠,宋国公冯胜,卫国公邓愈。
二十八名侯爵也基本都是淮西人,且以凤阳人为多。朱元璋出生在钟离东乡,后来搬到西乡,也就是后来的凤阳县广德乡东湖里,十二岁时搬到太平乡孤庄村。中国地图上根本找不到的这几个小小乡里,后来成了著名的“将军乡”,共出了十二名侯爵:中山侯汤和、巩昌侯郭兴、武定侯郭英和永平侯谢成,都是广德乡东湖里人,朱元璋的同村“发小儿”。延安侯唐胜宗是广德乡毛城村人,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同乡”。吉安侯陆仲平是太平乡义城村人,江夏侯周德兴、燕山侯孙兴祖、临江侯陈德都是太平乡孟家庄人。济宁侯顾时是太平乡涂山村人,凤翔侯张龙和航海侯张赫是太平乡焦山村人。
中国东部这块最贫瘠的土地,一时之间却成了功臣名将的富产区。朱元璋乡土情结十分浓重,只要一听到濠州话,他就觉得异常亲切;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