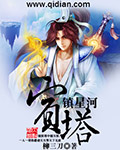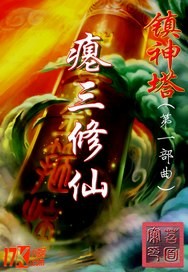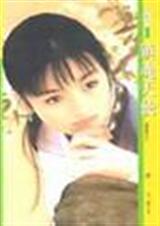南河镇-第2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每侧有四根椽依次向上换翻,如果财东娃把日子过烂包了,或者是穷汉娃把日子过红火了,人们都会形象地感叹到:“唉,过日子就跟打墙的板一样,上下翻!”
河东堡郭福寿拿出金条办学的事,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河西堡老地主捐地做校址,却是不争的事实。他捐出的二十亩地紧挨着九子滩,据说原来也是没人要的盐碱地。
把自家茅房和牛圈里的土粪,以及打掉的塌塌炕和塌塌锅头,一有空就套上牛车拉到就近的滩地里扬开,回来时又顺便把滩地里的盐碱土捎回家垫茅房垫牛圈,简直成了地主家人老几辈的光荣传统。这个光荣传统究竟是从哪一代留传下来的,包括老地主在内,三女河两岸的人谁也说不清楚。直到老地主在他五十岁那年给这些滩地里扬麦种时,人们不但没有觉醒,反而还嘲笑说这老汉粮食多得没处搁了,烧包得胡成精呢。当嫩绿的麦苗齐蓬蓬地顶出地皮时,一般人这才明白了,同时也吃惊了。当地主家场里扬出的麦堆,黄澄澄的而且比往年大了一倍多时,一般人又开始张嘴了瞪眼了。当他们知道盐碱地原来也可以改造为良田而纷纷效仿时,为时已经晚了。官府的人拦住了他们:“这几千亩滩地是官产。要用得掏钱买。”
举人陈德润陈老爷在河西堡办学的事,惊动了渭河南的五六十个大小村庄。向来自以为是的南河镇人,从此再也不敢自以为是了。千百年来南河镇人在自以为是的同时,也隐隐约约地感觉到美中还有些不足,觉得似乎还欠缺点什么。但这点“不足”却一直为“美”所掩盖,自己到究欠缺的是啥,没有一个人认真地思考过,自然更没有一个人认真地寻找过。现在他们终于明白了,自家缺少的,原来就是举人陈德润陈老爷要办的学堂。举人老爷在“美”中发现了这个“不足”,并已着手在弥补这个不足。为了使美玉无瑕,那些觉悟得早的,已有人拿出了自家的金条;那些反应得快的,已有人捐出了自家的“刮金板”。那些觉悟晚反应也迟钝的,在觉悟后在反应过来后,也想到应该做点什么或拿点什么。于是有钱的想到了自家的银子,带手的想到了自家的手艺,没钱也不带手的,也想到了自家的力气。渭河南岸的人们,终于学会了思考。
帮工的越来越多,打墙的架子,也由一副增加到三副。锤子打击黄土发出的砰砰咚咚的闷响,瓦刀敲击砖块发出的叮叮当当的脆响,锯子撕咬木头的咝咝声和刨子舔啃木料的嗤嗤声,与镢头碰到铁锨而发出的金属的撞击声,以及人们的吆喝声混杂在一起,打破了倒春寒带来的静谧。木工房里洋溢着木屑的气息,从锯缝里撒落的,是细细的锯末;从刨口里吐出的,是长长的刨花。空气里弥漫着黄土的气息,白灰的气息和青苗被踩断后发出的清香气息。人们来这里的目的,虽然不纯粹是为了钱,但最后他们还是拿到了钱。陈德润心里跟明镜似的,他们的孩子需要读书,他们的孩子也需要吃饭。
济世堂里进进出出的人,也在与日俱增。不排除有些是来看病的,有些是来抓药的,但更多的却既不是来看病也不是来抓药,手头宽展的,十两八两地捐着银子;囊中羞涩的,也码着他们的铜圆或麻钱。瓜子不饱见仁(人)心。银子也好麻钱也罢,都是一片心意,是一颗已经觉悟了的“心”。
颠着小脚,柳叶也来到了济世堂。拿出三十两银子后,她歉意地对老秀才说:“我家里没人出不上力,用这点钱聊表心意。”老秀才接过银子说:“柳妈妈,话可不能这么说!余儿跟子明不都在工地上吗?他们可是你的亲女儿亲女婿!”记完账他将收条递给柳叶并接着对她说:“既出了钱又出了力的,你还是第一家!”
西街上那个吓跑土匪的老汉,其三个儿子虽也都是水性极好的船工,却因家里穷在当地问不上媳妇。不久前在逃荒的人群中,老汉给他的大儿七十子跟二儿子八十子,各收揽了一个女人,并求爷爷告奶奶东挪西凑着,总算是给他们成了个家。没成家时,三个儿子还能跟老人相依为命,成家后老大跟老二的媳妇,却尿不到一个壶壶里了,整天打破头吵翻天地闹着要老汉分家。分就分吧!那些说书的说到三国,不一开口也是“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么?连天下都是如此,又何况一个破家!
挣家不匀分家匀。分什么呢?一人一间破草屋,自然是用不着再分的。除此而外,再也找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因此破费请人说话,也就免提了。老三玉团还没成家,所以暂时还是跟老爸一起过。六个碗不多也不少,正好每人一个,各拿各的也无需多说。数来数去后筷子却只有五双,儿子媳妇们正不知如何是好,老汉却说:“你们拿你们的。甭管我。”说完便摸出已经没了把把的切菜刀,又从光骨朵扫帚上抽下了一根竹竿,手起刀落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儿子们拿在手里的碗,都打得豁豁牙牙的,三双筷子也都弯成了背弓蛇腰;两个媳妇的碗却完好无缺,筷子看起来也还端正,而且还白生生的。这是在前不久娶新媳妇时,他们家新添置的家当。
最让老汉为难的,是锅锅灶灶。如果有两套的话,老大跟老二每家一套,自己跟老三或提前或缓后,可借用老大或老二家的,反正谁家也不会一把火从早烧到黑,闲着还不是闲着。问题是眼下只有一套,给谁老汉都觉得不妥,于是便留给了自己。可娶媳妇时拉下的那一河滩烂账,却咋说也不能留给自己,于是二一添作五,分给了老大和老二。理由再充分不过也再简单不过,因为他还要给老三娶媳妇。七十子和八十子虽然都没言传,两个媳妇却不愿意了:“人家分家都是分钱分地分庄子分房,我先后俩倒好,钱没分上房没分上地没分上庄子也没分上,倒是分了一河滩的烂账!”你有来言我有去语,老汉自然有他的道理:“人常说五年六月七日八时,我都快奔七十了,是活一天算一天有今天没明天的人了,把烂账分给我即便是我能成,但那些债主们人家能答应吗?到时我两腿一蹬,你教人家挖抓谁去?父债子还天经地义。更何况这些烂账是给你们娶媳妇拉下的,又不是我给你们办后妈拉下的。常言说的好,好儿不在家当,好女不在嫁妆。你们还是各想各的办法,各过各的日子吧!”
看到人家纷纷给学堂里捐钱,老大老二弟兄俩急得猴抠脸而腰里却都是一文不名,正巧这时门外传来“收废铜烂铁打打锅”的吆喝声,他们便不约而同地盯上了各自刚背回家的,还带着红锈的铁锅,于是又同时找到他爸,吵吵嚷嚷地说还不如一块过。老汉开始坚决不答应,当知道儿子要砸锅卖铁给学堂里捐钱时,这才感动得流着老泪点了那颗已经苍白的脑袋。八十子正要摸砖头砸锅,却被他哥七十子给拦住了:“生铁能换几个钱,还不如折点钱把锅退掉。”
刚背回家的铁锅,又被弟兄俩背回到杂货店。杂货店的掌柜开始咋说也不给退,但一张嘴抵不住两张嘴的软缠硬磨,最后才答应按八折退货。当听说弟兄俩退锅是为了给学校捐钱时,掌柜的非但没有打折,还给哥俩倒贴了四钱银子补足了二两。
砸锅卖铁,原是人们顺口说出的一句赌气话,而这句赌气话在南河镇,却被那哥俩变成了活生生的事实。从来都是被人取笑的老汉一家,虽依然还是穷困潦倒,却从此不但不再被人取笑,反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敬重。在南河镇一带,这个掌故还被人们作为乡土教材,一代又一代地影响教育着后人。
孙兰玉跟菊儿、余儿和明儿,都在工地上帮厨。余儿明儿是先后俩,跟菊儿又都是大姑弟妹,这三个儿时的朋友,如今真的成了一家人亲姐妹。盖学堂又使她们有机会整天厮守在一起,重新成了不拆把儿的胡萝卜。余儿跟明儿虽然都已做了妈妈,但俩人仍像两只巧舌多嘴的鸟儿,一天到晚嘁嘁喳喳的,似乎有永远也说不完的话题。
菊儿的二儿子叫郭德玉。郭德玉跟郭福寿像极了,跟他的大哥郭德厚,更像是出自同一个模子。出生前的郭德玉虽不能确定到底是谁的,但在菊儿的希望中,他应该属于谢铁成而不属于郭福寿,因为谢铁成尚无一男半女,而她已经给郭福寿生了个顶门杠子,也算是对得起他,也对得起他们老郭家了。在菊儿的感觉中也是如此,因为谢铁成跟她在一起的时间毕竟比郭福寿多得多,而且这个打铁汉子,又比郭福寿壮实得多也强悍得多。既然谢铁成的种子饱满,耕耘多播种也更多,果实理所当然地非他莫属了。这一点菊儿深有感受,也只有她才会有这种感受,但事实上郭德玉并不属于强者,而是属于弱者。希望归希望感觉归感觉,希望和感觉都改变不了这个铁的事实,而铁的事实又大出了菊儿的意料。
第十章三女河顺水送木 九子
刚出生那阵,郭德玉既像谢铁成又不像谢铁成,既像郭福寿又不像郭福寿。菊儿弄不清,郭福寿跟谢铁成当然更弄不清他到底应属于谁,但他们却都跟菊儿一样疼爱着他,特别是谢铁成,他就是再忙,每次也要给孩子买点东西,而绝不会空着手回来;即便是再累,他都要抱抱他并亲个不够。
一般的打铁汉子,似乎都生硬而粗鲁,但谢铁成的感情,却是那样的丰富而细腻!
月月娃儿丑似驴。刚生下的孩子都红赤赤的,像个没皮的老鼠,看上去百球一个样又百球不一样。随着一天一天的长大,郭德玉一天一天地在变化,菊儿也一天比一天更加不安了。事与愿违,这孩子没有越来越像谢铁成,而是恰恰相反,他越来越像郭福寿了。虽一如既往,郭福寿跟谢铁成都爱着、疼着这孩子,但细心的菊儿,却还是觉察到他们那些难以掩饰的细微变化。郭福寿本来就感到有负于谢铁成,这孩子如果越来越像谢铁成,郭福寿或许能从中得到一些平衡,但事实让他的心理天平非但没有得到平衡,反而更加的倾斜了。谢铁成虽然照样地亲着疼着孩子,照样地给他买着东西,但却还是难以掩饰他内心的失望与落寞。有几次去陪郭福寿,菊儿都被拒之于门外。她也明白他是一片好意,于是只得又默默地回来陪谢铁成,并发誓一定要给谢铁成生个顶杠子。
如今菊儿又有了,并且身子日渐沉重。然而比身子更为沉重的,却是心情。孙兰玉不断地安慰她说:“这是由不得人的事,你可千万别甭老是挂在心里,这样既伤大人又伤孩子。啥都在其次,最重要的,是大人跟孩子的健康。若果真是谢铁成的,孩子不健康,你可就更对不住他了。退一万步说,即便不是他的,只要你身体好,还可以再生嘛!如果你的身体垮了,谢铁成他,可就真的没指望了。到时候更对不住他的,就是你。你可得千万保重自己的身子骨。啊——”孙兰玉的一番道理,可以说再透彻不过,但菊儿却依然还是忧心忡忡:“我倒没啥,只怕铁成他。。。。。。”孙兰玉说:“铁成那儿由德润去跟他说。这你放心!铁成是个明白人,依我看不会有啥问题的。”
但愿上天有眼,能使善良的菊儿如愿。
这年的气候,出奇的反常。去冬没见一片雪,今春又没落一滴雨。学堂的围墙已经合拢,教室的山墙也已高过檐墙并正在收梢。当老木匠正在为今年的天气好而暗自庆幸时,不想老天说翻脸便翻脸,雨,已经黑明不停地连着下了四五天,却仍然看不到一丝转机。正街和东街的路面虽然泥泞,但在绕来拐去后,却还可以勉强通过;而被车轧马踏的西街上,却已是积水及膝,人们更是无法越大门一步。那些年久失修的房屋,也都跟筛子一样外面大下屋里小下,外面停了,里面却还在滴答,用来接水的盆盆罐罐也已宣布告罄。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前两天还在为“久旱逢甘霖”而欢呼雀跃的大人孩子们,如今又不得不埋怨和诅咒起“贵如油”的春雨来。
过犹不及。久旱有久雨,汛期提前了,建校工程却被迫停了下来。
济世堂里,老神仙老秀才陈德润孙兰玉和郭福寿等,正谋划着天晴后进山拉木料的大事,但老木匠这个关键人物,却迟迟不见闪面。小相公正待去请,却与浑身上下跟泥猴似的一个人,撞了个满怀。以为是个疯子,小相公正准备将他推出门外,不想反被他推了个趔趄:“快!三女河涨水了!”
闻声众人大吃了一惊。来人并非疯子,而是老木匠。
“兄弟,你咋弄成这摸样?”老神仙吃惊地问道。
“大家都急死了,你却还有心情去看水涨河塌!”老秀才也埋怨道。
“大叔,河水到底有多大?”陈德润急切地问道。似乎只有他,领悟了老木匠的意思。
“半河水。咱们用,足够了。赶紧准备牲口。我这就去叫人。”说着老木匠折转身就往外走。
“大叔,洗个脸换了衣服再走。小心凉着!”双手端着水盆腋下又夹着衣服的孙兰玉,正好赶了出来。
“来不及了。。。。。。”话还没说完,老木匠已经出了济世堂。当他的话跟他那泥猴似的身影,被一块淹没在雨雾中时,大家这才惊醒了过来。
其实老木匠比谁都起得更早,他头戴斗笠身披蓑衣打着赤脚来到了工地,土打的围墙虽然倒塌了不少,但一砖到顶房子却损失不大。耽误了工期,老木匠的心情比天气还要坏,倒塌的围墙又给他平添了些懊恼,脚下一时不留神他竟滑了一跤,爬起时浑身都是泥浆,老木匠活象一尊泥塑。连他自己也不曾想到,正是这一跤,才甩掉了他刚才所有的懊恼。浑身的泥浆就留给老太爷了,让大雨慢慢地去冲刷吧!老木匠跌跤爬坡地来到了三女河边。果然不出所料!那刚涨起半河水使他欣喜若狂:“这一跤跌得好,跌得值!”自言自语地嘟哝了一句后,老木匠立即赶回了济世堂。
当刘子明马子亮弟兄俩,与七十子、八十子、玉团弟兄仨跟着老木匠来到车马店时,六匹骏马已经备好了。孙兰玉手里仍然拿着那套衣服,陈德润挎着一个红布包袱,再加上老神仙跟老秀才,像泥猴的已经不是一个,而是一群。
等老木匠匆匆洗完脸换掉衣服后,陈德润将包袱递到他的手里